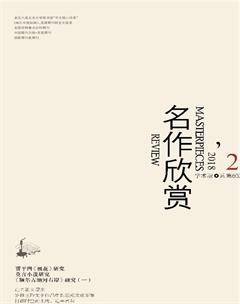中國詩歌中隱喻的法蘭西解讀
摘 要:在今天,西方漢學已經成為中國重建傳統學問時的一個重要參考,如研究西域的伯希和,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研究中國語言史中外來詞的馬西尼等。法國漢學淵源已久,成果豐富。被稱為“中西文化的擺渡者”的法國漢學家程抱一,以及法國漢學家、哲學家弗朗索瓦·于連是當代法國漢學界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他們都有著在中國生活的經歷,熟知中西文化,并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此文針對二者關于中國詩歌中隱喻修辭手法的觀點,從隱喻的含義,隱喻與象征、換喻的關系等方面進行對比與分析,意在進一步認識中國詩歌。
關鍵詞:詩歌 隱喻 象征 漢學
對于中國詩歌的研究是國際漢學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部分。從18世紀傳教士對《詩經》的譯介與研究,到19世紀德理文的《唐詩》(法語: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再到20世紀眾多漢學家對中國詩歌的研究,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對唐詩、詩論的研究,葉維廉對中國詩學的研究,葉嘉瑩對杜甫、陶淵明詩歌的研究等。然而,對于中國詩歌隱喻的分析和研究并不常見,同樣身處法國的漢學家程抱一和于連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詩歌進行研究,卻都關注到了中國詩歌語言隱喻的特點。
路易斯(C.Lewis)說,隱喻是詩歌的生命原則,是詩人的主要文本和榮耀。巴克拉德(Gaston Bachelard)說,詩人的大腦完全是一套隱喻的句法。費尼羅撒(E.Fenellos)指出,隱喻是自然的揭示者,是詩歌的實質。中國的唐詩宋詞堪稱隱喻的語料庫。同樣身處法國的漢學家程抱一和于連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詩歌進行研究,卻都關注到了中國詩歌語言隱喻的特點。
在法蘭西,你對任何一位法國人提起“Francois Cheng”,對方都會以敬佩的口吻告訴你:他是法蘭西學院院士,是個了不起的人!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Francois Cheng),這位被法國媒體稱為“中國和西方文化間永不疲倦的擺渡人”的華裔作家,榮幸地當選為法蘭西學院第705位院士。的確,程抱一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播,以及對法國文化的充實貢獻頗豐。程抱一的《中國詩語言研究》一經出版便在法國引起反響,他運用中法兩重視角對中國詩歌進行了反傳統的解構。一方面,他采用法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分析學的研究方法,從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對詩歌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國詩語言構建的思想基礎是中國道家三元論的宇宙觀。
無獨有偶,與程抱一同處一片法蘭西天空下的巴黎第七大學教授,法國當代漢學家、哲學家、希臘文化學者于連(Fransois Jullien)對于中國文學以及思想的研究也不可小覷,在狄艾里·馬爾塞斯(Thierry Malthus)對于連的采訪中這樣寫道:“很多人要見您,很多人在讀您,很多人……現有十五六個國家翻譯了您的作品。德樂滋援引您,索萊爾推崇您,巴拉杜爾在沉思您。”于連的《迂回與進入》一書,借道中國,回歸希臘,借助東方文化的“妙處”,反思西方文化的“盲點”。正如他在前言中說:“正面對著中國——間接通過希臘。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臘。”于連通過一個西方學者的視角,對中國詩歌的特點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了中國詩歌是隱喻的,中國人的思維和表達都是迂回的結論,而這種迂回的本質在于詩歌語言的隱喻性質。
程抱一和于連都對中國詩歌的隱喻進行了分析,二者既有共同之處,又存在著不同,本文將從隱喻的含義、思想根源,以及與象征、換喻的關系幾個方面對程抱一和于連的研究進行比較。
一、研究思路
也許是因為他是華人,而且在中國生活時間較長的緣故,程抱一雖然借用了西方結構主義和符號分析學的研究方法,但無論是他對中國的詩歌的解讀,還是他的小說《天一言》等作品中,都體現著強烈的道家思想,陰陽、虛實、天地人三元論思想可謂無處不在。例如,程抱一用“陰——陽——中空”的三元空間來進行詩律研究,中國詩歌的音韻(押韻、停頓、平仄)、句法(對仗)都體現了陰陽的對立與互補,而“中空”則是詩歌所體現出的意境,前者激發了“陰”和“陽”,并將兩者引入相互作用和相互轉變之中。
于連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希臘文專業,師承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他在20世紀70年代來到中國,游學于北京、上海兩地,后輾轉至香港新亞學院跟隨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潛心研習中國古代典籍。但他畢竟是在法國成長起來的,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是西方的,研究中國文學也許并不是他的最終目的,在這里,中國用于再開放;它用于讓人們拉開距離,用于從外部反思。它不是又一個要清點的大抽屜,然則,它成為一種理論工具。由此可見,他是通過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和習慣,從而反觀西方的文學乃至哲學。
所以從研究思路來看,程抱一和于連恰恰是相反的,程抱一是在已有的對中國道家思想的理解之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詩歌,但他的研究最終還是回歸到了中國。而于連則是通過對中國詩歌的解讀,來尋找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思想特征,與西方思想文化進行對比,他的研究最終回歸到西方文化本身。研究思路的差異也是造成研究成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二、隱喻的含義
隱喻按照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打比方”,但是這種解釋并不能說明隱喻的本質,中國和西方對于隱喻的研究淵源已久。在西方,從古希臘至今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修辭學——詩學、詩學——語言學、語言哲學——人類學以及思維認知研究。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認為隱喻只能用于詩歌中,是添加在語言上的一種修辭手段。18世紀的浪漫主義隱喻觀則強調隱喻與語言的本質聯系,隱喻增強了語言特有的活動,并創造著新的現實。20世紀50年代,隱喻研究進入多元研究高潮,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歐美隱喻研究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中國古代對于隱喻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階段:先秦時期的哲學研究、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的詩學研究、唐宋至明清時期的修辭學研究。清末民初至20世紀末屬于轉型期。1949年之前,傳統隱喻研究向西方隱喻研究范式靠攏;1949年以來,漢語學界的隱喻研究開始注重引進并且評述西方當代隱喻理論。由此可知,隱喻包括三種基本含義,中國固有的“隱—喻”范疇、作為修辭學術語的隱喻以及西文“metaphor”的漢語對譯,前者是“比興”“意象”“意境”等古典詩學的基型,后者大眾理解的修辭的“隱喻”僅在隱喻層面與“隱—喻”和“metaphor”相對應,而“metaphor”包含了修辭學、詩學、語言學、認知哲學層面的隱喻。本文以中國詩歌中的隱喻為研究對象,主要指中國固有的“隱—喻”范疇。
程抱一認為隱喻是與“比”相對應的概念。“比”和“興”是中國文體學的兩種基本手法,而在西方修辭學中與之對應的是“隱喻”和“換喻”。“比”的含義是詩人求助于一個意象(通常來自大自然)來形容他想表達的意念或感情。“隱喻”與“比”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們的區別在于,在中國這方面,“比”寓于一個普遍化了的系統中,而“隱喻”所指向的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隱喻與換喻相關聯,從而更新了含義,避免詩歌落入窠臼。
于連認為隱喻的本質是歸于某種沒有說出來但以間接方式指明的東西,它相應于并囿于重視暗含意義的理論傳統,即中國評論家們有關景的觀點。于連認為隱喻的價值在于它的多義性,它使詩的意義層出不窮,使感情的表達間接而含蓄,使詩歌只微露情感就得以使情絲綿長難盡,詩的生命力正是系于這種不定性。例如: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這首詩的優美之處在于微妙而間接的表達,詩中無一字涉及所述之情,而憂傷之情卻已經寓于詩歌的每個字中,隱喻使情感的間接表達成為可能。詩中出現的“越鳥”“胡馬”“衣帶漸緩”“浮云蔽日”等形象在那個時代早已是老生常談了,但是對于詩歌的解讀卻不止一種,這首表達忠誠之心的作者可能是被誹謗的賢臣、被拋棄的妻子,抑或是朋友。
程抱一和于連都認為中國詩歌是高度隱喻的,而且都認為隱喻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程抱一是在隱喻與比的對比中得出的結論,而于連是在隱喻與象征的對比中得出結論,比和象征指向一個普遍化了的系統之中,而隱喻是具有多義性、模糊性的,這對我們理解詩歌具有啟發性,正如古人所說“詩無達詁”,詩歌并不是具有固定的解釋的,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也曾說過:“詩歌就是我們對它的闡釋。”但程抱一所研究的隱喻更接近于中國傳統固有的“隱—喻”范疇,而于連對隱喻概念的界定帶有一些哲學的意味,例如:“隱喻的距離以一種隱—顯的方式說明它所引述的現實,而又不去定義或表現它,也就是說不是從同一性的角度觀察它:它顯示的是事物的內涵,而不是本質(使存在與顯現相對立的本質)。”于連在這里從哲學的角度對隱喻進行分析,認為隱喻顯現的并非全部“真實”或核心本質,但也絕未變幻出假象或幻象,而是最大限度地還原了“真實”的原生風貌。隱喻是一種非真非假、亦真亦假的“幻境”或曰仿真的隱喻現實。
三、隱喻的根源
中國詩歌為什么會形成隱喻的特征?程抱一與于連都進行了探索。程抱一認為中國詩歌的高度隱喻性要從特定的宇宙觀和文字本身的性質去尋找,而他所說的宇宙觀是道家的宇宙觀,即天地人三元,在這三元中,對人和地的關系而言,天代表了一種另外的秩序,一種對人地之間親密結合的超越,而意象正是人的精神與世界精神的相遇,在中國人眼中,在人的想象能力和形象化的宇宙之間的持續和必然的交流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他堅信二者形成一個整體,它們由同樣的生氣所激發,生氣將它們結成有機的和表意的組合。從文字本身的性質來看,整個表意文字,通過它們與所指稱的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字與字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個隱喻——換喻(Metonymy)系統。從某種方式上說,每一個表意文字都是一個強有力的隱喻,它在與其他表意文字的結合上享有極大的靈活性,并創造出豐富的引申寓意,更勝于一種指稱語言所能做的。程抱一在書中還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
a.由兩個成分構成的表意文字
心+秋=愁,哀愁
人+木=休,休息
b.形成隱喻的兩個字的詞
天——地=宇宙
手——足=親情
于連則把中國詩歌隱喻性歸結為兩個方面。首先是漢語言的普遍特征,即迂回,它體現在中國的作戰戰術、外交辭令、歷史文獻等方方面面,它意味著中國文化示意方式的獨特性。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也在他的《中國人的性情》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來評論中國人“迂回表達的能力”,例如文中寫道:“中國人能夠以千百種不同的方式宣布一個人的死亡,而每一種方式都極優雅地掩飾了事件的殘酷。”于連認為這種迂回的微妙并不產生于語言的復雜,而產生于間接的說明,中國傳統習慣在詞外理解真正的意義,例如《論語》,于連認為其中的對話既無意于構建一種“科學”,亦不想構建一種道德,它也從不會去定義什么,盡管它含義深遠,可往往是引而不發。在古代中國“理論”的和“本質”的范疇沒有建立起來,透明的象征沒有出現,而更加及時、自發、間接、多義的隱喻存在于詩歌中。其次,回歸到詩歌本身,于連站在評論詩歌的角度對隱喻進行解釋,認為隱喻的存在與“詩緣情”的詩歌理論緊密相關,聽憑不同觀點的解釋使詩歌進入隱喻的結構。也正由于此,詩的主題為不盡的境界所激動并且抒發最深遠的情感,詩意應從“寄情”出發理解,并不希求轉向另一種觀念。
對于詩歌語言隱喻性根源的探尋,二者得出了不同的答案,程抱一把它歸結為宇宙觀和表意文字的特征,正是由于中國人把自己與天、地視為互相溝通、聯系的,才在詩歌中大量引入景物以表達自己的情感,而表意文字本身的隱喻性質也影響了詩歌語言的隱喻性。思維與語言是隱喻互為表里的二維,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它與語言符號產生的文化、歷史等息息相關。程抱一用道家宇宙觀來分析隱喻,體現了思維方式在隱喻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于連則從中國語言迂回的特征及其產生的原因,“詩緣情”的詩歌理論進行探尋,使得中國詩歌的隱喻性有跡可循,說明了隱喻是一種情感表達需求,也是一種修辭策略。
四、隱喻與換喻、象征
在隱喻和象征(Symbolize)的關系上,程抱一一方面認為隱喻使語言組織成一個廣大的結構化的象征的整體,由此使自然的大部分得到清點、開發與教化,中國詩歌是民間的共有財富,構成一部真正的集體神話,通過這個象征網絡,詩人尋找打破能指/所指的閉合路線,并借助類比和內在聯系的游戲建立符號與事物之間的另一種關系。另一方面,他認為,系統化的因襲的象征整體并不會使詩歌落入窠臼,因為隱喻又形成了一個換喻網絡,而這一網絡得到由五行出發加以精致化的整整一個感應系統的強化。詩人以這一敞開的網絡為依傍,便能夠避免落入窠臼的危險。他舉了一首杜甫的《月夜》:“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其中“云鬟”和“玉臂”的意象是因襲的,云鬟用來比喻女人的頭發,玉臂用來形容皮膚白皙柔滑的女子的臂膀,這些意象都是平庸的,看上去非常陳舊,幸而有了與它相伴的其他意象,它們顯得非常清新,并且必不可少,云鬟與香霧相連接,因為這兩個意象都含有大氣的成分,它們的共同本性給人一種一個受另一個激發而生的印象,因此因襲的隱喻不但沒有使詩句淪為“窠臼”,而且當它們被巧妙地組合,反而得以創造出意象之間的一些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并且自始至終,將它們如此保持在隱喻層。
于連則認為中國詩歌本身就是隱喻的而不是象征的:“如果說中國詩幾乎沒有在象征意義上得到解釋,那它卻在隱喻的范圍內得到發揮。在一方面難以開辟的道路,于另一方面則通暢無阻。”“它并不會讓我們進入另一范圍之中——人們以某種名義命名的:即普遍的、抽象的、精神的名義。”于連發現中國的注釋者在解釋《詩經》中的種種形象時,并不是從普遍性和各種本質范圍內展現它們,而是偏向于歷史角度在政治范圍內閱讀,對每一首詩的理解都是結合特殊的歷史境況的,不是從中尋找象征意義而是發掘隱喻。
隱喻與象征不同。原始社會,象征是物體與觀念之間在人的心理上形成的某種神秘而特殊的等同結構;古希臘時期,象征獲得了形而上的維度;中世紀時期,象征是宗教社會的生活方式;18至19世紀,象征的理論形態逐步走向系統和完整,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新語言,更被源起于法國的象征主義文學作為詩歌乃至一切藝術的基本原則,登上了詩學領域的神壇;進入20世紀,象征不再囿于表現手段、思維方式和創作原則,而被界定為人類的生存方式,廣泛滲透于文化學、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和符號學等多種學科。于連所說的象征指詩歌的表現形式。象征代表的是具體而特殊的某種東西,任何象征意義都是以足夠穩定和邏輯的方式構建的,象征指向更普遍、更本質的范疇,把詩的主題導向普遍性的新領域,象征更加透明,任何象征意義都是以足夠穩定和邏輯的方式被構建的。而隱喻則把詩的主題變成無盡而不定的情的向量,它的本質是歸于某種沒有說出來但以間接方式指明的東西,它并不會讓我們進入另一范圍之中——人們以某種名義命名的,即普遍的、抽象的、精神的名義。例如在中國傳統中,沒有人把“浮云蔽日”的景讀作描寫景物的現實記錄,也沒有人把它讀作“障礙”或“距離”的純粹形象,而是作為一種隱喻,一種情感的記憶。
程抱一和于連都認識到了中國詩并非是落入窠臼的固定象征系統,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但是程抱一是從隱喻與換喻(Metonymy)的關系中說明的,而于連是通過隱喻與象征的不同說明的。同時程抱一也并沒有否定中國詩歌中存在著象征,并認為隱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象征網絡,隱喻使自然界中的事物得到清點、開發與教化,中國詩歌是一個集體神話。程抱一從符號與事物的聯系中,看到了隱喻與象征的聯系,同時又從符號與符號的聯系中看到了隱喻與換喻的聯系,從而全面地解釋了中國詩歌既高度隱喻又不會落入窠臼,相比之下于連只看到了符號與事物的聯系,否定中國詩歌是象征的,“說有容易說無難”,于連對于中國古代詩歌中象征的否定還稍顯薄弱。
兩位有著相似經歷的法國漢學家,一個帶著對中國文化深厚的理解,又站在語言文字的角度,采用西方結構主義的方法解讀中國詩歌;一個帶著思想雄心,不愿只做中國漢學的重述,而是站在哲學的視角,試圖探尋中國文學背后隱藏的思想。從此觀之,他們為我們重新認識西方漢學,重新認識中國的詩歌以及語言,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也使中西有關隱喻的詩學理論互相補充,豐富了隱喻的含義。
參考文獻:
[1] 張沛.隱喻的生命[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 宇文所安.迷樓[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3] 弗朗索瓦·于連.迂回與進入[M].杜小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4] 阿瑟·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情[M].王續然譯.北京:長征出版社,2009.
[5] 束定芳.論隱喻的詩歌功能[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6).
[6] 馮曉虎.隱喻——思維的基礎篇章的框架[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
作 者:海麗瑋,華東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編 輯:趙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