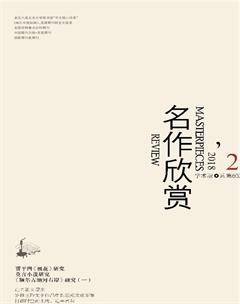趙翼論吳梅村
摘 要:詩話大多是散見而沒有組織的條例,趙翼晚年的代表作《甌北詩話》不同于普通詩話,它分人論述,可見其是有意識(shí)地在作論述。吳梅村入《甌北詩話》卷九,趙翼用縝密的論證抉發(fā)了吳梅村詩歌諸多為人忽略的獨(dú)創(chuàng)性,他才學(xué)式的批評(píng)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rèn)識(shí)吳梅村其人以及清代中期學(xué)者對(duì)吳梅村的接受,對(duì)吳梅村的評(píng)論意見至今仍值得我們參考。
關(guān)鍵詞:趙翼 吳梅村 甌北詩話
趙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松,號(hào)甌北。江蘇陽湖人,和袁枚、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jìn)士,官至貴西兵備道,著有《廿二史札記》《檐曝雜記》《甌北詩話》等。其中《甌北詩話》成書于嘉慶七年(1802)五月,是趙翼晚年時(shí)讀完唐宋各詩家的“全集”之后,心有所悟后寫出的評(píng)論,因此其評(píng)論注重于詩人實(shí)際的作品內(nèi)容。在評(píng)論諸詩家時(shí),趙翼一以貫之地堅(jiān)持了其“創(chuàng)新”與“性情”的標(biāo)準(zhǔn),他比其他詩論家更重視詩人的生平考證及其實(shí)際作品內(nèi)容,因此對(duì)于詩人的優(yōu)缺點(diǎn)都能有客觀的論述。
吳偉業(yè)(1609—1672),字駿公,號(hào)梅村,是趙翼心儀的前輩詩人。趙翼用縝密的論證在《甌北詩話》卷九中抉發(fā)了吳梅村詩歌諸多為人忽略的獨(dú)創(chuàng)性,書中對(duì)吳梅村的論述尤見批評(píng)眼光的銳利和內(nèi)容安排的匠心,對(duì)吳梅村之人及其詩的評(píng)論意見至今仍值得我們參考。
一、論吳梅村其人
趙翼在《甌北詩話》卷九中首先對(duì)明代詩壇作了一個(gè)總體評(píng)價(jià):“高青丘后,有明一代,竟無詩人。”有明一代,詩壇流派眾多,明初期有以歌功頌德為能事的“臺(tái)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明中期有掀起“復(fù)古”運(yùn)動(dòng)的前、后七子,明后期有影響巨大的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明末還有幾社陳子龍等人,這其中不乏名家,但是到了趙翼這里,卻成了高啟之后明無詩人。經(jīng)過多方比較,趙翼指出明初李東陽有“才力尚小”的缺點(diǎn),明中前、后七子“迄今優(yōu)孟衣冠,笑齒已冷”,明末大家陳子龍存在“意理粗疏處,尚未免英雄欺人”的不足,在他看來,只有明末期的錢謙益和吳梅村可以稱為大家。錢、吳二人在明末就已經(jīng)享譽(yù)詩壇,其中錢謙益更是當(dāng)時(shí)的文壇盟主、士人領(lǐng)袖,趙翼評(píng)“惟錢、吳二老,為海內(nèi)所推,入國(guó)朝稱兩大家”,很顯然他已經(jīng)把錢謙益、吳梅村放在清初詩壇來研究。從趙翼這則對(duì)明代詩壇評(píng)價(jià)的詩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duì)吳梅村的重視。
對(duì)于吳梅村,趙翼字里行間充滿贊賞之情,他稱贊梅村:“以唐人格調(diào),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為近代中之大家。”趙翼喜歡把不同的作家放在一起進(jìn)行比較,辨別這些作家的異同、高下,高啟被收錄在《甌北詩話》第八卷(和元好問合為一卷),為了突出吳梅村的才華,特地拿吳梅村和高啟進(jìn)行比較,他認(rèn)為高啟的健舉之氣勝于梅村,梅村語言不若高青丘之清雋,但也提到在情感表達(dá)方面,吳梅村深于高青丘。的確,吳梅村寫有大量感傷時(shí)事、反映現(xiàn)實(shí)的作品,他所詠的也大多和當(dāng)時(shí)的重大時(shí)事有關(guān),比如《蕭史青門曲》《圓圓曲》等作品,感情充沛,纏綿凄婉,其中《圓圓曲》更是清詩中享有最高聲譽(yù)的七言歌行。吳梅村詩歌才華高卓,受到趙翼青睞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了。
除了詩歌成就不凡,吳梅村的個(gè)人魅力也受到趙翼的欣賞。清兵南下,南明弘光王朝滅亡,錢謙益率先投降,他的這一舉措為遺民所不齒,因此趙翼本人雖然承認(rèn)了吳梅村“當(dāng)時(shí)名位聲望,稍次于錢”,但是他看不起當(dāng)時(shí)的文壇盟主錢謙益,對(duì)錢謙益的評(píng)價(jià)字里行間充滿諷刺語氣。錢謙益的成就高于吳梅村,但是錢的名聲早壞,且清高宗時(shí)錢氏之詩已被列為禁書,因此趙翼并沒有把錢謙益收入到《甌北詩話》。吳梅村后期也和錢謙益一樣出仕了新王朝,但是趙翼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卻截然不同于錢謙益:“梅村當(dāng)國(guó)亡時(shí),已退閑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于降表僉名。”在趙翼看來,南明王朝滅亡時(shí)吳梅村已是平民百姓,吳并沒有對(duì)不起國(guó)家和人民,而且他的出仕是出于無奈,是為了保護(hù)家人和朋友,即使出仕了新王朝,吳也一直自慚自悔。趙翼的評(píng)價(jià)并不是憑空想象的,吳梅村赴召北上,經(jīng)過淮陰時(shí)就說:“我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為了保全家族、朋友,吳梅村迫于壓力不得不出仕新王朝,但是由于自悔愧疚于平生之志,他一直非常后悔和痛苦,在即將死亡之際還一直惦念著舊王朝。吳梅村忠心于平生之志,他的自慚和悔恨一直陪伴到死亡,因此趙翼認(rèn)為吳梅村并沒有做錯(cuò)什么。既然吳梅村心與跡皆可以體諒,再加上吳梅村本身確實(shí)才華高卓,詩歌成就不凡,趙翼將吳梅村收入《甌北詩話》也就順理成章了。
二、論吳梅村詩歌的用典
王漁洋中年搜輯平生故舊之詩,編成《感舊集》,其中選取了吳梅村詩歌十二首。針對(duì)王漁洋所選之詩,趙翼認(rèn)為這只是一時(shí)之見,不能作為定評(píng),在他心里,王漁洋選的這十二首詩并不能代表吳梅村詩歌的最高成就,趙翼曰:“梅村之詩最工者,莫如《臨江參軍》《松山哀》《圓圓曲》《茸城行》諸篇,題既鄭重,詩亦沉郁蒼涼,實(shí)屬可傳之作……特少遜其遒煉耳。”
趙翼推崇吳梅村的詩歌基本都是描寫歷史事件的長(zhǎng)篇歌行,這一方面和他史學(xué)家的身份有關(guān),趙翼精通史學(xué),和王鳴盛、錢大昕并稱為乾隆朝三大史學(xué)家。他本人寫過《逃荒嘆》《剝榆皮》《海上》等反映百姓遭遇沉重災(zāi)難的作品,頗有“以詩為史”的自覺,因此對(duì)于同樣具有“詩史”意識(shí)、喜歡將史實(shí)寫入詩歌的吳梅村,他是極力肯定的。吳梅村寫有《過維揚(yáng)吊少司馬衛(wèi)紫岫》,自注:“韓城人,余同官同年,死揚(yáng)難。”趙翼根據(jù)這首詩“以詩證史”,多方考證,得出:“按此即《明史·高杰傳》中衛(wèi)胤文也。今正史不載,獨(dú)賴梅村一詩,得傳死節(jié)于后,不可謂非胤文之幸矣。”關(guān)于明朝將領(lǐng)李國(guó)禎究竟是留名青史還是遺臭萬年的問題,后人爭(zhēng)論不休。當(dāng)時(shí)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rèn)為李國(guó)禎是殉節(jié)而死,另一種說法認(rèn)為李國(guó)禎是拷贓而死,究竟應(yīng)該相信哪一種說法?趙翼把吳梅村的詩句作為解決歷史爭(zhēng)議話題的定論,吳寫有一首《吳門遇劉雪舫》,趙翼根據(jù)其中的詩句“寧為英國(guó)死,不作襄城生”判斷李國(guó)禎是殉節(jié)而死,他說:“梅村赴召入都,距國(guó)變時(shí)未久,國(guó)禎之死,尚在人耳目間,固不敢輕為誣蔑也……是蓋據(jù)梅村詩為證,然則梅村亦可稱‘詩史矣。”除了贊賞吳梅村的詩歌題材內(nèi)容選取于重大歷史事件,趙翼還很欣賞吳梅村詩歌的用典。吳梅村詩歌用典多取正史,趙翼評(píng)價(jià)吳梅村詩歌:“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shí),而選聲作色,又華艷動(dòng)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作為史學(xué)家,趙翼喜歡“以詩為史”,和吳梅村一樣都具有“詩史”意識(shí),他稱贊吳梅村用典道:“梅村熟于《兩漢》《三國(guó)》及《晉書》《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后人獵取稗官叢說,以炫新奇者也……可謂典切矣!”
對(duì)于吳梅村詩歌的用典不當(dāng)?shù)牡胤剑w翼也會(huì)指出:“然亦有與題不稱,而強(qiáng)為牽合者。”趙翼列舉了吳梅村的《補(bǔ)禊鴛湖》《觀棋》等詩,提出了吳梅村隨手闌入,不加檢點(diǎn)之病。吳梅村《揚(yáng)州》詩:“豆蔻梢頭春十二,茱萸灣口路三千。”趙翼根據(jù)杜牧詩“娉娉裊裊十三馀,豆蔻梢頭二月初”,認(rèn)為無所謂“春十二”也。當(dāng)然,對(duì)于吳梅村用典與題不稱,強(qiáng)為牽合的問題,趙翼并沒有盲目批評(píng),他看到后來的文壇盟主王漁洋也寫過類似用典與題不稱,強(qiáng)為牽合的詩句:“景陽樓畔文君井,明圣湖頭道韞家。”清朝初期,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漢族士大夫眷戀故明,宣揚(yáng)“夷夏之防”一類思想,對(duì)鞏固清統(tǒng)治極為不利。清廷統(tǒng)治者為鞏固統(tǒng)治,迫害知識(shí)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因此清朝也是文字獄最為盛行的朝代。吳梅村詩歌多隱含時(shí)事,其中也不乏批評(píng)新朝統(tǒng)治者、眷戀舊王朝的詩作,這些詩作如果不進(jìn)行修改、刪減,就極易被清朝犬牙抓住把柄,牽連家人和朋友,因此后期吳梅村出仕,他對(duì)自己以前寫過的詩歌進(jìn)行了大量的刪減、修改,詩歌的一些內(nèi)容、用典也理所當(dāng)然地在修改范圍里。趙翼應(yīng)該也有這一方面的考慮,所以他對(duì)吳梅村這類用典與題不稱,強(qiáng)為牽合的詩句評(píng)價(jià)道“蓋當(dāng)時(shí)風(fēng)氣如此”。
三、論靳榮藩注吳詩
吳梅村的詩集很少有注,乾隆年間黎城麥倉村人靳榮藩用了數(shù)十年的時(shí)間為梅村詩箋釋,無一字無來歷,著《吳詩集覽》20卷。趙翼肯定了靳榮藩為吳梅村箋釋,他說:“介人注梅村詩,在一百余年之后,覺更難也。且梅村身閱興亡,時(shí)事多所忌諱,其作詩命題,不敢顯言,但撮數(shù)字為題,使閱者自得之……”靳榮藩根據(jù)吳梅村同時(shí)在朝、在野往還贈(zèng)答之人,一一考查史傳;如果史傳沒有記載,就考查各府、各縣志;如果各府、各縣志都還是沒有記載,就采取故老傳聞,一一詳盡地完善吳梅村的履歷,可以說是花費(fèi)了大量的時(shí)間和心血。靳榮藩援史以證詩,他的注釋使吳氏之詩“本指顯然呈露”,因此趙翼大贊道:“梅村詩一日不滅,則靳注亦一日并傳無疑也。”
蔣寅在《才學(xué)識(shí)兼?zhèn)涞脑姼柙u(píng)論家趙翼》一文中說:“貫通古今的文學(xué)史眼光最終成就了趙翼的史識(shí)。”身為史學(xué)家的趙翼,始終秉持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shí)錄精神。同時(shí)憑借豐厚的史學(xué)知識(shí),他能夠正確審視靳榮藩為吳梅村詩集所作之箋釋。靳榮藩在《吳詩集覽》論梅村謂:“大家手筆,興與理會(huì)。若穿鑿附會(huì),或牽合時(shí)事,強(qiáng)題就我,則作者之意反晦。”趙翼評(píng)道:“此真通人之論也。”但他也提到了靳榮藩的缺點(diǎn):“乃其注梅村詩,則又有犯此病者。”并指出了靳注中有大量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地方:“梅村五古如《讀史雜詩》四首、《詠古》六首,七古如《行路難》十八首,皆家居無事,讀書得間所作,豈必一一指切時(shí)事……”
除了大量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注釋,趙翼還以自身的史學(xué)之才指出并糾正了靳注錯(cuò)誤的地方,他說:“《避亂》第六首‘曉起嘩兵至,戈船泊市橋。草草十?dāng)?shù)人,登岸沽村醪。不知何將軍,到此貪逍遙?按此系順治二年,太湖中明將黃蜚、吳之葵、魯游擊,吳江縣吳日生、好漢周阿添、譚韋等糾合洞庭兩山,同起鄉(xiāng)兵,俱以白布纏腰為號(hào),后入城,圍巡撫土國(guó)寶,為國(guó)寶所敗,散去。此事見《海角遺編》。福山人所著,不著姓名。靳注亦不之及。”靳注中錯(cuò)誤之處,趙翼都一一指出并糾正,這對(duì)后世之人了解梅村其人其事無疑幫助巨大。
四、結(jié)語
詩話大多是散見而沒有組織的條例,但《甌北詩話》分人論述,可見其是有意識(shí)地在作論述。由于趙翼史學(xué)家的背景,加上其多年來的學(xué)力積累,可以看到《甌北詩話》一書的內(nèi)容不同于“以資開談”的一般詩話,而是從詩人的作品及創(chuàng)作背景中找到確實(shí)的證據(jù),從而提出他的看法。趙翼選吳梅村入《甌北詩話》,對(duì)吳梅村前后詩風(fēng)的變化、詩歌體裁的優(yōu)劣都有精彩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吳梅村所具的“詩史”意識(shí)、“以史入詩”尤為贊賞,也通過詩話的形式將靳榮藩注梅村詩歌中錯(cuò)誤的地方進(jìn)行糾正,他才學(xué)式的批評(píng)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rèn)識(shí)吳梅村其人,以及清代中期學(xué)者對(duì)吳梅村的接受。
參考文獻(xiàn):
[1]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diǎn).清詩話續(xù)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吳偉業(yè)著,葉君遠(yuǎn)選注.吳偉業(yè)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
[3] 杜牧著,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王士 著,趙伯陶選注.王士 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
[5] 蔣寅.才學(xué)識(shí)兼?zhèn)涞脑姼柙u(píng)論家趙翼[J].文學(xué)評(píng)論,2014(5):170-177.
作 者:楊戴君,廣州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
編 輯: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