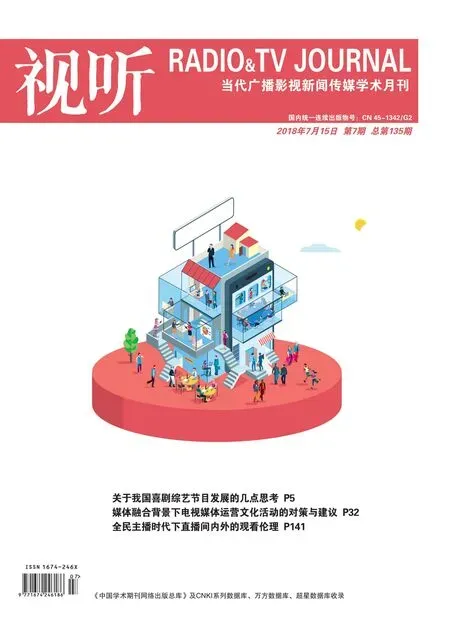《時(shí)務(wù)報(bào)》政論與維新變法的公共輿論建構(gòu)
□楊雪瑩 魯學(xué)靜
一、維新思潮與《時(shí)務(wù)報(bào)》的誕生
(一)甲午戰(zhàn)敗與變法圖強(qiáng)
1894年6月30日,中日兩國(guó)宣戰(zhàn),爆發(fā)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中國(guó)戰(zhàn)敗。1895年2月24日,清政府代表李鴻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馬關(guān)正式開(kāi)議。3月23日,經(jīng)清政府同意,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馬關(guān)條約》上簽字。這是近代中國(guó)最為不平等的條約之一,割臺(tái)灣、賠巨款、開(kāi)商埠、片面最惠國(guó)待遇等,喪權(quán)辱國(guó),舉國(guó)震驚,愛(ài)國(guó)志士們更緊迫地尋求救國(guó)良方。一時(shí)間,對(duì)于外國(guó)先進(jìn)思想文化、科學(xué)技術(shù)的需求大增,要求有能“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的橋梁,于是“有《時(shí)務(wù)報(bào)》之設(shè)”,“律閱者周知全球大勢(shì),熟悉本國(guó)近狀,不足以開(kāi)民智而雪國(guó)恥。”
(二)《時(shí)務(wù)報(bào)》創(chuàng)刊
1895年,康有為創(chuàng)辦的“強(qiáng)學(xué)會(huì)”被查封后,梁?jiǎn)⒊⑼艨的辍ⅫS遵憲等人利用強(qiáng)學(xué)會(huì)的剩余公款在上海籌辦起了《時(shí)務(wù)報(bào)》,汪康年擔(dān)任經(jīng)理,梁?jiǎn)⒊沃鞴P。1896年8月9日,《時(shí)務(wù)報(bào)》創(chuàng)刊,發(fā)行第一冊(cè)。每十天出刊一期,每?jī)?cè)三萬(wàn)余字,是一份旬刊雜志。1898年8月8日出版最后一冊(cè),為期兩年,共計(jì)69冊(cè)。
《時(shí)務(wù)報(bào)》是戊戌時(shí)期改良派的機(jī)關(guān)報(bào)和維新運(yùn)動(dòng)的陣地,以“變法圖存”為宗旨,大膽批評(píng)時(shí)政,針砭時(shí)弊,傳播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介紹西方科學(xué)文化。《時(shí)務(wù)報(bào)》分設(shè)論說(shuō)、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bào)譯等欄目。其中“論說(shuō)”部分是該報(bào)的精華和點(diǎn)睛之處,由于議論新穎、文字通俗,數(shù)月之內(nèi),銷售萬(wàn)余份,大大促進(jìn)了維新變法的思想宣傳,推動(dòng)了維新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發(fā)行一年后,《時(shí)務(wù)報(bào)》的發(fā)行量由創(chuàng)刊時(shí)的3000多份增加到1.2萬(wàn)份,最高達(dá)1.7萬(wàn)份,成為維新派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機(jī)關(guān)報(bào)。
二、《時(shí)務(wù)報(bào)》政論與維新變法的政治宣傳
近代中國(guó)的文人非常重視報(bào)刊論政,認(rèn)為“其論說(shuō)耶,夫人之語(yǔ)言,猶人之行步也,一舉足則不能無(wú)方向,一著論則不能無(wú)總之”①。因此,中國(guó)近代報(bào)紙的政論部分,無(wú)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輿論導(dǎo)向和動(dòng)員。
《時(shí)務(wù)報(bào)》下設(shè)論說(shuō)、諭折、域外報(bào)譯、文編等數(shù)個(gè)欄目,其中,以政論文部分的影響最為廣泛,而域外報(bào)譯雖然所占比例很大,但“閱報(bào)者仍注意前數(shù)頁(yè),而后載西事均不甚留意”②。由此可見(jiàn),政論是《時(shí)務(wù)報(bào)》的精華和點(diǎn)睛之處。而梁?jiǎn)⒊鳛椤稌r(shí)務(wù)報(bào)》的主筆,在發(fā)行55冊(cè)共133篇政論中,出自他筆下的有60多篇。
《時(shí)務(wù)報(bào)》上所登載的言論,宗旨大都為救亡圖存、變法圖強(qiáng)。梁?jiǎn)⒊瑸椤稌r(shí)務(wù)報(bào)》撰稿期間,先后發(fā)表了《變法通議》《知恥學(xué)會(huì)敘》《論中國(guó)積弱由于防弊》等文章,充分表明了梁?jiǎn)⒊祜诶脠?bào)刊進(jìn)行變法維新、民智啟蒙的直接陳述與鼓吹。
《時(shí)務(wù)報(bào)》宣傳變法維新的第一篇系列性文章是梁?jiǎn)⒊摹蹲兎ㄍㄗh》,包括《論不變法之害》《論學(xué)校》等內(nèi)容,在報(bào)上分期刊載,是維新運(yùn)動(dòng)的綱領(lǐng)性著作。在這組文章里,梁?jiǎn)⒊瑯O力論證了對(duì)于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變法乃是勢(shì)在必行的觀點(diǎn),除此之外,還將變法與國(guó)民的個(gè)性解放和思想啟蒙結(jié)合在一起,對(duì)維新變法的理論主張進(jìn)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
此外,該文還提出了歷史進(jìn)化論的觀點(diǎn),將達(dá)爾文的生物進(jìn)化論從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引入人文社科領(lǐng)域,認(rèn)為自然界中的事物固然在不斷變化,而人類社會(huì)中亦無(wú)一成不變的社會(huì)制度,進(jìn)而以考察中外的關(guān)系,以闡明變法改革是當(dāng)今的必然之勢(shì),同時(shí)說(shuō)明不變之害及變法自強(qiáng)之理。
戊戌變法時(shí)期,梁?jiǎn)⒊l(fā)表的《變法通議》《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論中國(guó)積弱由于防弊》等重要文章均登載于《時(shí)務(wù)報(bào)》。梁?jiǎn)⒊凇稌r(shí)務(wù)報(bào)》上發(fā)表政論,呼吁變法改革、痛陳愛(ài)國(guó)救亡,言語(yǔ)犀利,在一部分有識(shí)之士和開(kāi)明士紳中引起了強(qiáng)烈反響,“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窮陬,無(wú)不知有新會(huì)梁氏者。”其他維新派人士也紛紛提筆撰稿,呼吁變法改革,深刻揭露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jī),猛烈抨擊封建頑固勢(shì)力,因此《時(shí)務(wù)報(bào)》風(fēng)行全國(guó),“為中國(guó)有報(bào)以來(lái)所未有,舉國(guó)趨之,如飲狂泉。”
三、《時(shí)務(wù)報(bào)》與中國(guó)近代公共輿論空間的建構(gòu)
(一)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認(rèn)為,18世紀(jì)的西歐社會(huì)中出現(xiàn)的咖啡館、俱樂(lè)部、報(bào)紙、雜志和沙龍,是公眾進(jìn)行自由交往、討論公共問(wèn)題的公共領(lǐng)域,促進(jìn)了政治權(quán)威重要合法性基礎(chǔ)的形成。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lǐng)域”,指的是形成于政府和社會(huì)之間、特定的公共空間,假定在這個(gè)空間中,公眾們可以自由發(fā)表言論,議論時(shí)政,而不受國(guó)家的干涉。公共領(lǐng)域最關(guān)鍵的含義是獨(dú)立于政府管控和政治建構(gòu)之外的公共輿論和公眾交往,它們對(duì)于國(guó)家政治權(quán)力具有批判性功能,而且也存在政治合法性基礎(chǔ)。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理論,政府與社會(huì)之間若出現(xiàn)公共輿論空間,以下兩個(gè)先決條件是首要前提:一是社會(huì)公眾群體具有強(qiáng)烈的政治批判意識(shí)和公共輿論關(guān)懷;二是公眾群體參與討論社會(huì)化的獨(dú)立于國(guó)家權(quán)力系統(tǒng)之外的公共社會(huì)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這二者以梁?jiǎn)⒊啊稌r(shí)務(wù)報(bào)》其他主編的政論為表現(xiàn)形式,充分融會(huì)并體現(xiàn)于《時(shí)務(wù)報(bào)》,逐步建立起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代表著社會(huì)共同利益的公共領(lǐng)域,從而建構(gòu)了近代中國(guó)變法維新的公共輿論空間。
(二)《時(shí)務(wù)報(bào)》的維新思想宣傳與社會(huì)動(dòng)員
作為呼吁變法維新、致力于傳播改良主義思潮的有識(shí)之士在維新變法的旗幟下共同創(chuàng)辦的報(bào)刊,《時(shí)務(wù)報(bào)》流通和影響的范圍極為廣泛。此外,《時(shí)務(wù)報(bào)》借助救亡圖存的大旗,呼吁改革,倡言變法,觀點(diǎn)新穎,議論犀利,且文筆富有激情、清新流暢,因而大受讀者歡迎。由此可見(jiàn),《時(shí)務(wù)報(bào)》雖在上海發(fā)行,卻已風(fēng)靡全國(guó),這說(shuō)明《時(shí)務(wù)報(bào)》已經(jīng)具備了社會(huì)的、公共的、為大多數(shù)國(guó)民所接受的、營(yíng)造公共輿論空間所需的許多要素,真正開(kāi)啟了近代中國(guó)公共輿論空間的全面整合與整體建構(gòu)。
哈貝馬斯提出,由于社會(huì)進(jìn)步和思想解放,由社會(huì)輿論環(huán)境和公眾意見(jiàn)表達(dá)所構(gòu)成的公共輿論空間日益擴(kuò)張。《時(shí)務(wù)報(bào)》喚醒了大部分知識(shí)分子和開(kāi)明士紳的愛(ài)國(guó)良知,也使普通大眾受到了教育,從而形成了近代中國(guó)公共輿論空間的短暫擴(kuò)展。而《時(shí)務(wù)報(bào)》對(duì)維新思想的宣傳,使變法維新的呼聲在士人群體中充分?jǐn)U散和傳播,而它呼吁變法改良的觀念與主張,也令民眾群起而呼應(yīng)。對(duì)于致力于變法維新的有識(shí)之士和開(kāi)明士紳而言,《時(shí)務(wù)報(bào)》的主編們便是他們聲同氣求、志同道合的同志,而《時(shí)務(wù)報(bào)》更是成為他們凝聚彼此意識(shí)的平臺(tái)。變法聲勢(shì)既起,維新運(yùn)動(dòng)便借勢(shì)而發(fā)展壯大,而啟發(fā)民智、變法圖強(qiáng)的思想主張也逐漸為公眾群體所理解和接受。
(三)《時(shí)務(wù)報(bào)》與維新變法的公共輿論建構(gòu)
近代中國(guó)有識(shí)之士的辦報(bào)理念,是參政議政先于經(jīng)營(yíng)利潤(rùn)。他們最為注重的是傳播報(bào)刊的思想主張,培養(yǎng)國(guó)民的政治批判意識(shí),從而營(yíng)造社會(huì)公共輿論空間。《時(shí)務(wù)報(bào)》創(chuàng)刊后,一些新學(xué)士子“群相呼應(yīng),起而組織學(xué)會(huì),討論政治問(wèn)題與社會(huì)問(wèn)題”。③《時(shí)務(wù)報(bào)》上第一篇宣傳變法思想的文章《變法通議》就已經(jīng)提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kāi)學(xué)校。”因此,維新派努力經(jīng)營(yíng)《時(shí)務(wù)報(bào)》,以充分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觀念,此外,還大量創(chuàng)辦學(xué)會(huì)和學(xué)堂,將報(bào)刊視為擴(kuò)音機(jī)和傳聲筒,充分發(fā)揮其政治功能,以延伸社會(huì)公共討論。
受到《時(shí)務(wù)報(bào)》的熏陶和影響,全國(guó)各地陸續(xù)成立了大量報(bào)館、學(xué)會(huì)和學(xué)堂。湯志鈞《戊戌變法時(shí)的學(xué)會(huì)與報(bào)刊》一文中統(tǒng)計(jì),戊戌變法前的報(bào)刊有《中外紀(jì)聞》等35種,學(xué)會(huì)有強(qiáng)學(xué)會(huì)等44個(gè)。1895至1898年間,有大約60種報(bào)紙出現(xiàn),還出現(xiàn)了如格致書(shū)院等許多學(xué)堂,在擴(kuò)大變法影響、推動(dòng)改良運(yùn)動(dòng)的開(kāi)展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三種手段互相促進(jìn),形成了“三位一體”的互動(dòng)行為模式,進(jìn)而使“維新運(yùn)動(dòng),頓呈活躍之觀”。也就是說(shuō),“三位一體”模式培養(yǎng)了近代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參政議政的批判精神,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擴(kuò)展了變法圖強(qiáng)的公共輿論空間。《時(shí)務(wù)報(bào)》的創(chuàng)辦發(fā)行和風(fēng)靡全國(guó),標(biāo)志著近代中國(guó)“規(guī)模較小,但已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lǐng)域”的形成。④
《時(shí)務(wù)報(bào)》共發(fā)行兩年,出版66冊(cè),時(shí)間短,卷數(shù)少,但為社會(huì)公眾的思想交流與溝通提供了新的交往渠道和自由表達(dá)的公共平臺(tái),“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gè)人觀點(diǎn)集中起來(lái)并加以鼓吹,創(chuàng)造了類似于現(xiàn)代社會(huì)輿論的事物”,“這就是現(xiàn)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guó)的開(kāi)端。”⑤由于《時(shí)務(wù)報(bào)》的創(chuàng)辦和發(fā)行,近代中國(guó)媒介史上出現(xiàn)了結(jié)構(gòu)合理化和數(shù)
量規(guī)模化的良好輿論環(huán)境,近代中國(guó)變法維新的公共輿論空間暫時(shí)處于相對(duì)良好的狀態(tài)。
四、結(jié)語(yǔ)
1897年,由于張之洞橫加干預(yù),汪康年接任主筆,汪梁之間矛盾激化,梁?jiǎn)⒊瑧嵍o職,自第55期后,《時(shí)務(wù)報(bào)》上再無(wú)梁文。1898年8月8日,《時(shí)務(wù)報(bào)》停刊,共出69期。
由于甲午戰(zhàn)敗后中國(guó)歷史的特殊性,戊戌變法時(shí)期改良救國(guó)的新思想新理念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而維新派最重要的機(jī)關(guān)報(bào)《時(shí)務(wù)報(bào)》作為維新變法的輿論中心,擔(dān)負(fù)了很大的歷史和革命使命。《時(shí)務(wù)報(bào)》雖然出版時(shí)間較短,但態(tài)度鮮明,筆鋒犀利,呼吁改革,倡言變法,在晚清政治輿論場(chǎng)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外,《時(shí)務(wù)報(bào)》對(duì)西方先進(jìn)科學(xué)文化知識(shí)的引進(jìn)傳播,及其結(jié)合西方政治理論對(duì)啟發(fā)民智、變法圖強(qiáng)的大力呼吁,亦奏響了中國(guó)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最強(qiáng)音。
注釋:
①王栻.嚴(yán)復(fù)集[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6:491.
②上海圖書(shū)館.汪康年師友書(shū)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682.
③戈公振.中國(guó)報(bào)學(xué)史[M].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1955:123.
④許紀(jì)霖.近代中國(guó)的公共領(lǐng)域:形態(tài)、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J].史林,2003(02):77-89+123-124.
⑤[美]費(fèi)正清.劍橋中國(guó)晚清史(1800-1911):下卷[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5:379-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