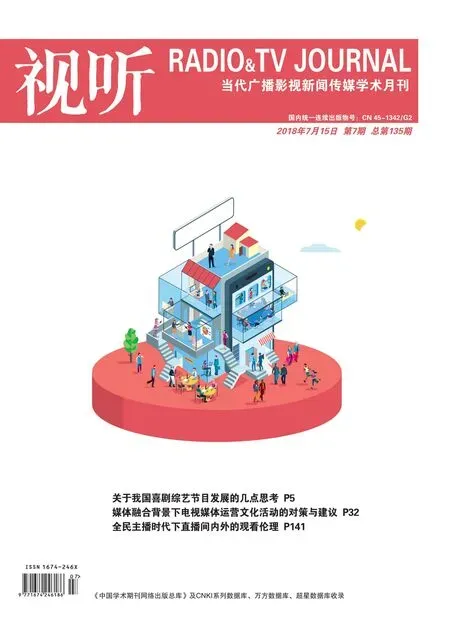新媒介環(huán)境下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的嬗變及其原因
□張雨曦
近年來,體育粉絲效應(yīng)在里約奧運(yùn)會(huì)后持續(xù)發(fā)酵,引起人們的空前關(guān)注。關(guān)于中國粉絲現(xiàn)象和粉絲文化,前人以娛樂界粉絲研究為主,對(duì)體育粉絲的研究相對(duì)較少且主要針對(duì)體育粉絲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中的問題、粉絲與網(wǎng)絡(luò)媒體的關(guān)系等內(nèi)容進(jìn)行研究,側(cè)重于現(xiàn)象分析,缺乏對(duì)原因的分析。故本文以里約奧運(yùn)會(huì)后的粉絲現(xiàn)象為例,對(duì)新媒介環(huán)境下,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的嬗變及出現(xiàn)其原因進(jìn)行研究。
一、粉絲文化與中國體育粉絲文化
粉絲是“fans”的音譯,丹尼斯·麥奎爾認(rèn)為粉絲是對(duì)媒介明星、演員、節(jié)目和文本極端投入的迷狂者。隨著工業(yè)時(shí)代的來臨,粉絲現(xiàn)象借助大眾傳播媒體,逐漸沉淀出今日的粉絲文化,成為大眾文化的組成部分。由粉絲的行為實(shí)踐、語言符號(hào)、行為規(guī)范、價(jià)值取向、文化文本等內(nèi)容組成的亞文化,被稱為粉絲文化。
中國的粉絲文化自改革開放后,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改革初期社會(huì)單向傳播的粉絲文化、生產(chǎn)方式變革影響下的粉絲文化和數(shù)字化新媒體傳播平臺(tái)上的粉絲文化。
中國體育粉絲文化在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隨著彩色電視在中國的普及,有了較為適宜的發(fā)展環(huán)境。央視轉(zhuǎn)播的1984年奧運(yùn)會(huì)在中國產(chǎn)生巨大效應(yīng),奧運(yùn)報(bào)道開始在中國受到重視,為體育粉絲的培育提供了土壤。之后在體育市場化和職業(yè)化的進(jìn)程中,隨著媒介環(huán)境的變化,體育粉絲群體的不斷壯大,體育粉絲文化日漸豐富。
二、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的嬗變
新媒介環(huán)境下,中國體育粉絲文化在崇拜對(duì)象特征、關(guān)注焦點(diǎn)、行為實(shí)踐方式等方面都發(fā)生了變化,并在里約奧運(yùn)會(huì)后,呈現(xiàn)出更豐富、更具象的特點(diǎn)。
(一)“粉”的對(duì)象,由冠軍偶像到多元偶像
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許海峰、李寧、中國女排等冠軍,是中國體育粉絲心中的偶像,這種崇拜包含著國家主義情懷,也包含勇敢拼搏的精神對(duì)個(gè)人的激勵(lì)。
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姚明、劉翔等人成為新一代偶像代表,他們既強(qiáng)調(diào)為國爭光,還憑借幽默表達(dá)或張揚(yáng)個(gè)性,更全面地詮釋著對(duì)體育的追求,在粉絲心中延展了體育的內(nèi)涵。里約奧運(yùn)會(huì)后,“洪荒少女”傅園慧、“不懂球的胖子”劉國梁等個(gè)性鮮明者都成了粉絲追捧的對(duì)象。另外,體育明星也頻頻現(xiàn)身綜藝,從體育健將轉(zhuǎn)變?yōu)槎嗝媾枷瘢Ψ蹮o數(shù)。
(二)粉絲關(guān)注焦點(diǎn),從關(guān)注比賽結(jié)果到對(duì)偶像的全面關(guān)注
偶像發(fā)揮如何曾是體育粉絲最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如今,產(chǎn)生了被熟悉體育項(xiàng)目和規(guī)則的粉絲戲謔地稱之為迷妹、親媽粉等的粉絲群體,比起比賽結(jié)果,他們可能更關(guān)心偶像的外形和個(gè)人生活,但他們的主動(dòng)性、參與性卻不比真體育迷差,場內(nèi)場外都是他們的身影。
還有一些粉絲熱衷于為偶像的終身大事考慮。球員帕托曾多次表白演員迪麗熱巴,粉絲們就為他在迪麗熱巴的微博下留言求回復(fù)。值得一提的還有“CP粉”。CP即人物配對(duì)關(guān)系(CharacterPairing)。“CP粉”傾向于將兩個(gè)人想象成親密關(guān)系。里約奧運(yùn)會(huì)后,馬龍和張繼科就被迷妹們強(qiáng)行組了“CP”。
(三)粉絲行為實(shí)踐,由單向接受信息到線上線下全面互動(dòng)
在報(bào)紙、廣播、電視作為主要傳播媒介時(shí),處于社會(huì)單向傳播中的體育粉絲的行為實(shí)踐多為關(guān)注媒介呈現(xiàn)的賽事,具有一定消費(fèi)能力的粉絲則會(huì)通過購買球票和裝備等行為來支持偶像,雖然有了短信互動(dòng)的方式,但這種互動(dòng)在參與度、便利性等方面都和今日無法比擬。
在新媒介環(huán)境下,除了傳統(tǒng)追星方式,粉絲還可通過微博、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tái)等線上渠道與偶像和粉絲互動(dòng)。粉絲群體為偶像包看臺(tái)、買版面、直播打賞等多種應(yīng)援方式,催生了體育粉絲經(jīng)濟(jì)熱潮,出現(xiàn)了傅園慧的網(wǎng)絡(luò)直播圍觀粉絲超過1000萬、粉絲為張繼科慶生耗資百萬、寧澤濤粉絲包場等現(xiàn)象。
三、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發(fā)生嬗變的原因
在新媒介環(huán)境下,新媒介技術(shù)帶來的實(shí)時(shí)性和互動(dòng)性、中國體育傳播話語體系的變遷、粉絲對(duì)自我認(rèn)同與群體認(rèn)同的追求成為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現(xiàn)象發(fā)生嬗變的主要原因。
(一)新媒介技術(shù)帶來的實(shí)時(shí)性和互動(dòng)性,為粉絲行為實(shí)踐提供支持
新媒介技術(shù)在體育傳播領(lǐng)域的廣泛應(yīng)用,使體育賽事得以全方位呈現(xiàn),尼爾森數(shù)據(jù)顯示,網(wǎng)絡(luò)、手機(jī)等新媒體已成為中國體育粉絲獲取賽事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新媒介因其交互性和即時(shí)性等特點(diǎn),為粉絲的行為實(shí)踐提供支持。“粉絲是所有媒介技術(shù)的先行實(shí)踐者”,亨利·詹金斯的觀點(diǎn)同樣體現(xiàn)了二者的親密性。
首先,新媒介環(huán)境為體育粉絲提供了海量信息,粉絲可以主動(dòng)找到興趣點(diǎn),隨時(shí)關(guān)注偶像動(dòng)態(tài);其次,新媒介技術(shù)尤其是社交媒介和移動(dòng)終端的發(fā)展,為體育粉絲提供了豐富的互動(dòng)渠道和即時(shí)性的互動(dòng)方式;第三,新媒介環(huán)境為粉絲的迅速動(dòng)員集聚和社群的壯大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形成組織有序、分工明確的體育粉絲群體。
(二)中國體育傳播話語體系的變遷,影響著粉絲的體育價(jià)值觀
中國體育傳播的話語體系與中國體育發(fā)展的歷史階段息息相關(guān)。20世紀(jì)末,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和體育產(chǎn)業(yè)化等因素,使得單一的革命話語和民族國家話語演變?yōu)槎嘣捳Z,民族國家話語、體育專業(yè)主義話語、消費(fèi)主義和娛樂主義話語等共同構(gòu)成了復(fù)雜多元的體育傳播話語。
新媒介環(huán)境為多元話語體系的形成提供了支持。新媒介環(huán)境下,公眾更熱衷于自由表達(dá),粉絲的體育價(jià)值觀也在多元話語體系中得以形成或重塑。這充分體現(xiàn)了時(shí)代在變,話語體系在變,粉絲的思維方式、價(jià)值觀念和文本解讀方式也在改變。
(三)追求自我認(rèn)同與群體認(rèn)同,促使體育粉絲積極投身粉絲活動(dòng)
新媒介環(huán)境下,信息爆炸帶來的信息焦慮和群體性孤獨(dú),使人們既缺乏安全感又渴望建立親密關(guān)系。根據(jù)“使用與滿足”理論,從體育粉絲的個(gè)體需求來看,追求自我認(rèn)同和群體認(rèn)同是他們投身粉絲活動(dòng)的內(nèi)在動(dòng)因。
追求自我認(rèn)同體現(xiàn)在兩方面。首先,體育粉絲追星是將自己的思想、情感等投射到偶像身上,追星是在追求“理想的我”的過程。其次,粉絲之間通過組團(tuán)應(yīng)援等方式,容易獲得他人對(duì)自己的肯定,從而實(shí)現(xiàn)自我認(rèn)同。正如“鏡中我”理論,人們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是在與他人的互動(dòng)中形成的。
群體認(rèn)同對(duì)粉絲來說同樣重要。通過對(duì)同一偶像的支持,背景各異的粉絲緊密相連,新媒介環(huán)境加速了粉絲聚集的過程和粉絲群體的組織化進(jìn)程。粉絲不再是孤軍奮戰(zhàn),他們的思想和情感趨同,擁有共同的意義符號(hào)、組織紀(jì)律,進(jìn)而獲得群體歸屬感,群體認(rèn)同也在粉絲活動(dòng)中強(qiáng)化。
四、結(jié)語
中國體育粉絲文化經(jīng)歷了粉絲崇拜對(duì)象由冠軍偶像到多元偶像的變化,粉絲關(guān)注焦點(diǎn)由關(guān)注比賽結(jié)果到對(duì)偶像全面關(guān)注的變化,粉絲的行為實(shí)踐由單向接受信息到線上線下全面互動(dòng)的變化。這與新媒介技術(shù)帶來的實(shí)時(shí)性和互動(dòng)性、中國體育傳播話語體系的變遷、粉絲對(duì)自我認(rèn)同與群體認(rèn)同密切相關(guān)。
體育粉絲效應(yīng)必然會(huì)加大社會(huì)對(duì)體育發(fā)展的關(guān)注,但體育明星畢竟有別于娛樂明星,相對(duì)于人氣熱度,如何保持競技狀態(tài)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而媒體的過度曝光和粉絲的過度關(guān)注并不利于運(yùn)動(dòng)員的發(fā)展。首先體育部門和媒體需引導(dǎo)粉絲理性追星,媒體在報(bào)道中要體現(xiàn)職業(yè)素養(yǎng),體育運(yùn)動(dòng)員自身更要避免過度娛樂化,莫使運(yùn)動(dòng)潛能淹沒于資本狂潮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