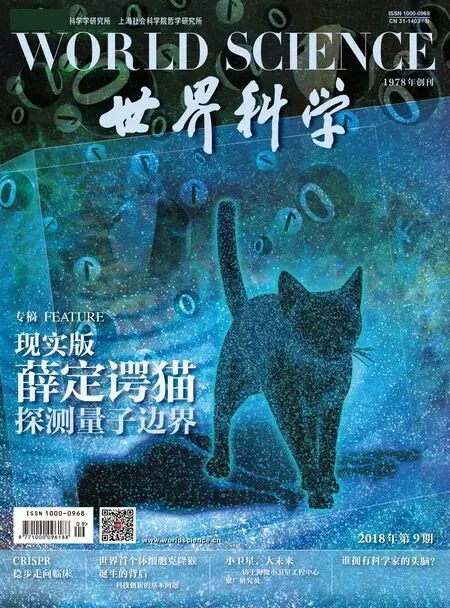我們已經(jīng)生活在虛擬現(xiàn)實里嗎?
編譯 費文緒
虛擬化身技術挑戰(zhàn)了我們對自己是誰和是什么的認知,請看《紐約客》編輯喬舒亞·羅思曼(Joshua Rothman)帶來的報道。
緣起
托馬斯·梅青格爾(Thomas Metzinger)19歲時,第一次有了“靈魂出竅體驗”。那時,他在德國法蘭克福自己家附近的韋斯特瓦爾德山區(qū)進行為期10個星期的禪修。經(jīng)過漫長一天的瑜伽和冥想修煉后,他吃了一片蛋糕后入睡了。等他醒來時,感覺到后背發(fā)癢。他想撓癢卻做不到,因為他的手臂似乎癱瘓了。他想強迫手臂移動,卻使自己升起,脫離軀體,這樣他就似乎在自己的身體上方漂浮。從身體之外凝視著房間里面,他感到既驚訝又害怕。他聽到另一個人驚慌地呼吸,環(huán)顧四周尋找入侵者。直到過了很久之后,他才意識到這個呼吸聲來自于他自己。
梅青格爾開始閱讀關于靈魂出竅體驗的資料。他了解到,8%~15%的人有過靈魂出竅體驗——可能是在夜里,或是手術之后。2003年,他認識了瑞士神經(jīng)科學家奧拉夫·布蘭克(Olaf Blanke),布蘭克學會了在人們完全清醒的狀態(tài)下如何使人體驗靈魂出竅。在治療一位43歲的女性癲癇患者時,布蘭克在她大腦的特定區(qū)域通了電流,使她體驗到向上漂浮、俯視自己身體的感覺。布蘭克發(fā)現(xiàn)了很多相關的幻覺。刺激大腦的另一個區(qū)域,則讓人產(chǎn)生活的分身站在房間對面的印象。刺激大腦的第三個區(qū)域,則會讓人產(chǎn)生“存在感”——感覺到某人在看不見的附近徘徊。不確定如何闡釋這些結果,布蘭克檢索了文獻,查到了梅青格爾寫的一些論文,這些論文從心理模型的觀點得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梅青格爾在論文中寫道,我們不只是生活在一個關于外部世界的心理模型里面,也生活在關于我們自己的身體、心靈和自我的心理模型里面。這些“自我模型”(self-models)并不總是反映現(xiàn)實,也可能以不合邏輯的方式進行調(diào)整。比如,這些模型可以描繪存在于身體之外的自我——靈魂出竅體驗。
梅青格爾和布蘭克開始著手破解自我模型。他們同認知科學家比格納·倫根哈格(Bigna Lenggenhager)和泰杰·塔迪(Tej Tadi)一起,創(chuàng)造了一個虛擬現(xiàn)實系統(tǒng),用來誘導類似靈魂出竅體驗的事件。2005年,梅青格爾戴上一個虛擬現(xiàn)實頭盔——頭盔帶有與眼睛相配的兩塊屏幕,會一起產(chǎn)生3D世界的幻覺。在屏幕里面,他看見自己的身體站在房間里,遠遠面對著自己。當他觀看著屏幕中自己的身體時,倫根哈格敲打了這個身體的背部;梅青格爾能感覺到敲打,但是承受敲打的身體似乎站在他面前。他感到一種奇特的激動,仿佛他正在太空中漂浮,或是在兩個身體之間被拉扯。他想完全跳到他面前的這個身體里,但是不能。他似乎被放逐到他自己身體之外。這不完全是靈魂出竅體驗,但是證明了:利用計算機技術,能夠輕而易舉地操縱自我模型。由此,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誕生了:虛擬化身(virtual embodiment)。
虛擬化身的目標
從2010到2015年,虛擬現(xiàn)實研究者梅爾·斯萊特(Mel Slater)和馬維·桑切斯-比韋斯(Mavi Sanchez-Vives)同梅青格爾和布蘭克在一個14方參與的歐盟資助項目“虛擬化身和機器人再化身”中合作。他們的實驗室位于西班牙巴塞羅那,運用沉浸式虛擬現(xiàn)實技術來操縱研究對象的身體模型,讓他們相信他們在虛擬現(xiàn)實中占有的身體是他們自己的。(斯萊特和桑切斯-比韋斯是一對夫妻,他們在2001年的一次虛擬現(xiàn)實研討會上相遇。)桑切斯-比韋斯說:“我們有一種錯覺,覺得我們的身體模型非常穩(wěn)定,但那只是因為我們從未遇到過其他模型。”那些對自己的身體意識感極強的人——比如舞者、運動員、瑜伽修行者,會發(fā)現(xiàn)很難接納一個虛擬的身體,因為他們很難“放任自己的身體”。“但是你練習得越多,就變得越容易。當你體驗過一次兩次之后,你會豁然開朗。”過去幾年來,斯萊特、桑切斯-比韋斯和其他的虛擬化身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了這項技術的治療和教育用途。與此同時,梅青格爾和哲學家邁克爾·毛道里(Michael Madary)已經(jīng)一起起草了聚焦虛擬化身的虛擬現(xiàn)實“倫理準則”,梅青格爾相信虛擬化身使得虛擬現(xiàn)實在根本上區(qū)別于其他所有媒介。這兩位哲學家寫道,化身的虛擬體驗能深刻改變我們,能以我們幾乎不理解的方式影響我們,重新定義“我們同自己的心靈之間的關系”。
虛擬化身則有一個不同的目標:讓你相信你是另一個人。這不需要高級的繪圖,而是需要跟蹤硬件和在虛擬的鏡子面前進行幾分鐘有引導的類似太極的運動;跟蹤硬件讓你的虛擬身體準確映射你真實的頭部和手足的運動。在巴塞羅那大學斯萊特的實驗室,我戴上一個虛擬現(xiàn)實頭盔,注視著一面虛擬的鏡子,看見一個身穿牛仔褲、T恤和芭蕾舞平底鞋的年輕女子的身體。當我移動時,她也移動。
“你將會看到很多漂浮的球,你得去觸碰它們。”軟件開發(fā)者吉列爾莫·伊魯雷塔戈耶納(Guillermo Iruretagoyena)說。一些彩色的球出現(xiàn)在我的手和腳附近,我移動我的四肢去觸碰它們。這些球消失了,又有新的球代替它們。當我觸碰新的球之后,伊魯雷塔戈耶納解釋說,“化身階段”已經(jīng)完成——我已經(jīng)欺騙我的大腦認為虛擬的四肢是我自己的。我并沒有感覺到我的虛擬自我特別真實。虛擬世界的質(zhì)量可以和20世紀90年代的視頻游戲相提并論,當我靠近鏡子,與我自己進行眼神接觸時,我發(fā)現(xiàn)鏡子中我的臉是平面的卡通化的,就像吸血鬼一樣,我的身體并沒有影子。
虛擬化身的奇妙應用
自從2011年以來,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qū)政府與斯萊特的實驗室合作,將這種模擬技術用于男性施虐者的改造計劃。心理學家索菲婭·塞恩菲爾德(Sofia Seinfeld)在桑切斯-比韋斯的實驗室開展了一項控制研究,其研究結果最近發(fā)表于 《自然》子刊 《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上。該研究中,在面對女性時,體驗過這種模擬的男性更明顯感到害怕(家庭暴力施虐者往往缺乏對女性的害怕)。過去3年來,作為一個規(guī)模更大的改造計劃的一部分,有數(shù)百位男性施虐者在實驗室之外體驗了這種模擬。因為樣本量很小,桑切斯-比韋斯和斯萊特猶豫是否要發(fā)表模擬實驗的初步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體驗過這種模擬的男性實施家暴的再犯率降低了。一名男性回憶自己接受模擬實驗的體驗時說:“我感覺變成了我的前妻。”另一名參加實驗的男性說:“我以為丈夫要打我,所以我用一只手擋住我的臉。”只是看過視頻或是體驗虛擬現(xiàn)實模擬卻沒有經(jīng)歷化身過程的男性,則較少報告這種領悟。
斯萊特是一個身材纖細、說話溫柔的英國男人,他帶我走進巴塞羅那大學校園的咖啡吧。我們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前坐下,他試圖向我解釋虛擬化身這項技術如何會導致這樣的改變。他說:“沒有人真正理解這項技術是什么和如何使用這項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大腦并不知道真實現(xiàn)實和虛擬現(xiàn)實之間的差別。”
斯萊特和桑切斯-比韋斯與各種合作者組成研究團隊,創(chuàng)造了很多其他身體的模擬實驗;他們表明,心靈棲息于一個新的虛擬身體中,可以產(chǎn)生有意義的心理學轉變。在一項研究中,實驗參與者作為小女孩重新化身,她們被毛絨熊、搖搖馬和其他玩具包圍,看著她們的母親嚴格要求她們保持房間干凈。之后,在心理學測試中,她們具有更多孩子的特點。在另一項研究中,在虛擬的黑人體內(nèi),白人參與者用大約10分鐘學習太極。之后,他們在一項專門測試中的得分顯示,他們的無意識種族偏見發(fā)生了顯著改變。“這些影響產(chǎn)生得很快,而且似乎會持續(xù)。”斯萊特說。一個星期后,白人參與者仍然具有較少的種族主義態(tài)度。種族偏見的研究結果在巴塞羅那的實驗中多次重復,在倫敦的第二個研究組開展的實驗中也可以重復。化身模擬似乎滑到認知的閾值之下,影響到思維的聯(lián)想和無意識部分。斯萊特說:“這是直接的實驗,這不是‘我知道’,而是‘我是’。”
斯萊特設想了通過虛擬化身的健康甚至極樂的學習方式。他說:“想象一下,如果你害怕公眾演講,現(xiàn)在你能化身為著名女演員安吉麗娜·朱莉,在成千上萬為你喝彩的人們面前發(fā)表演講。”2015年,在巴塞羅那當代文化中心舉辦的一場藝術展覽中,斯萊特的研究團隊搭建了一個虛擬現(xiàn)實體驗展臺。在虛擬現(xiàn)實中,參與者一起生活在迷幻的熱帶島嶼上,化身為優(yōu)雅的類人生物,讓人想起電影《阿凡達》中藍色的納美人。在一個半小時的體驗過程中,參與者的虛擬身體衰老而死;死后,參與者在閃回中回顧他們的虛擬人生,然后向上漂浮到一個白光隧道中。當他們摘下頭盔,他們看著屏幕上的島嶼同胞在為他們建造紀念碑。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對人生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斯萊特的實驗室正在研究虛擬死亡是否會產(chǎn)生類似的效果。他說:“我們過去努力想實驗這個隱晦的想法,那就是存在不朽,而此生是一個虛擬的人生——仿佛我們死后,我們只不過是摘下體驗虛擬現(xiàn)實的頭盔,實際上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虛擬的靈魂出竅體驗
在到達巴塞羅那之前,我問過斯萊特和桑切斯-比韋斯,我是否可以嘗試一下虛擬的靈魂出竅體驗。那天晚些時候,在實驗室的另一個部分,我坐在一把椅子上,3位研究者——皮埃爾·布爾丹(Pierre Bourdin),伊特薩索·巴韋里亞(Itsaso Barberia)和拉蒙·奧利瓦(Ramon Oliva)把小型振動電機戴到我的手腕和腳踝上。在虛擬現(xiàn)實頭盔里面,我看見了一個虛擬的房間,有一張咖啡桌,還有一個點著火的壁爐。在我面前的虛擬鏡子中,我看見了一個不安的形象:一個穿著黑色尼龍搭扣西裝的男人,他的眼睛藏在一個黑色的虛擬現(xiàn)實頭盔后面。這就是我,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中的我。
布爾丹說:“你將會在咖啡桌上看見一些圖形,用你的腳追蹤它們。”
我聽到電腦鼠標的點擊聲。像象形文字一樣的圖形出現(xiàn)在桌子上,我用腳追蹤它們。
奧利瓦說:“接下來,你將會看見一些彈跳起來的球。”鼠標點擊,然后藍色的小球開始在我的身體周圍跳舞。多虧振動電機,我感覺到了它們,當它們碰到我時,感覺很輕很軟。
“試試移動你的手臂和腿。”奧利瓦說。我照做了,然后小球跟著我的動作在運動。
有那么幾分鐘,我坐著享受我周圍奇怪的事物。然后,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我的視點開始移動,我正在往后退,脫離出我自己。首先,我看見了我的后腦勺,然后從我的背后看見了我的身體。我開始向天花板漂浮,從天花板上,我俯視著坐在椅子上的自己的身體,被旋轉的小球包圍。我的內(nèi)心完全靜默,沒有任何想法能夠等同于這種體驗。我并沒有感覺到我已經(jīng)離開了我的身體;我只是感覺到我的身體離開了我。當我摘下頭盔,斯萊特和布爾丹正看著我。“如何?”斯萊特問。
“我不知道。”我說。
“你感覺如何?”布爾丹問。
“不可思議。”我說。
“有些人會有非常強烈的體驗。”布爾丹說。
“有人會大喊大叫。有人會抓住椅子。”他停頓了一下說,“我認為這種體驗讓你產(chǎn)生一個隱含的想法,那就是你能把你的身體和你的靈魂分離。這大概就是死亡的恐懼。”
我贊同地點點頭,搖晃著手中的頭盔。
他山之石
在法蘭克福,在一家波斯餐館吃過午飯后,我向梅青格爾描述了我的虛擬體驗。我想知道這種虛擬體驗是否真實。我在虛擬現(xiàn)實中的靈魂出竅體驗是真實的體驗嗎?那么,在虛擬現(xiàn)實中觸碰外套的感覺呢?是真實的嗎?
“當真實這個詞有意義時,這是一個宏大的問題,”梅青格爾說,他皺了皺眉,“一種有趣的可能性是真實與不真實之間的區(qū)別被誤導了。”他打手勢指向桌上的蠟燭火焰。“在佛教形而上學中,有所謂‘空’的觀念。實現(xiàn)事物的空意味著‘既不是真實也不是不存在。’我們感知到的蠟燭指的是真實世界的真實事物。但是這個蠟燭——我們看見的這個,是心理內(nèi)容。不過,如果說我們心中的模型、體驗是不真實的,這也是不對的。模型和體驗是‘空’。按照他們的說法,‘空’也許只是一個虛擬模型,‘空虛’可能是‘虛擬’。”
我一邊聽著,一邊用手指摩擦著我的外套。我的外套是真實的,就像我的手指一樣真實。但是,我的手指之間對外套的準確感覺,在我的心里卻是既可靠又朦朧,也許這就是空。
梅青格爾點了波斯咖啡,服務員用一個華美的銀色盤子端給我們。在小巧的優(yōu)雅的咖啡杯之間——咖啡幾乎從杯子里漫出來了——是撒上糖的棗。我們的女服務員用德語告訴我們怎么喝咖啡。“非常感謝,”梅青格爾也用德語跟女服務員說,然后解釋給我聽,“她說吃一顆棗,再呷一口咖啡,因為這樣可以讓苦澀與甜蜜形成鮮明對比。”我嘗了一顆棗,從我的手指上拂去糖,然后啜飲我的咖啡。女服務員說得很對,的確如此。
天色向晚,我們走出波斯餐館,去公園里散步。當我們漫步時,梅青格爾好奇,虛擬現(xiàn)實通過改變我們對自己的體驗,將會如何影響宗教和藝術。“你能體驗到把自己看作空的感覺嗎?”他問,“在空的世界里,沒有自我——沒有控制?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狀態(tài)往往有開始和結束。”一個微笑打破了他嚴肅的表情。他繼而哈哈大笑說:“你知道,斯萊特的實驗室最酷的事情是——我坐在虛擬現(xiàn)實的一個房間里。那里有燃燒的爐火和一面大鏡子。他們還沒有打開虛擬化身的開關。然后我俯視下面,發(fā)現(xiàn)沒有軀體,椅子是空的。我喜歡這種感覺!”
公園靜謐而美麗。昨夜下過雨,沙礫小徑濕漉漉的。落日低垂,我們的腳步碾過沙礫。一個小男孩騎著自行車碾過一個水坑;我們聽到濺起的水聲。我感到疲憊又興奮——腦海中充滿了想法。天空湛藍,草坪翠綠。
資料來源 The New 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