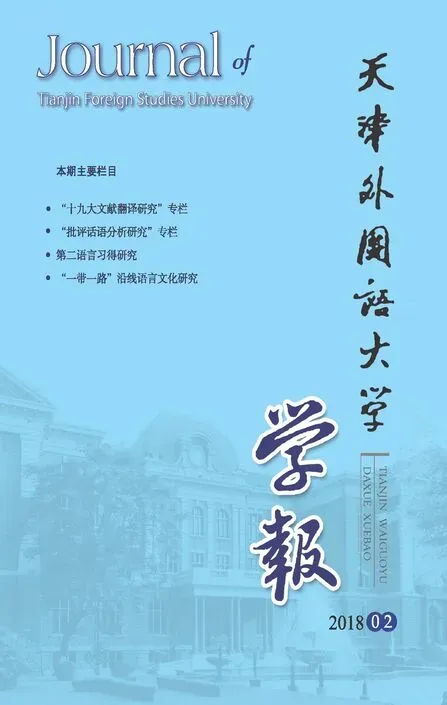詞匯習得模式對ESL詞匯知識習得的影響研究
成利軍
?
詞匯習得模式對ESL詞匯知識習得的影響研究
成利軍
(安陽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安陽 455000)
以英語專業三年級學生為被試,通過實證研究考察了詞匯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關系以及詞匯知識之間的差異性和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傳統習得模式能夠顯著地預測和解釋習得者的接受性詞匯知識,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更能夠顯著地預測和解釋習得者的產出性詞匯知識;在傳統習得模式下接受性詞匯知識與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英語專業學生宜通過傳統習得模式習得接受性詞匯知識,通過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習得產出性詞匯知識。
詞匯習得模式;接受性詞匯知識;產出性詞匯知識
一、引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詞匯知識及其習得模式已經從一個被忽視的領域(Meara,1980)發展成為二語習得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Henriksen,1999;Nation,2011;Cook & Singleton,2014)。我國雖有全球最大的英語學習群體(張勇先,2014:5),但是英語學習的效費比依然很低,尤其是在詞匯習得方面,“學習者花費大量時間學習英語詞匯,但真正掌握并靈活運用的詞匯少之又少”(于涵靜、戴煒棟,2016:52)。這一方面是因為習得者的詞匯習得模式不正確,尤其是忽略了情景語境在詞匯知識習得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習得者所習得詞匯知識的單維性、片面性也是原因之一。鑒于此,本文首先對詞匯知識進行了重新界定,然后通過對比傳統習得模式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詞匯知識的不同影響來探討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關系,進而闡釋這兩種習得模式各自的優劣所在,以期為ESL詞匯教學提供某種啟示。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詞匯知識是衡量ESL學習者語言水平高低的標志之一(St?hr,2009:577)。它是二語習得的基礎和關鍵(王立非、江進林,2012:6),貫穿語言習得的整個過程,是聽(Wen,2014;Wang & Treffers-Daller,2017)、說(Koizumi & In’nami,2013;張曉東,2015)、讀(Qian,2002;Li & Kirby,2015)、寫(Baba,2009;Shi & Qian,2012;Johnson,Acevedo & Mercado,2016)、譯(于涵靜、戴煒棟,2016)等各項語言技能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成利軍,2017)發展的基石,影響著語言輸出的準確性、得體性和流利性。因此,詞匯知識的學習是二語習得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Bao,2015:84)。

表1 多維詞匯知識框架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ESL詞匯知識的習得一般分為詞匯附帶習得(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和詞匯有意習得(intentional vocabulary learning)兩種模式(Hulstijn,2003)。詞匯附帶習得(Laufer & Hulstijn,2001;苗麗霞,2014)是指習得者在進行讀或者聽(視聽)等語言輸入的過程中無意識地、附帶地習得詞匯,被認為是二語詞匯習得的主要途徑(Gass,1999)。但是,詞匯有意習得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習得模式,尤其是對ESL習得者來說(Hulstijn,2003)。詞匯有意習得是指學習者主動地、有意識地、專門地學習詞匯。
在借鑒以上觀點的基礎上,本研究將詞匯有意習得模式具體界定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習得模式(rote memorization,RM),主要是通過識記英文詞匯的常用義項的中文釋義以及固定搭配來習得;另外一種則是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situational contextualization vocabulary acquisition,SCVA),該模式不僅要求識記詞匯的中文釋義,還須理解該詞匯的英文釋義,最重要的是要將該詞匯置于真實的、具體的情景語境中來進一步識記、理解、習得該詞匯的全部五個維度的詞匯知識。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是指話語發生時的即時場景,包括時空位置(spatial-temporal location)、參與者(participants)、話題(subject matter)以及相關文化信息等(朱永生,2005),其載體可以是來自真實語料的文本、圖片或視頻片段。
國內外對詞匯習得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附帶習得的研究,而關于詞匯知識則多是探討其內涵,以及它對語言技能、語言綜合能力的作用這些方面(成利軍,2017)。Zhang和Lu(2015)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了詞匯習得策略(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與詞匯知識之間的關系。但是到目前為止,很少有研究從宏觀的角度考察詞匯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關系。鑒于此,本研究通過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探討詞匯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是否具有線性回歸關系,進而分析傳統習得模式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兩個維度詞匯知識的影響和作用機制,以期為英語專業ESL詞匯教學提出針對性建議。具體研究問題為(1)傳統習得模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具有怎樣的解釋力和預測力?(2)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具有怎樣的解釋力和預測力?(3)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是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4)英語專業學生應采用何種模式習得詞匯知識?
三、研究設計
1 研究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為河南某高校英語專業三年級兩個平行班的64名學生。被試的英語專業四級考試成績(2016年4月)的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兩個班的成績無顯著差異(t=1.228,df=62,p>0.05),因此可以認為兩個班被試的英語水平在整體上沒有明顯差別。被試分為控制班和實驗班,各32人。兩個班均由筆者執教,使用相同的教材,控制班詞匯教學采用傳統習得模式,而實驗班則采用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實驗從三年級第一學期第二周開始,共16周。實驗期間,被試須要習得十個單元的500個單詞。
2 測試工具
本研究由前測、后測和訪談三部分組成。前測、后測均由接受性詞匯知識測試和產出性詞匯知識測試兩部分組成。接受性詞匯知識測試借鑒了Nation和Belgar(2007)的詞匯量測試量表Vocabulary Size Test(VST)中的題型。測試采用多項選擇題型,從500個單詞中隨機抽取200個作為測試單詞,每個單詞構成一道題,共200道題。被試答對一道得0.5分,答錯得0分,滿分100分。以stealth為例,以下是測試題型。
STEALTH: They did it by stealth.
a. spending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為使配電網自動化系統運行效率得以提升,不但要保障配電網常態運行時,自動化系統可精確、高效地將電能輸送給用戶為一,還需保障當配電網處于故障狀態時,自動化系統依然能第一時間處置故障問題,加強修復力度,進而使供電的安全性得以增強。
b. hurting someone so much that they agreed to their demands
c. moving secretly with extreme care and quietness
d. taking no notice of problems they met
產出性詞匯知識測試借鑒了Laufer和Nation(1995)的Lexical Frequency Profile, Meara和Fitzpatrick(2000)的Lex30以及王新朋等(2017)編制的多維詞匯知識測試卷中的產出性詞匯知識測試題。這些測試量表雖各有特點,但其共同的不足之處在于,這些量表僅能測試產出性詞匯知識的一部分(Schimitt,2014:922)。測試題型有單詞朗讀(5分)、短文聽寫(15分)、根據語義聯系或句法搭配填詞(15分)、近義詞語用辨析(15分)、單詞情景語境化造句(15分)、情景語境化漢譯英(15分)和寫作(20分)共七種,總分為100分。試卷經試測、修改之后最終確定。測試數據錄入SPSS19.0進行信度檢驗,結果顯示試卷各部分的內在一致性信度系數Cronbach’s Alpha取值處于0.72~0.83之間,均高于0.70的信度接受標準(秦曉晴,2003:76-77)。試卷的效度檢驗主要是從內容和結構兩方面展開,對試卷進行的研究者自評、專家評價、被試的評價(秦曉晴,2009:224)以及隨后的修改確保了較高的內容效度。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KMO統計量為0.721,大于最低標準0.5(武松、潘發明,2014:342);Bartlett球形檢驗拒絕單位相關陣的原假設,P<0.05,這都說明試卷也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訪談在測試后的一周之內完成。以測試成績的五個分數段(優、良、中、及格和不及格)為依據,每個班都隨機從每個分數段抽取三名被試,每個班15名,共30名。為使被試能夠清晰、準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避免因語言表達問題影響訪談的有效性,訪談全部使用漢語。
3 研究步驟
前測和后測均隨堂進行。前測安排在三年級第一學期實驗開始之前進行,后測則安排在期末進行。接受性詞匯知識測試和產出性詞匯知識測試的時間分別為60分和120分鐘。測試結果用SPSS19.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分析,輸出結果包括描述性統計、回歸分析、t檢驗以及相關性分析等數據。
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1 傳統習得模式對詞匯知識的影響和作用機制
控制班的后測成績(見表2)顯示,預測變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R方為0.801,即傳統習得模式能夠解釋接受性詞匯知識80.1%的變異;與此相比,預測變量對產出性詞匯知識雖然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R方為0.467),但其明顯低于對接受性詞匯知識的預測力,只能解釋46.7%的變異。這說明,對于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傳統習得模式在習得接受性詞匯知識方面更有優勢。

表2 傳統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模型匯總
對傳統習得模式和接受性詞匯知識、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分別進行的回歸分析(見表3)顯示,無論是回歸方程還是回歸系數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p<0.05),因此,我們可以在前者和后兩者之間分別建立一個回歸方程。傳統習得模式和接受性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方程為接受性詞匯知識=28.256+0.834×傳統習得模式,而傳統習得模式和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方程為產出性詞匯知識=26.544+0.636×傳統習得模式。從兩個方程的回歸系數(0.834>0.636)同樣可以看出傳統習得模式更有利于接受性詞匯知識的習得。
表3 傳統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線性回歸關系

由于英語專業的精讀教材基本上沒有給生詞提供相關詞匯知識,學生就主要通過詞典等工具來習得詞匯的簡短的中文釋義、詞性、常見固定搭配等知識。筆者不領讀學生朗讀單詞,其發音主要由學生基于自己的語音知識掌握。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簡便、省時,因此學生沒有動機,也沒有壓力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單詞在真實情景語境中的相關詞匯知識,而只愿意掌握詞匯的基本知識和用法。由于這些主客觀原因,控制班學生對接受性詞匯知識的習得效果顯著優于產出性詞匯知識。
2 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詞匯知識的影響和作用機制
從結果來看(見表4),在實驗班詞匯教學中所采用的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接受性和產出性兩種詞匯知識都有較高的預測作用,對接受性詞匯知識的決定系數R方為0.551,對產出性詞匯的決定系數則達到0.821。與傳統習得模式相比,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兩種詞匯知識的習得有著相對均衡的促進作用。

表4 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回歸模型匯總
從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看,兩者的回歸方程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p均為0.000,都小于0.05。接受性詞匯知識的回歸系數t檢驗表明回歸方程的常量和回歸系數都具有顯著性,故我們可以建立回歸方程:接受性詞匯知識=25.261+0.711×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產出性詞匯知識回歸系數t檢驗表明回歸方程的常量和回歸系數同樣都具有顯著性,故我們也可以建立回歸方程:產出性詞匯知識=21.517+1.004×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
表5 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線性回歸關系

總的來看,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的習得都有明顯的、相對較均衡的促進最用(R方接受性=0.551,R方產出性=0.821),但是對產出性詞匯知識的習得有更為明顯的促進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在應用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的過程中,被試首先要理解單詞的含有語用信息的、詳細的英文釋義,然后識記相應的中文釋義,接下來要在語用信息或者語境信息豐富的例句中理解、識記該單詞,最后還要在來自真實語料的、含有豐富的語域知識、語體知識和感情色彩知識的情景語境中進一步理解、識記該詞的各方面詞匯知識。
3 不同詞匯習得模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的影響差異
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見表6)顯示,采用不同習得模式的控制班和實驗班學生的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之間有顯著差異(t=5.337,df=62,p<0.05),在傳統習得模式下學生的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顯著高于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下的學生成績(MD=9.969)。我們可以推斷除精讀課之外,其他專業課上所遇到的生詞,英語專業的學生都可以采用這一種模式:一是應試的需要,因為英語專業的專四、專八等標準化考試會考察學生大量的接受性詞匯知識;二是精讀課課時少的客觀條件限制,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則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學習時間和精力。

表6 采用不同習得模式學生的接受性詞匯知識差異
在對控制班15名學生的訪談中,有80%(12人)的學生反映采用傳統習得模式習得接受性詞匯知識的兩大優點是方便、省時,還有約87%(13人)的學生認為這種模式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了,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面臨詞匯知識考核的直接壓力,在他們的輸出任務中對產出性詞匯知識并無特別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可能也受到社會上英語學習大環境的影響,認為英語在我國只是一門外語,沒有必要學習地那么深入。
4 不同詞匯習得模式對產出性詞匯知識的影響差異
由表7可知,控制班和實驗班在產出性詞匯知識的成績上存在顯著性差異(t=-5.998,df=62,p<0.05),兩組平均值的差異為-11.813。這說明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在產出性詞匯習得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表7 采用不同習得模式學生的產出性詞匯知識差異
對實驗班15位學生的訪談結果也證實了該種模式的有效性。在這種習得模式下,約87%(13人)的學生認為,他們掌握的單詞比以前更加得準確,約73%(11人)的學生認為,他們對的單詞的應用比以前更加得體和流利,80%(12人)的學生認為,他們掌握的單詞比以前更加得牢固,80%(12人)的學生認為,他們掌握的單詞比以前更加得全面,約93%(14人)的學生認為他們掌握的單詞比以前更加得深入。但是,接受訪談的15位同學全部反映這種習得模式大大加重了他們的學習負擔和時間壓力,有時甚至需要犧牲其他專業課學習時間。
5 接受性詞匯知識與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的相關性
雖然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是兩個不同維度的詞匯知識,但從表8 控制班的Pearson 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兩個變量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 =0.582,p<0.05),也就是說,產出性詞匯成績隨著接受性詞匯成績的提高而提高,后者可以解釋前者成績的34%(r2=0.34)的方差,這與前人(Qian,2002;Schmitt,2014:914;Li & Kirby,2015:17)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表8 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的相關性
**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但是實驗班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表8)顯示,接受性詞匯知識與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并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146,p>0.05)。這表明在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下,產出性詞匯知識成績并不隨著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的提高而提高。這可能是因為二者之間的關系還取決于其他多種因素,比如,被試的詞匯量、測試詞的詞頻以及被試的母語水平等(Schmitt,2014:941)。
五、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考察了ESL詞匯的傳統習得模式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分別與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之間的線性回歸關系以及兩種詞匯知識之間的差異性和相關性。傳統習得模式能夠解釋和預測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80.1%的變異,對產出性詞匯知識成績的解釋量則為46.7%。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模式在接受性詞匯知識習得方面更有優勢。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對接受性詞匯知識和產出性詞匯知識成績均有顯著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能夠解釋前者55.1%的變異,對后者則有高達82.1%的解釋力。這說明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更有利于產出性詞匯知識的習得。控制班與實驗班兩個班的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之間(t=5.337,df=62,p<0.05)以及產出性詞匯知識成績之間(t=-5.998,df=62,p<0.05)均有顯著差異,且產出性詞匯成績之間的均值差(MD=11.813)高于接受性詞匯成績之間的均值差(MD=9.969)。這驗證了傳統習得模式更有利于接受性詞匯知識習得,而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則更有利于產出性詞匯知識習得。在傳統習得模式下,接受性詞匯知識成績和產出性詞匯知識成績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582)。但是在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下,兩種知識之間并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146),這說明二者之間的相關程度還取決于其他諸如被試的詞匯量、測試詞的詞頻以及被試的母語水平等多種因素(ibid.)。
本研究的結論對ESL詞匯教學亦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第一,教師既要重視學生對產出性詞匯知識的習得,又不忽視接受性詞匯知識的重要性;第二,在英語專業精讀課的詞匯教學過程中,宜采用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尤其是對那些低頻詞、高語境詞以及易混詞要以一定的頻次呈現在情景語境中;第三,在諸如泛讀、語言學等專業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宜采用傳統習得模式;第四,教師應不斷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知識、跨文化能力、跨文化態度以及跨文化意識,以有利于情景語境化習得模式下詞匯教學的順利實施(成利軍,2017)。
因條件所限,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產出性詞匯知識測試量表的信度、效度還需要進一步的提高;其次,研究被試的來源較為單一,可以考慮不同學校、不同地區的被試,以便更全面客觀地考查詞匯習得模式的作用及其適應性。本研究也沒有將情景語境化輸入頻次作為一個研究變量來考察頻次效應對ESL詞匯知識習得中的作用(崔靖靖、劉振前,2016),日后的研究可以在這方面展開。
[1] Baba, K. 2009. Aspects of Lexical Proficiency in Writing Summaries in a Foreign Language[J]., (18): 191-208.
[2] Bao, G. 2015. Task Type Effects o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J]., (53): 84-95.
[3] Cook, V. & D. Singleton. 2014.[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4] Corson, D. 1995.[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 Cronbach, L. 1942. An Analysis of Techniques for Diagnostic Vocabulary Testing[J]., (3): 206-217.
[6] Gass, S. 1999.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J]., (2): 319-333.
[7] Harrington, M. 2018.[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8] Henriksen, B. 1999. 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J]., (2): 303-317.
[9] Hulstijn, J. 2003. Incidental and Intentional Learning[A]. In C. Doughty. & M. Long (eds.)[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0] Johnson, M., A. Acevedo. & L. Mercado. 2016.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Vocabulary Use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J]., (3): 700-715.
[11] Koizumi, R & Y. In’nami. 2013.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Speaking Proficiency among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rom Novice to Intermediate Levels[J]., (5): 900-913.
[12] Laufer, B. & I. Nation. 1995. Vocabulary Size and Use: Lexical Richness in L2 Written Production[J]., (16): 307-322.
[13] Laufer, B., & J. Hulstijn. 2001.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nstruct of Task-induced Involvement[J]., (1): 1-26.
[14] Li, M. & J. Kirby. 2015. The Effects of Vocabulary Breadth and Depth on English Reading[J]., (5): 611-634.
[15] Meara, P. 1980.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Language Learning[J]., (3-4): 221-246.
[16] Meara, P. & T. Fitzpatrick. 2000. Lex30: An Improved Method of Assessing Productive Vocabulary in an L2[J]., (28): 19-30.
[17] Melka, F. 1997. Receptive vs Productive Aspects of Vocabulary[A]. In N. Schmitt & M. McCarthy. (ed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 Nation, I. 1987. What Is Involved in Learning a Word?[A].[C]. Nueva Zeland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19] Nation, I. 1990.[M]. New York: Newbury House.
[20] Nation, I. & D. Belgar. 2007. A Vocabulary Size Test[J]., (7): 9-13.
[21] Nation, I. 2011. Research into Practice: Vocabulary[J]., (4): 529-539.
[22] Nation, I. 2013.[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Qian, D. 1999. Assessing the Roles of Depth and Bread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J]., (2): 282-308.
[24] Qian, D. 2002.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Academic Reading[J]., (3): 513-536.
[25] Richards, J. 1976. The Role of Vocabulary Teaching[J]., (1): 77-89.
[26] Schmitt, N. 2014. Size and Dep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What the Research Shows[J]., (4): 913-951.
[27] Shi, L. & D. Qian. 2012. How Does Vocabulary Knowledge Affect Chinese EFL Learners’ Writing Quality in Web-based Settings?—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Writing Quality[J]., (1): 140-156.
[28] Stewart, J., A. Batty. & N. Bovee. 2012. Comparing Multidimensional and Continuum Models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Vocabulary Knowledge Scale[J]., (4): 695-721.
[29] St?hr, L. 2009.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Advance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J]., (4): 577-607.
[30] Wang, Y. & J. Treffers-Daller. 2017. Explain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mong L2 Learners of English: the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Metacognitive Awareness[J]., (65): 139-150.
[31] Wen, W. 2014. Assessing the Role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J]., (3): 358-372.
[32] Wesche, M & T. Paribakht. 1996. Assessing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Knowledge: Depth versus Breadth[J]., (1): 13-40.
[33] Zhang, X. & Lu Xiaofei.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Breadth and Dep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J]., (4): 740-753.
[34] 成利軍. 2017. EFL詞匯習得模式與詞匯知識之間的線性回歸分析[J]. 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 (4): 52-58.
[35] 崔靖靖, 劉振前. 2016. 輸入間隔與頻次對二語詞匯習得影響的微變化研究[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 56-61.
[36] 馬廣惠. 2007. 二語詞匯知識理論框架[J]. 外語與外語教學, (4): 22-24.
[37] 苗麗霞. 2014. 第二語言詞匯附帶習得研究30年述評[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1): 23-29.
[38] 秦曉晴. 2003. 外語教學研究中的定量數據分析[M].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39] 秦曉晴. 2009. 外語教學問卷調查法[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40] 王海華, 孫智. 2007. 詞匯知識框架與詞匯研究[J]. 外語教學, (3): 52-55.
[41] 王立非, 江進林. 2012. 國際二語習得研究十年熱點及趨勢的定量分析(2000-2009)[J]. 外語界, (6): 2-9.
[42] 王新朋, 孔文,王永祥. 2017. 輸出驅動對多維詞匯知識習得的影響研究[J]. 外語與外語教學, (1): 86-94.
[43] 武松, 潘發明. 2014. SPSS統計分析大全[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44] 于涵靜, 戴煒棟. 2016. 國外二語詞匯習得研究趨勢的可視化分析——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J]. 外語界, (5): 52-60.
[45] 張曉東. 2015. 詞匯量與產出性詞匯知識對二語口語的影響[J]. 外語界, (4): 34-41.
[46] 張勇先. 2014. 英語發展史[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47] 朱永生. 2005. 語境動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05-21;
2018-02-26
安陽工學院科研基金項目“語境化輸入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YJJ2015026)
成利軍,講師,研究方向:二語習得、英漢對比
H319.3
A
1008-665X(2018)2-01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