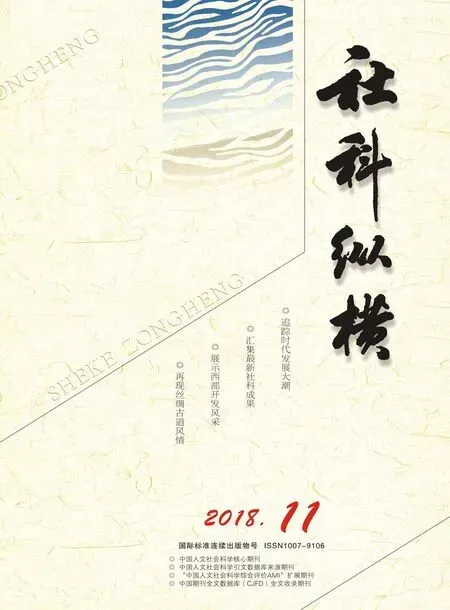論隋唐時期定西以優化農牧結構為主開發經濟
邵小芳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 甘肅 蘭州 730000)
隋唐時期,尤其唐太宗至唐玄宗年間,全國疆域擴大,經濟繁榮,相繼形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是中國歷史的鼎盛時期之一。這一時期,隋唐王朝大力開發隴右。今定西作為隴右的主體組成,以完善綜合經濟制度促使種植業新發展,以官辦“馬政”帶動畜牧業大發展,促使全社會“勤于稼穡”、經濟社會蒸蒸日上,確實如北宋大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所說: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自安遠門(長安西城門之)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1]。
一、提高對開發定西地區戰略意義的認識,增強開發的主動性
一是充分認識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定西是東西交通咽喉,地勢險要,山高谷深,重巒疊嶂,歷代政治家和兵家高度重視。隋朝和唐朝的都城在關中地區的長安(今西安),包括定西在內的隴右地區,對維護其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對此,隋唐統治者的認識十分清楚。《舊唐書》卷198說:關中為“天下之上游”,而隴右則是“關中之上游”,“欲保關中,先顧隴右”[2]。此種認識,一直延續。明清之交的大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今隴西、臨洮縣等地,“翼蔽秦隴,控扼羌戎”,“各當有守”,“自古用武之國也”。在這里“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成,而良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而河湟之要領舉。”今岷縣等地:“東連秦隴,西達河湟,北阻臨鞏,南控階文,雖避在一隅,而道路四通,一縱一橫,末易當也,豈惟形援河洮,為西篇之翼蔽而已哉。”[3]
二是充分認識長期戰亂后亟待開發的緊迫性。隋唐統治者不但認為要占有包括定西在內的隴右,而且加強對這里的統治。因為自東漢末年至隋實現統一以前的四百年間,也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定西一直處在連年的大規模的動蕩中,人口流亡,土地荒蕪,經濟凋敝、社會發展低迷。隋末唐初,由于吐谷渾、突厥等周邊少數民族不斷入境,這里“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大力開發農業、增強經濟實力,是隋唐統治者加強統治最迫切的大事。
三是充分認識發展農業具有良好的基礎性。定西有渭水、洮河等河流,水草豐腴,人口較多,習慣發展以畜牧和種植為主的農業。這里的人不但“尚節約,習仁義”,而且“勤于稼穡,多畜牧”,得其地、足以給軍儲。
四是充分認識大開發具有良好的人力資源。定西是蕃漢雜處地區,自古以來,喜田獵,人性猶質直,人馬驍勇,崇尚武藝,習于戰守。得其人、足以資戰斗,提高統治能力。
二、推行“馬政”制度,以官辦馬業促進畜牧業的昌盛,促使畜牧業在整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隋朝認識到今定西森林茂盛,水草豐美,秦漢以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以“勤于稼穡,多畜牧”[4]著稱于世,就在隴西設置了全國最重要的官營牧區——隴西牧,積極促進這里發展畜牧業。隴西牧的位置很特殊,據《隋書·百官志》記載隴西牧的總監官銜“為五品”,具有統管其它諸牧區的權力,設有驊騮牧、三十四軍馬牧、苑川十二馬牧。隴西牧的規模最大,養馬很多。據《資治通鑒》卷176記載,開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派辛公義檢核群牧時,所獲官馬十萬多匹。
唐朝更加重視畜牧業,尤為重視馬政。唐初,沿襲隋代制度,繼續設置隴西牧監、發展以國有為主的牧馬業,隴中地區成為當時全國四大牧業基地之一,有馬45萬匹,牛5萬頭,羊28.6萬只。至天寶十三年(754年),隴右群牧都司奏:馬、牛、駝、羊總計60萬匹(頭),基中馬為32萬匹,牛7萬多頭,駝500多頭,羊20多萬只[5]。貞觀至麟德40年間(公元627-665年),官馬數量劇增至76.5萬匹,并在甘肅的涇、寧等縣地及今陜西的岐、彬等縣地設置8坊。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始置48監,專門管理官馬牧羊為主的畜牧業的經營、生產和管理工作。隨著唐太宗貞觀以后設置8坊、48監,隴西牧監規模更大,由關中西部逐步向西發展,“由京渡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數郡……員廣數千里,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其馬繁盛”。
為了持續發展畜牧業,唐政府非常注重收購和引進周邊少數民族及國外的馬匹,曾規定凡市馬30匹酬一游擊將。當時,隴西牧監遵從朝廷旨意,積極通過市場貿易和從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及外國引進良種馬匹,改良本地馬種,收到了“既雜胡種,馬乃益壯”的成效。在官方養馬業的帶動下,隴西民間大量養馬。唐睿宗年間(710年—712年),太平公主在隴西就有馬過萬匹,普通庶民養馬有十的也屢見不鮮。唐代后期,隴中地區的畜牧業衰退,不及初唐繁盛,但在中原地區不斷從西域各國引進馬、牛、羊和苜蓿良種的過程中,定西經常其益,畜牧仍有發展。今隴西博物館收藏的陶馬,高35.5厘米,為細膩紅陶,造型體格肥碩,筋骨健壯,昂首聳耳,若經欲奔,神采俊美,栩栩如生,為陶器藝術寶庫中的珍品,這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定西畜牧業的發達。吐蕃占領定西以后,大量牧養牛羊馬,畜牧業進一步發展。在渭源縣,至今有吐蕃首領每年在草茂馬壯季節設帳選馬、騎手編充軍隊的傳說,現存的“選馬村”、“跑馬溜子”等遺址,保留的如丈乍灘(意為草山灘)、巴兒山(意為牧點)、干乍(意為東窩子)、牧兒山(意為放牧山)等很多藏語村名,都與畜牧業生產有關。在臨洮,引入了西域的優良山羊,養羊業進一步發展起來。隨著畜種的改良,畜產品大量增加,洮河流域特別是臨洮逐漸成為隴中的毛褐生產基地。從這時期起到民國時期,臨洮的毛褐一直在隴右猶為享譽。可見,隴中畜牧業在隋唐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租庸調和均田屯田營田多管齊下,綜合實行開發人力和土地、賦稅資源的經濟制度,減輕農民負擔、解放農業生產力,調動全社會開墾荒地和發展農耕經濟的積極性
一是實行租庸調制度。為了解決過去官吏無休止無數量的苛索農民,隋唐政府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租庸調制,計丁征取。規定每丁年納“租”粟2石,隨鄉所出,輸“調”卷2丈,棉3兩或布2丈5尺,麻3斤。每年服徭役20日,不應役者,則按每日3尺絹折納,叫做“庸”。凡加役15天免調,30天租調俱免,額外加役最多不超過30天。租庸調法不但有利于解決官吏無休止無數量的苛索農民的問題,減輕了農民的賦役負擔,而且以庸代役有利于解決過去農民必須利用大量時間進行重體力型的服徭役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勞動力,減輕了人的體力勞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到唐盛世時期,渭州有6425戶、24520口,臨州有2899戶、14226口,岷州有4325戶、23441口,比其它州多。斯大林說:“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必要因素,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人口的增加,有力促使農民在恢復和發展生產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是推廣先進農業生產工具。在古代社會,農業是經濟的核心,生產力水平的先進與否首先體現在農業生產工具上。魏晉南北朝時期,定西在農業生產中普遍使用犁、耱、耙、叉、連枷、鋤、鐮、車、挽具在內的各式農具,最主要的農業生產工具之一犁還是由二牛抬杠。隋唐時期,犁經過二牛三人耦犁、二牛一人雙轅犁式改進,發展為曲轅犁,使耕犁開始定型化,這大大提高了墾荒和耕種的能力,發展了生產力。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指出:社會“生產的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的開始”。[6]
三是實行均田制。均田制是國家將荒田閑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將農民與土地結合起來,早在北魏時期,均田制作為一項必須落實的國策,今定西已實行。從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敦煌文書中《鄧延天富等戶戶籍殘卷》記載西陲敦煌實行可推斷,西魏、北周時期定西也實施均田制。隋朝時期繼續實行,唐朝時期的均田制比較完善。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全國面向滿18的男丁、工商業者、6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廢疾人口、寡妻和妾、僧徒、道士、女冠、尼等實行均田制。雖然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得到足數的土地,一般只有30畝、20畝,或者10畝、8畝,但農民還是得到了一定的土地。這樣,把社會上的流動勞動力有效的組織起來、墾荒種田。也使許多無地少地的人口得到土地、有權開墾荒地,發展農業。
四是實行屯田制。早在魏晉時期,今定西是魏蜀爭奪的戰略要地,魏蜀部隊交替占領,在很多荒閑的田地上以區種法屯田。南安、隴西至祁山一帶麥熟千頃。蜀將姜維曾在“沓中(原岷縣大珞鄉一帶)種麥,以避內逼”。南北朝時期,定西境內的北朝各政權相繼推行屯田制。唐朝時,今定西地廣人稀,以軍屯為主,民屯次之。《唐六典》卷7載:“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7]軍屯的土地屬國家,耕牛、農具、籽種由政府配發,口糧由官方供給,收獲物全部上交,存于本軍。設在狄道縣的臨洮軍有兵5500人,馬8400匹。今定西境內同樣一定實行軍屯。軍屯開墾了大量土地,還提高了將士的素質,整頓了軍旅,保證了定西的社會穩定。
五是實行營田制。隋朝時期,以隴西土曠民希,經常受到吐谷渾、突厥的寇掠騷擾,而俗不設村塢。隋文帝聽從賀婁子干的建議,令賀婁子干組織民眾建筑城堡,營田積谷,首創了政府直接組織民眾墾荒營田的生產形式。《隋書·食貨志》記載,包括定西在內的隴右居民多“立堡營田”。唐朝時期,繼續在土曠民希的地方實行營田。《新唐書·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捍要沖,因隙地置營田”。[8]營田就是將丁夫或流民組織起來的民屯,屯丁是均田制之外的國家佃農。營田的實行,推動了荒地的開墾。伴隨著土地的大量開墾,種植的物種增多,一些物種推廣到其他地區。
隋唐時期的定西開發歷史昭示我們:經濟大開發和大發展必須對農民輕徭薄賦、減輕負擔,不斷激發生產力的內在活力;必須把土地這一最基本的農業生產資料與農民緊密結合起來,長期保障農民對其所有權和更多獲得感,才能從根本上調動其發展農業的積極性;必須把種植業、畜牧業、林草業融合起來,進行大農業的開發和發展,才能增強農業的內生動能、提高農業的質量、獲取“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