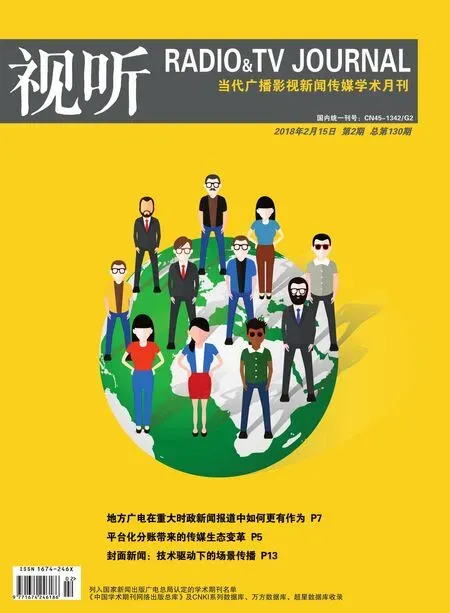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特點與發展趨勢
□ 陳亮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56個民族共同構筑起絢麗多姿的中華文化。而我們所講的少數民族,是在中國的多民族范圍內提出的漢族以外的其他55個民族。以這些民族為主要反映對象的紀錄片,都是我們討論和研究的對象。
一、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顯著特點
紀錄片是影像的藝術,是真實人和事的記錄展示,也是創作者思想意圖的表達。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因其以少數民族的風、物、人、情等為主要講述內容,在根源上就帶有與其他題材紀錄片不同的特質,形成了自身顯著的特點。
(一)神秘性
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各民族歷經遷徙、融合,逐漸形成比較穩定的民族區域分布。由于歷史、民族習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許多少數民族居住在山高林密的地區,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少數民族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社會體系。對于外界來說,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民族風俗習慣、倫理觀等都是神秘而新奇的,外人在進入到少數民族地區時,往往首先被他們獨特的習俗所吸引,而這些也成為民族題材紀錄片中最常見的展示內容。
(二)思想性
紀錄片導演孫增田認為,紀錄片應該成為人類的自省,文明的守望者,正視弱小的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沖突,提醒人類思考向前走。①一部成功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必然蘊含著深刻的思想性。從一些屢獲大獎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中,我們不難看出思想性是其作品的靈魂。比如《最后的馬幫》《神鹿啊,我們的神鹿》等作品,在記錄少數民族生產生活狀況的同時,都融入了創作者深切的思考與價值取向,這種思考不是狹窄的,而是關乎人類生存的思考。比如在《神鹿啊,我們的神鹿》一片中,導演通過鄂溫克女畫家柳芭走進城市又逃回森林的歷程,講述了三代鄂溫克女人的命運,進而反映鄂溫克民族的起落興衰。這種思想內涵已不再是單一、表象的介紹,而是多元、深層次的解讀。因此,思想性決定了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深度和生命力,能夠流傳于世并引發受眾共鳴的作品,必然蘊含著創作者的情感和思考。
(三)脆弱性
1958年文化部在文件中批示:“我們認為反映少數民族生活情況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僅對研究人類生活發展史有巨大價值,而且對廣大人民也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尤其是目前各少數民族社會生活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如不及時拍攝,即將散失,很難補救。”②受歷史、自然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我國許多少數民族的發展是分散而碎片化的。一些少數民族更是連民族文字都沒有,許多民族文化知識都依賴于口口相傳,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其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都顯得脆弱不堪,這也是目前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中所展示的主要內容——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紀錄片《達巴在歌唱》以四川和云南交界處的摩梭人文化傳承為故事線索,講述了摩梭人世襲的老達巴(祭司)因后繼無人,最后把經書傳授給了文化學者的歷程,片子反映出的不僅僅是達巴自己的痛苦和矛盾,更是民族文化面臨消亡時的抗爭與無奈。
二、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進階變化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少數民族地區也一改閉塞落后的歷史,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文化等得到極大的改善,民族交流和融合更加便捷、迅速。得益于這些改變,外界能夠通過更多的渠道來了解少數民族的情況,但紀錄片仍然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與使命。
近年來,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呈現出了新的變化,而在內容選擇和表現形式上尤為明顯。以往的許多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從名字就打上了非常明顯的烙印,表現的內容和形式都過于單一。而近年來,這種痕跡開始變淡。尤其是一些少數民族自治區創作的紀錄片,獵奇性逐漸淡弱,取而代之的是用客觀、發展的眼光和態度來展現少數民族的現狀與變化。
內容選擇上,除了傳統的民族習俗、節慶、生活等內容,少數民族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開始成為紀錄片創作的題材。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傳承與發展的矛盾、信仰與現實的碰撞等,都成為了反映少數民族狀況的選擇。內容的多樣化既是符合少數民族地區實際情況的必然之選,也是此類題材紀錄片發展的大勢所趨。
2015年,廣西電視臺創作的三集紀錄片《秘境廣西》中,關于少數民族傳統的呈現別具一格。第三分集《人和》講述了廣西南丹白褲瑤服飾制作技藝的傳承。在內容選擇上,片子把一個12歲白褲瑤小女孩作為主角,通過小女孩學習服飾制作技藝、完成自己的成人禮為主線,把白褲瑤服飾的歷史、制作、傳承等融匯其中,既生動形象,又易于接受。
表現形式上,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片經歷了從政治宣傳到大眾傳播的演變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由于中央需要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狀況,第一批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片開始出現,以《西藏的農奴制度》《涼山彝族》《大瑤山的瑤族》等作品為代表,它們在加強中央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溝通聯系等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這類少數民族紀錄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人類學研究價值,而大眾傳播的效果卻不佳。
改革開放以后,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表現手法開始發生變化,之前政治宣傳的色彩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真實生動的人和故事為主要講述對象,《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龍脊》等一系列優秀的作品是承載這種變化的典型。而人文關懷和平民化視角則成為主要的表現手法。人文關懷的突出表現是尊重少數民族生活習性,解讀文化的多元化,思考少數民族族群生存與發展,這些成為近年來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中表達的重要議題。平民化視角,一改主題宣傳的“畫面加解說”模式,見微知著,以細節的故事、大眾的視角進行平等對話,呈現出了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思想光輝。
三、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發展趨勢
(一)國際化表達手法成為主流
站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來看待、理解、展現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把民族的故事通過國際化的表達手法來講述,這是此類題材的紀錄片呈現出的新態勢。以中央電視臺推出的六集大型涉藏紀錄片《第三極》為例,它沒有轟轟烈烈的情節,沒有堆砌的華麗辭藻,而是通過一個個細小而生動,普通而感人的故事,表達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反映出藏族人民與自然、生活與信仰有機統一的主題。于細致入微處入手,以故事的平實敘述,精美的畫面呈現,表達博大精深的民族傳統與文化,是中國故事國際表達的典范。
(二)創作視角日趨多元化
隨著影視制作器材的不斷更新,新的創作手法不斷在紀錄片作品中得到呈現,小到微觀生物,大到航拍世界,俯視眾生,科技的進步不斷推動人們創新,刷新人們的思想認知。除了科技手段外,創作者的思想對于作品多元化的影響更加突出。廣西電視臺創作的紀錄片《終身大事》和《我的山水中國》,講的故事都與廣西柳州元寶山青山寨有關。前者講述了青山寨青年小杜為了延續梯田的歷史,接續苗家的香火,費盡心思尋找對象和勤勞致富的故事;后者以著名畫家黃格勝在青山寨寫生作畫的角度,講述了元寶山一帶數十年的更新改變。兩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反映的是不同人眼中的少數民族世界,更能夠引人思考。
(三)市場化影響愈加明顯
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片也不應該把自身與市場隔絕,商業價值不應該被忽視,擁抱市場,進行產業化生產是當今紀錄片領域的新趨勢。在借鑒一些成功經驗的同時,還要注重初期的市場調研、后期的宣傳與品牌管理。同時,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片不應該成為過度迎合大眾的市場產物,為了博眼球和經濟效益就一味獵奇,而應該在記錄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現狀的同時,通過作品的傳播,幫助、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與進步,這是紀錄片真正的價值所在。
注釋:
①聶欣茹.紀錄片概論 [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20.
②王華.從戰事“拾零”到民族大團結想象——建國初期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J].新聞大學,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