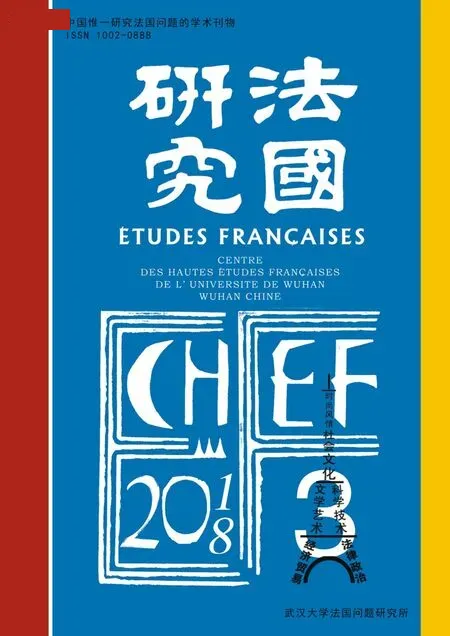艾什諾茲“傳記三部曲”中的機械和反機械原則
趙佳
法國作家艾什諾茲(Jean Echenoz)近幾年來對人物傳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經歷了漫長的虛構敘事階段,他進入傳統意義上的“真實敘事”階段。《拉威爾》,《跑》和《閃電》構成了他的傳記三部曲,分別以法國作曲家拉威爾(Maurice Raval),捷克長跑運動員艾米爾·扎多貝克(Emil Zatopek)和塞爾維亞裔的美籍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的生平為藍本。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傳記這一原則上需要尊重現實的“真實敘事”在艾什諾茲這里并沒有被如其所是地對待。誠然,他盡可能地保持了現實中人物的生活軌跡,但整個敘事從總體上來說仍然屬于虛構體,它從原則、結構、敘事和基調上來講和此前艾什諾茲式的虛構小說并無二異。作者狡猾地借用了歷史人物的殼,像機器一樣地拆解和重裝了傳記體,使之充滿了虛構敘事的樂趣。艾什諾茲的反諷體現在將人物傳記虛構化,并將虛構敘事機械化的做法。
之所以說傳記變成了一臺可被任意擺弄的機器,是因為機器不但被作為內容呈現,它甚至作為小說的精神被弘揚,而小說本身也像機器一樣被布局。艾什諾茲所選取的三個歷史人物所存在的歷史階段均為西方工業文明迅猛發展的階段,機器作為這個時代的主要特色被生動地呈現在文本中,我們能在這三部傳記中隨處發現對機器和工業的描寫。然而,機器不盡然是時代布景,它更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風尚和標志,即對蓬勃發展的大工業的贊嘆,對人類現代化進程的信心:機器成為了時代精神。從敘事的層面上來講,整個敘事的結構也像鐘表機械一樣被精確地構架,敘事節奏的把握,對細節的專注,敘事者的冷峻無一不使敘事打上了機器的烙印。因此可以說,艾什諾茲的傳記三部曲是以機器為原則構架的。
然而,作者的反諷在于,這并不是從流水線上下來的機器,而是經過了拆解和重裝的機器;不是標準化的機器,而是變形了的機器。首先小說所呈現的機器是變形的機器。我們所看到的雖然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機器,但這只是表象。工業革命時代的機器充滿了力量與美感,體現了進步和擴張,是實實在在,可被觸摸,具備實形的機器。艾什諾茲小說中的機器穿著工業化的外衣,內里卻是后工業時代的核。他的機器更多是作為表象和戲法的機器,強調的是機器的功能性、人工性、游戲性和裝飾性。其次人物也被表現為一臺變形的機器。我們所面對的是工業化時代的人,有著機器一樣被塑造的行為和習慣,有著機械一般強健的肉體和智力,驚訝并臣服于工業文明的人。但是這些人物卻被后現代的表現方式所表現,他們和艾什諾茲其他虛構人物一樣無血無肉,只有骨架,外形扁平,內里中空。他們被抽空了深度心理,只剩下一個模模糊糊的剪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艾什諾茲的傳記同時遵循機械和反機械原則。像機器一樣的人卻總是能擺脫僵化和束縛,通過艾什諾茲創造的奇異和怪誕的效果,迸射出浪漫主義時期的天才和激情。甚至機器也能擺脫單純的機器的地位,被賦予陌生化的效果,我們所看到的機器更多像一場盛裝出行的節日或魔術表演,它的娛樂功能超過了實際功用。反機械的原則也同樣體現在敘事中。作者并不在意敘事是否能像機器一樣被絲毫不差地組裝,他像一個即興的爵士樂手隨時調整節奏,插入意想不到的元素,在這部看似精密的儀器中加入反諷的潤滑油,在停停走走,拆拆裝裝中給出了傳記的另一種寫法。
一 . 對機器的崇拜和作為景觀的機器
《閃電》一書描寫了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傳奇一生。特斯拉生于 1856年,卒于1943年,他的發明旺盛期正是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期。艾什諾茲對這一時期的美國工業化進程進行了描寫。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成為西方歷史上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之一,生產力飛速發展,新產業層出不窮,科學創新和技術發明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美國社會狀況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從此美國社會開始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工業文明的物質基礎上。特斯拉所從事的電力行業在當時很具有代表性,它屬于新興的產業, 新產業的形成代表了新工業革命的完成。“經濟革命首先表現在動力上的革命…… 20世紀初電力工業部門成為美國現代工業體系中的重要部門之一。”①余志森等編,王錦塘等著:《美國通史,崛起和擴張的時代,1898-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頁。;“電從它開始踏上近代技術舞臺的時候起,就同時顯示了它為現代社會充當動脈和神經的雙重職能。”②易杰雄編,祖嘉合等著:《工業文明》。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334頁。《閃電》中提到了發電廠的建立,無線電、電話以及電影的相繼發明。《閃電》這一書名也表達了電力文明發軔期那種令人目眩的發明速度和發展趨勢。《閃電》的作者帶著和那個時候的人們一樣的驚訝之情,通過天才發明家的一生,表達了對電力的贊嘆。比電力發明更早的還有鐵路交通:“1902年美國的鐵路線幾乎已經編織成一個巨大的交通網絡,它已經可以直接或接近全國所有的大小村莊。”③余志森等編, 王錦塘等著:《美國通史,崛起和擴張的時代,1898-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頁。《拉威爾》中有相當的篇幅描寫拉威爾在美國的旅行,四通八達的鐵路串聯了整個路線。對電力和鐵路的贊嘆實則是對正在興起中的工業文明和現代技術的膜拜。在艾什諾茲這里,我們仿佛找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未來主義者對鋼筋水泥和轟隆的機器的贊美,有一種天真的信心和振奮。
和大洋彼岸遙相呼應的是歐洲大陸同樣迅猛的發展。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北部、比利時和奧地利帝國西部的某些地區成為最為發達的地區。“實際上歐洲所有的重工業全部集中在這個地帶。這里的鐵路網是最密的,歐洲的財富都聚集于此……”④[美]R.R. 帕爾默等著:《工業革命, 變革世界的引擎》,蘇中友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167頁。自 1895年起,法國經濟結束了停滯和蕭條,從二十世紀初到一戰前的十多年里處于高漲時期,逐步興起了一場以能源、交通和新興工業部門為代表的工業革命。“法國也和其他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經歷了資本和生產的集中過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壟斷,從而從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⑤張芝聯編《法國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62頁。工業革命催生了現代城市的產生,工廠和住宅區的建立,市內交通的建設,無一不在改變傳統歐洲的城市面貌。敘事者借作曲家拉威爾的眼睛如此描寫工業化的城市:
“他一直都很喜歡機器人和機器,喜歡參觀工廠和工業景觀,他記得二十年多前當他坐在游艇上路過比利時和萊茵蘭時,整個城市布滿了煙囪,頂上冒出紅棕色和藍色的火苗和煙來,鋼鐵做的城堡,熾熱的教堂,傳送帶,汽笛和鐵錘聲在火紅的天空下共同編織的交響樂。”①Echenoz, Jean. Ravel. Paris : Minuit, 2006, pp. 77-78. 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在今天看來如此熟悉并被飽受爭議的工業景觀在那個時代人們的眼中卻別有一番異國情調;煙囪、汽笛、鐵錘共同構成了一幅表現主義的繪畫和拉威爾式的現代交響曲。
然而,艾什諾茲的反諷在于他既不是未來主義者,盛贊新興的工業時代的到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機器中看到人的異化。他無意于用現實主義的筆調重現一個輝煌的時代,描寫二十世紀初的時代變遷和人事沉浮。他用近乎自然主義的寫法表達了一個后現代主義者的立場。他更像是一個波普藝術家,或超級寫實主義藝術家,他截取現實的片段,尤其是物像,如其所是地將之黏貼在作品中。如此被截取和放大的現實超越了現實本身,成為現實的影像,從而達到反諷的效果。艾什諾茲無所謂歷史的真實呈現,他將歷史變成了景觀,像標本一樣固定,供人觀看。機器在這樣的語境下失去了功能意義,它既不指向自己,也不指向歷史背景,它是裝置藝術,是景觀,追求轟動性和奇異的效果。
《閃電》中的人物代表了作者的立場,愛迪生和格里高爾將機器的演示過程變成了一場行為藝術。在交流電和直流電之爭中,西屋公司和格里高爾堅持研發交流電發電技術,作為競爭對手的愛迪生堅持直流電技術,他千方百計地阻撓交流電的推廣,他想到的方法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用交流電屠殺動物和死刑犯,讓公眾看到交流電的毀滅性效果。艾什諾茲花了大量篇幅描寫屠殺場面,用充滿漫畫色彩的喜劇風格想象了當時的場景。比如:
“鮮血淋淋的牲口被當街放在草墊上,展示在人群面前,有一位演示者當眾演示,在簡短的發言后,牲口們將會被充足的交流電電死,我們可以想象那個場面,濃煙滾滾,火光四射,噼啪作響,眾人的歡呼聲,肉的焦味,僵硬的尸體。路人都被震住了。②Echenoz, Jean. Des Eclairs. Paris : Minuit, 2010, p. 38. 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艾什諾茲筆下的愛迪生似乎非常享受自己一手導演的戲劇,我們甚至會有這樣的印象,他更在乎的是構思、導演和演出的過程,至于打敗競爭對手,只不過是附帶的效果。敘事者還提到愛迪生對電影的興趣,“非常喜歡爭端的他圍繞著這門新藝術展開了一場合同戰。他甚至在制作世界上第一部西部片和黑幫片 《火車大劫案》”(Echenoz,2010:40)。所有屠殺和死刑的場面都被愛迪生拍下來,傳播到各地。二十世紀初那些專注于競爭、擴張和資本積累的工業家在艾什諾茲這里變成了具有營銷意識,擅長造勢,精于傳播的后工業時代的企業家。機器在他們手里失去了現實的功用,成為舞臺道具。
愛迪生的對手格里高爾同樣將競技場變成了一個舞臺。為了展示自己的發明成果,他喜歡召集一大幫記者,在眾人面前做演示。與其說這是工業展覽會,還不如說是格里高爾的個人表演,他喜歡制造驚訝的效果,比如:
“一個房間先是完全沉浸在黑暗中,雖然時不時會有電光迅速地閃過。首先,他突然一下子出現,周身有一圈白色的光暈,不知道從哪里鉆出來,穿著緊身的燕尾服,臉長而蒼白,高高的身材因為高禮帽而顯得更高。他站在講臺上,被奇形怪狀,從沒見過的機器包圍著:螺線圈,熒光燈,各種螺旋形機器,尤其是眾多各式各樣的玻璃管,裝滿了低壓氣體。”(Echenoz,2010:53)
格里高爾根本無意于展示他的新發明,他更愿意制造戲劇化的舞臺效果,他不僅將機器變成了道具,甚至他自己也變成了一部機器,和其他裝置一起共同營造出一種炫目的舞臺效果。格里高爾和愛迪生的競爭不再是科學技術的競爭,而是藝術表演的競爭。兩個天才發明家將機器變成了一場可供娛樂和消費的表演。艾什諾茲的幽默就在于跳脫出機器本身,賦予它另外的角色,讓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中獲得陌生化的效果。
有時,格里高爾根本不需要觀眾,他獨自享受機器帶給他的表演:
“格里高爾用帶子把振蕩器固定在柱子的一側,開啟機器,回到座位上,很好奇地等待會發生什么。然而,慢慢地,這架裝置乍一看無害的振動效果,讓實驗室里散落的小東西都共振起來,他看到它們先是微微顫動,然后猛烈抖動,聽到它們先是發出低沉的聲音,隨后轟轟作響。共振很快就蔓延到更大的物體上,家具和機器振動得越來與猛烈,搖擺甚至變形。很快,一切都開始舞蹈。格里高爾在椅子上觀賞這一幕,覺得很有趣。完全忘記了他的憂愁。(Echenoz,2010:53)
在這一幕中,所有的機器都成為了演員,具備了生氣,在發明家的指揮下跳起了舞。電像是某種神奇的能量,不僅使機器和機器產生共振,甚至將人和機器置于同一場域之中。我們不再身處于人和機器對立的現實世界中,而是進入到一個奇妙的、魔幻的想象世界中。機器不再奴役人、異化人,它們是人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產物,是人的身體的延伸,人在機器的世界中如魚得水,自得其樂。
艾什諾茲的人物不但擅長制造稀奇古怪的機器,而且更是樂于故弄玄虛,操控他人。這樣的操控或許帶有現實的利益,但更多是一種游戲的樂趣。格里高爾便是如此,他“神秘,戲劇化,擅長擺弄燈光,制造效果,[同時擁有] 演說家,喜劇演員和魔術師的才能……”(Echenoz,2010:53);必要時,他還會使用“非常細微的欺騙手段,但無傷大雅,觀眾們信以為真,保證成功。”(Echenoz,2010:53-54)。發明家特斯拉在艾什諾茲筆下成為魔術師喬治,他將機器神秘化,進而將自己神秘化。必要時可以耍些小伎倆,真誠和真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有趣的幻覺,這是藝術和文學的原則,人物搖身一變成了小說家的代言人。這一招很奏效:“人們稱他為魔術師,能預見未來的人,先知,大天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家。”(Echenoz,2010:55)
“他的仰慕者風格不一,而且據說來自于藝術界、科學家和政界,發明家也成為不少神秘主義者和開天眼的人的崇拜對象。術士開始對他產生興趣,把他稱為他們摯愛的水星人,來自于遙遠的星球,乘著太空飛船來到地球,或者根據有些版本,他坐在巨大的白鴿翅膀上來到地球。” (Echenoz,2010:58)
艾什諾茲用夸張的、幽默的筆觸展現了一個被神化了的發明家形象。世紀初對科學技術的景仰瞬間變成了一場故弄玄虛的鬧劇。科學家被神化同時表現了機械和反機械的原則。它既體現了世紀初的人們對科學技術巨大發展的驚訝和惶惑,在面對神秘的技術之神時所形成的“拜物教”,又體現了個體在勢不可擋的機器面前仍然保留了想象和創造的空間,在偽裝和揭露之間將機器變成游戲的空間。
二. 被機械化的身體和身體的反機械化
艾什諾茲在三部傳記中不僅塑造了機器的形象,也呈現了被機械化的人身。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的時代伴隨著現代工廠生產制度的建立,這一標準化的方式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率,但隨之而來的是勞動者身體的異化:
“資本主義勞動將勞動產品與其生產者相分離,從而讓個體脫離其類生活中的本質部分,也脫離了與自然世界的關聯,使其陷于異化。隨著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強化,無論是身體勞動還是腦力勞動,都成為單純維持生命的手段。個體也就與自己的身體相異化。”①[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術與社會中的身體》,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9頁。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必須對勞動者的身體加以規訓,才能使他們適應既定的工業節奏和工作模式:
“工廠體制要求通過對‘手工匠人或外包工人驟發性的工作節奏進行例行化處理,直至適應機器的紀律/規訓,以此實現人性的轉型。……工廠體制對待工人就像機器,清除他們身上最后一絲獨立活動的痕跡……” (克里斯·希林,87)。
艾什諾茲所呈現的人是工業化時代炮制出來的個體,他們帶有那個時代鮮明的痕跡,即人逐漸淪為機器的趨向。所以他所描寫的人,不管處于社會的哪個階層(上流社會或底層民眾),也不管從事哪種職業(發明家抑或是音樂家)都打上了機械的烙印,“身體由于淪為工業化諸般效應的定位場所,已經受到深刻的形塑作用。”(克里斯·希林,88)。這是艾什諾茲眼中的人,被現代性打磨的人,一具完全被理性化、技術化的肉體。
《閃電》中的格里高爾從一開始就受到時間的困擾,他不能確定自己出生的時間。人生中“第一個坐標”(Echenoz,2010:7)的缺失確立了今后他的人生的一個重要命題:“時間問題如此廣泛,他卻使其成為人生中的頭等大事。”(Echenoz,2010:8)格里高爾對機器的熱愛來自于時間的模糊對他帶來的困擾:“應該是為了解決如此讓他揪心的時間問題,他才一有可能就拆卸鐘表,當然之后還要再裝上……”(Echenoz,2010:11)格里高爾對機器的狂熱來自于時間定位的缺失所帶來的不安全感,他體現了工業化社會中被時間規范和塑造的人一旦失去時間坐標而產生的焦慮。我們的身體如此被時間所定格,以至于任何對時間的違背都會導致生存感的喪失。控制時間的欲望最后變成對時間的譫念:“他五十年來毫無差錯地計算時間。每三十三分鐘他就看一下手表:他總是很精確地知道現在是什么時間,每一秒都擁有一個絕對的鐘表,就像其他人擁有耳朵一樣。” (Echenoz,2010:73)這種對效率和速度的追求根植在每一個現代人身上,格里高爾以其機器發明者的形象極具反諷意味地指出了現代人的世紀病: 那種始終在跟時間賽跑卻總是落在時間后面的挫敗和慌亂。其實,格里高爾一生致力于發明機器的過程也是旨在控制機器的過程,他的故事重演了人和技術之間模糊的關系:人既是技術的發明者也是技術的受害者;人企圖通過控制機器來保留最后一點主體的權力,最后發現機器蠶食了主體性,使人降格為和機器一樣的存在。
艾什諾茲對機械般身體的呈現不單局限于工作態的身體,還描寫了體育態的身體。《跑》一書講述了捷克長跑運動員艾米爾·扎多貝克的生平。敘事者在小說中長篇描寫了運動中的身體,尤其是扎多貝克獨特的跑步姿勢:
“艾米爾像在挖什么東西,在自己身上挖,好像很迷醉,或像一個挖土工人。艾米爾遠沒有遵守學院派的規則,也毫不關心是否優雅,他前進的方式很笨重,不流暢,很痛苦,斷斷續續。他并不掩蓋巨大的努力,從他痙攣的、扭曲的、因為苦笑而保持變形的臉上可以看出來。”①Echenoz, Jean. Courir. Paris : Minuit, 2008, p. 49. 后文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艾米爾的風格是一種“著力”的風格,所有的努力都展現在姿態中,而他的姿態也因為極端地呈現了這種努力而吸引人。扎多貝克所代表的是工業社會中的運動態身體,肉體無需額外展現靈魂,它只代表它自己,一個純粹運動中的身體,一個將自身作為施力客體的肉體。如果說勞動是將人的體力運用于外物,那么在運動中,人勞作的對象是自己的身體,這是工作態身體在體育中的再現。“體育活動曾經作為文化創造性的表達,而今則受制于遵循工作原則的重組。……唯功能、成就、科層標準化是瞻。”(克里斯·希林,112)。資本主義制度在體育賽場上塑造了高產量勞動者的英雄形象,并將之理想化為英雄主義意志力的體現,拔高被勞動降格的人的形象,使勞動者和觀者都將之作為典范來崇拜。“對意志的鍛煉,對強壯,粗野人格的期望都成為工具。由此誕生了能夠讓身體‘挺得更直’的細致的體育項目以及全民愿意共赴鐵血的瘋狂形象……”①[法]喬治·維加埃羅:《鍛煉》,載[法]讓-雅克·庫爾第納編,孫圣英等譯《身體的歷史,目光的轉變:20世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130頁。。
對產出的追求和對速度的迷戀結合在一起。“鍛煉你的風格。不,他說,風格是無稽之談。我的問題是,跑太慢了。要跑就要跑得快,不是嗎?”(Echenoz,2008:21)社會學家們從中看到了時間原則代替空間原則成為組織體育的標準,尤其體現在田徑賽場上:“所謂速度由于空間的價值評判的范例,還是堪稱現代運動之‘精華’的田徑運動,推崇線性運動,精確計時,打破記錄……”(克里斯·希林,112)。無論是速度還是效率都是機器原則在人身體上的貫徹。對技術的崇拜將身體也變成了一項應該不斷改進的機器。將人體比作機器的比喻在小說中隨處可見:“像機器人一樣僵硬的姿勢”(Echenoz,2008:53),“他那機械的力量和像機器人一樣的規律”(Echenoz,2008:60)“讓機器運轉,不停改進,使其出成果,只有這個才重要……”(Echenoz,2008:54)。于是身體被技術化了:這是一個“技術性的身體”,“一個經過精心測量的身體。它的‘進步’,如同它的‘鍛煉’,都是‘策劃’的結果。”②[法]喬治·維加埃羅:《鍛煉》,載[法]讓-雅克·庫爾第納編,孫圣英等譯《身體的歷史,目光的轉變:20世紀》。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118頁。人身技術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對自然理性化的過程,工具理性將其殖民的地域擴展到了所有有生命的機體中。
《拉威爾》一書則揭示了工業文明是如何深刻影響到現代藝術的形態。對機械的熱愛影響到了拉威爾的音樂創作,他在音樂中利用了很多日常器械發出的聲音,哲學家揚科列維奇不乏反諷地感嘆:“啊,在他的作品中就只缺奶酪擦碎器或者搖彩機和左輪手槍。③[法]弗拉基米爾·揚科列維奇:《拉威爾畫傳》,巨春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24頁。”對機器異常敏感的艾什諾茲不可能不注意到這一傾向,他在《拉威爾》中這樣描寫:“這段時間拉威爾很喜歡看一家工廠,在威斯內鐵路沿線,就在茹葉橋旁,這家工廠給了他一些想法。是的:他正在創作一種類似于流水線工作的音樂。”(Echenoz,2006:78)這部作品就是《波萊若舞曲》,它的成功在于它對節奏感的呈現,拉威爾自己曾說:“我寫這首曲子,并非全然為繪畫性質,而是意圖以節奏的反復為主。④許鐘榮編《現代樂派的大師》。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99頁。”在敘事者看來,這是一部源自工業革命,講述工業文明的作品,音樂性的喪失是指由旋律所支撐起的情感的表達讓位于一種控制妥帖的節律,正如工廠流水線的勞動,“拉威爾是個精確的計時員——他對同時性進行著精確的控制——所有這些重疊造成的混亂都是按秒計算,按秒控制的,時間一到,就會馬上停止。”①[法]弗拉基米爾·揚科列維奇:《拉威爾畫傳》,巨春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31頁。拉威爾對音樂的控制應和了機械文化下的理性原則。
然而,艾什諾茲通過塑造天才的形象成功消解了被機械化了的肉身。格里高爾、拉威爾和艾米爾都是各自領域內的天才,盡管他們花了很多精力工作,但紀律和勞作并不能掩蓋他們異于常人的天賦。對天才的塑造尤其體現在《閃電》一書中,敘事者竭盡所能將格里高爾塑造成一個罕見的發明天才。小說一開始就描寫了主人公異常的出生:狂風、暴雨、閃電、雷鳴,所有自然界狂暴的元素都被調動起來烘托一個天才的誕生。格里高爾異與常人的一點是他有非常敏銳的聽覺,并伴有幻覺等奇特的大腦現象。特斯拉本人也在自傳中屢次提及他的幻覺和驚人的聽覺。②[美]尼古拉·特斯拉: 《科學巨匠特斯拉自傳:超越愛因斯坦》,王磊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5,7,44,45頁。格里高爾的成長過程見證了一個天才的形成。他愛好數學、物理,有精確的記憶力,能夠在大腦中準確呈現一個空間結構,以至于他從來都不需要畫草圖,做模型,就好像“[那些東西]在它們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于[他的大腦中]。”(Echenoz,2010:13)如此反復暗示使格里高爾成為了神一般的存在:“當他有靈感的時候,很快就顯示出它們的高度,來自于浩渺的宇宙,具備了宇宙的意義。”(Echenoz,2010:14)敘事者將主人公塑造成具有非凡能力,受到神啟的天才形象。這里或許不無對特斯拉被整個二十世紀所神化的嘲諷,但更多卻是呈現了一個浪漫主義時代的天才形象:夸張的稟賦,不受任何束縛的張揚,對激情和內在性的追求,自然和藝術的雙重熏陶……艾什諾茲以一種頗具反差的筆調塑造了一個工業社會來臨之前,張揚個性和創造力的英雄形象。
這一形象的矛盾之處在于,主人公的勤勉、專注和高效使其和工業社會相得益彰,他是一個典型的工業時代的天才。但是他的恣意、率性、瘋狂又使他和身處的社會格格不入。在他身上同時有工業化和反工業化的影子,他的身心同時體現了機械和反機械的原則。格里高爾并沒有從實用的角度去思考發明,他的創造活動是靈感和個性的表達,以至于很多時候想法只停留在想法的階段,他并不關心是否將之付諸實踐,更不關心是否能憑此獲利。格里高爾從根本上是反對工具理性和資本邏輯的。“[他對金錢的看法]和利益主宰一切的工業邏輯格格不入。”(Echenoz,2010:82)和實用原則不相稱的還有格里高爾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他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進行高頻高壓實驗,試圖制造人工閃電;他通過自己的接收器觀察閃電并研究了大氣電;還有他未竟的沃登克里弗塔計劃。 敘事者將他描寫成一個試圖控制自然界,聲稱能和外星人溝通的奇人。這是個“瘋狂的學者”(Echenoz,2010:95),一個“將現實和想法混淆在一起”(Echenoz,2010:14)的人。敘事者用半是有趣,半是反諷的語調描寫了格里高利的瘋狂想法和舉動。艾什諾茲顯然并不贊同特斯拉的瘋狂以及后人對他的神化,但他樂于在小說中塑造一個癲狂的科學怪人的形象,和他所努力營造的工業氛圍形成一種強烈的沖擊。對機器的驚訝和盛贊絲毫不妨礙他引入一個破壞性的元素,在堅硬的機器中拉開一道想象力的口子。作者的反諷在于他自身模棱兩可的態度:他既將人體看做是一架機器,又不時地否定自己的論斷。對人的懷疑,對機器的懷疑伴隨著作者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共同構成了艾什諾茲反諷的特殊風格。
三. 被拆解和重裝的敘事
正如拉威爾將工業原則應用到音樂創作中,艾什諾茲也在小說創作中引入了機器的原則。他的傳記和他此前的小說一樣將傳奇性和現代主義的手法糅合在一起, 同時遵循了機械和反機械的原則。他的小說如同他熱衷塑造的機器形象一樣,人們總會被機器精密而繁復的表象所迷惑,作家如此賣力地制造機械的表象并非出于性能考慮,他更多出于魔術師惡作劇般的樂趣,制造一個空洞的存在,進行曇花一現的表演,讓觀眾在愕然中體會破壞的樂趣。
作者對一個貌似經典的小說結構暗中做了修改,時而擴充情節,時而壓縮情節,漫不經心地破壞了敘事的平衡性和穩定性。在制造機器的表象的同時,作者從內里抽出幾個原件,以至于敘事時快時慢,停停走走,機器實際的性能和它所呈現的表象形成反差。在《閃電》中,作者敘述了格里高爾一生中重大的事件。然而,這個結構顯得過于粗疏,作者并無意于記錄所有重要的事情,他更傾向于反轉重要和次要的關系,給予關鍵事件最少的、必要的描寫,將重心轉移到他認為重要的細節上。比如作者花了寥寥數筆來講述格里高爾如何被西屋公司相中,展開一系列合作計劃,作者很簡略地說:“所有的報紙都在說這件事。愛迪生有讀報的習慣。”(Echenoz,2010:36)相反,作者花了大片篇幅描寫愛迪生如何運用各種手段證明交流電的危害。在格里高爾發明旺盛期,作者更熱衷于描寫主人公發明的一些無足輕重的小玩意兒以及他的在公眾前的表演,而對重要的嚴肅的發明或者著墨不多,或者用夸張的、變形的方式加以描寫。《拉威爾》更加貫徹了主次顛倒的原則。整部小說彌漫著松散的氣息,除了演奏會和拉威爾晚年身體的衰敗用了比較緊湊的節奏外,小說更多是用慢節奏描寫旅行見聞、舞會等細節,作者甚至用整整一頁的篇幅來描寫拉威爾如何梳妝打扮(Echenoz, 2006:8)。 《跑》中有一段則直接將重大歷史事件和一樁無足輕重的事件放在一起敘述:“……當年年底起,報紙里有一則廣告,赫爾辛基奧運會的海報出售。兩千組三十五瓦的燈泡共計十萬個。 其他光明還有,斯大林次年年初去世,偉大領袖哥特瓦爾德在參加葬禮的時候著涼,從莫斯科一回來就在布拉格去世。”(Echenoz,2008:94)。這一段非常簡潔地將體育和政治,個人歷史和集體歷史放在同一水平面上,使其互相觀照,不僅對宏大的人類歷史加以嘲諷,更對個人在歷史機器里的命運進行戲謔。從敘事上來說,大事件和小細節的并列不僅打破了傳統傳記的原則,而且也破壞了經典虛構體的結構。
兩個原則還體現在詞匯選擇上。艾什諾茲動用了很多專業術語來陪襯人物的身份。比如《拉威爾》中的音樂術語,《跑》中的運動術語,《閃電》中的工程術語。術語的堆積強烈暗示了技巧的存在,不但將一個職業的內容濃縮成技巧的疊加,也加強了小說的專業色彩。術語的運用讓敘事顯得更加嚴謹,更加具有機器的效果。然而,艾什諾茲信手拈來的專業詞匯并不應該完全被看做是表詞達意的功能性的語言,很多時候它們并不是為了增加小說的專業性,而是為了起裝飾效果,和所有其他領域的詞匯一起制造一種怪異的氛圍,從而起到反諷的目的。在另一些場合,專業詞匯和瘋狂的舉動聯系在一起,使嚴肅的語言失去了可信度。比如《閃電》中一段:“很早他就確信應該運用潮力、地質運動、太陽光等此類元素做一個什么東西,或者干嘛不拿尼加拉瓜大瀑布試手,他在書中的木版畫中看到過,覺得足夠襯得上他。”(Echenoz,2010:117)物理詞匯和人物的奇思怪想搭配在一起,制造了喜劇效果。我們能感到艾什諾茲對專業詞匯的熱愛更多出于展示、陳列、搭配和制造噱頭的興趣。
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同時體現出敘事的機械性和反機械性。之所以說具有機械性是因為艾什諾茲動用了塑造類型人物的手法將人物描繪成漫畫圖譜。這一點在《閃電》中尤為明顯。除主人公格里高爾被塑造成瘋狂的發明天才外,其他次要人物也被打上了類型化的烙印。比如愛迪生被描寫成卑鄙自負的陰險小人,喬治﹒西屋被描寫成有雄心、有謀略、精于維護自己利益的企業家,J.P.摩根被塑造成果斷、具有威懾力的金融大鱷形象。作者并不關心這些人物是否完全符合歷史原型,也并不專注于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給了每個人物最基本的定義,并圍繞此定義完成速寫,用簡潔、變形的線條勾勒出人物的輪廓。作者用同樣的方式處理小說情節。比如愛迪生和格里高爾的直流電和交流電之爭這一歷史事件被描寫成兩個黑幫之間的火拼;格里高爾和艾特兒之間曖昧的情愫被描寫成艾什諾茲式的具有喜劇效果的情景劇。類型化的情節和類型化的人物給了小說臉譜化的機械感,但正是這種機械感應用到傳記中破壞了傳記的規則,反倒起了反機械的效果。傳記體被狡猾地轉換成艾什諾茲所擅長的黑色小說,歷史事件帶上了懸疑色彩,歷史人物被扭曲、被漫畫。作者非常巧妙地用類型化的方式達到了反類型的目的。
敘事的機械和反機械效果最后體現在敘事者的語調上。在這三部小說中,我們聽到了艾什諾茲慣有的冷峻和反諷。兩種語調互相作用,制造了冷和熱兩種效果。艾什諾茲在敘事上用了行為主義的敘事方式,即所有事件均用外視角進行敘述,既不深入人物內心,也不創造全知敘事者的形象。敘事只從外圍對人物的行為進行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僅限于最基本的情感,并盡量用克制的方式告知讀者。小說放棄了法語文學敘事中經典的簡單過去式,一律采用現在時和復合過去時制造當下感。敘事者如攝像機般跟蹤人物,給人很強的故事正在進行中的感覺。外視角和現在時的運用非常突出地制造了冷峻的、中性的、不動聲色的效果。然而,冰冷的機械感被反諷的語調反沖。一般來講,反諷即便不屬于中性的語調,至少也會制造一種距離感,因為反諷是對情感的節制,從根本上和情感相對立。但是在艾什諾茲的這三部小說中,反諷在中性敘事中加入了暖色調,引入了敘事者個性化的聲音,在外視角中插入了敘事者的視角,好比是在一臺悄無聲息運轉的機器中出現了吱嘎作響的聲音。反諷的手法非常多樣,在此僅列舉一二。比如敘事者會在第三人稱為主的敘事中突然出現第一人稱的自我指稱來表達對人物的嘲弄。在說到格里高爾對鴿子近乎偏執的愛時,敘事者說:“從我個人而言,我受不了這些鴿子了。我感到你也受不了了。我們都受不了,實際上這些無情多變的動物也受不了格里高爾了。”( Echenoz,2008:171-172)更多時候,敘事者用幽默的語調講述一個具有喜劇色彩的場景,比如拉威爾的求婚經歷:
“我們知道他有一天鼓足勇氣向一位朋友求婚,她笑得很大聲,在所有人面前大呼小叫,說他是瘋子。我們知道他跟愛蓮娜也試過,他很隱晦地問她是不是愿意在鄉下生活,她也拒絕了,雖然方式更加溫和。第三個女人又高又大,而他又瘦又小,當她向他求婚時,我們知道這回是他笑出了眼淚。”(Echenoz,2006:84-85)
敘事者的反諷有諸多變調,有時是幽默的、具有親和力的;有時是喜劇的、張揚的;有時是嘲諷的、略帶攻擊性的。不管反諷如何變化,它都給敘事帶來了生氣和情感。它在中性的、金屬色的敘事中加入了色彩,讀者似乎在機器的聲音中聽到人的笑聲。
在上文中,我們分析了艾什諾茲傳記三部曲中機械和反機械原則之間的相互作用,分別體現在三個方面:對機器的呈現,對人身的呈現,對敘事的呈現。三部小說重現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變革。工業化景觀,無處不在的機器成為時代的標志,艾什諾茲描寫了一個被普遍機械化的社會和歷史進程。然而,艾氏對機器的描寫使機器失去了真實性,成為純粹的景觀。機器被扭曲、被固定、被作為標本陳列在讀者眼前。機器被抽繹了內涵,被剝奪了功能性,成為娛樂大眾的小玩意兒。人的身體遵循了相同的邏輯。三部傳記展現了三具被機械化了的人身:格里高爾和工作態的身體;艾米爾和運動態的身體;拉威爾和音樂態的身體。三尊肉體是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雙重作用下的產物,它們體現了時間、速度、效率和產出的原則。肉體被迫遵從并內化了機器的要求,同時成為勞動者和勞動工具。不過,人的肉體唯其具有能動性而能夠反作用于工業原則。格里高爾的天才和瘋狂打破了肉身的功用性,引入了前工業時代的激情。拉威爾的音樂雖然被打上了機器的標志,但音樂作品中所蘊含的有節制的情感和出其不意的節奏讓人體驗到打破規律的美感。機械性不但體現在內容層面上,也蘊藏在敘事結構中。三部傳記承襲了艾氏小說的故事性和傳奇性:繁復的情節,張弛有度的節奏,類型化的人物,大量專業詞匯的應用以及不動聲色的敘事者,這些特點為艾什諾茲的小說打上了嚴謹的,冰冷的機械色彩。但作者在一個貌似經典的敘事中引入了很多破壞性的因子:隨意壓縮或擴張的情節,扁平的、漫畫式的人物速寫,反諷的介入等無一不使小說呈現出荒誕的、奇異的效果。
機械和反機械的效果給了艾什諾茲小說某種矛盾的張力,這種張力來自兩種力量的對沖: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前者代表了力量、進步、功能和深度。無論是對工業景觀的描繪,對勞動態和運動態身體的呈現,還是對經典小說性的追求無一不體現了工業社會的準則。乍一看,艾什諾茲懷著驚訝和贊嘆盛贊了興盛中的工業社會,展現了對機器和速度的極大興趣。但在訝異中透露出了迷惑,甚至是擔憂。這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發展以后的當代人對工業文明的惶惑。于是,三部以工業社會為內容的小說是以后工業社會的視角進行表現的:平面化,去中心化,對表象和影像效果的追求,玩世不恭,戲謔代替了工業社會的標準成為后工業社會的敘事原則。機械失去了其穩固的意識形態基礎,成為某種海市蜃樓般的假象。反機械的效果來自于對工業文明的根基的懷疑,是后現代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閃現。艾什諾茲的反諷是一種游戲性質的反諷,贊嘆和破壞這兩種模棱兩可的態度造就了后現代主義者對工業文明的立場,也造就了獨特的后現代敘事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