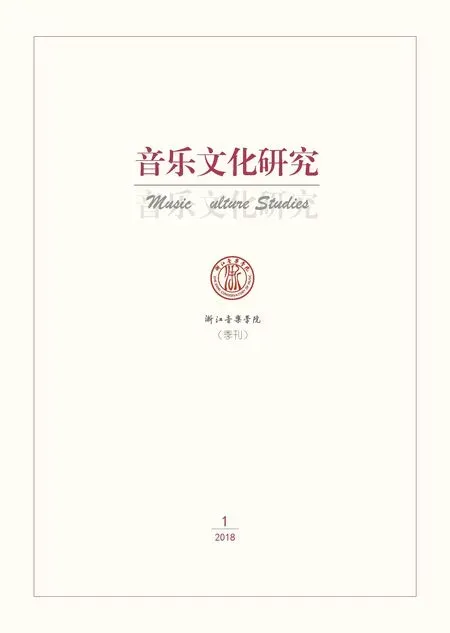摩洛哥哈穆利亞格納瓦音樂之初探
劉曉倩
格納瓦音樂在摩洛哥有三大中心,分別是摩洛哥南部的索維拉(Essaouira);阿特拉斯山脈中的圣所穆萊·布拉伊穆(Moulay Brahim);撒哈拉沙漠爾格·切比(Erg Chebbi)的村莊哈穆利亞(Khamlia)。三大中心對格納瓦有著重要意義,幾乎涵蓋了格納瓦音樂的全貌,是現存格納瓦(Gnawa)身份認定的三個代表性場所。筆者分別于2015年、2016年兩次赴摩洛哥進行田野工作,并對這三大中心的格納瓦音樂進行深入研究。在下文中,筆者主要以撒哈拉沙漠的村莊哈穆利亞為例,對哈穆利亞格納瓦音樂的組織之一進行一個較為深入的描述。
一、村莊哈穆利亞
哈穆利亞村莊位于摩洛哥的東南部,挨著撒哈拉沙漠爾格·切比(Erg Chebbi,阿拉伯文:),整個村莊約有三百七十人,族源包括格納瓦人和柏柏爾人。哈穆利亞也被稱為黑人村落(Black village)或非洲村落(African village),咨詢人穆罕默德·馬祖茲對筆者說:
哈穆利亞是偉大的撒哈拉沙漠的一扇門。
而初到哈穆利亞這個位于撒哈拉沙漠的村莊,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們黝黑的膚色。在從穆萊·布拉伊穆到哈穆利亞的長途跋涉中,筆者通過穆罕默德·馬祖茲的幫助,能夠通過女性村民的衣著清楚地識別所經過的哪個村莊是柏柏爾人,哪個村莊又是阿拉伯人,如果不看女性衣著,根本無法通過膚色分辨其民族,因為他們都擁有較淺的膚色。但當筆者終于到達了哈穆利亞之時,卻發現這個村莊的村民全是黑人,這個不同于柏柏爾人、阿拉伯人的族群在哈穆利亞形成了一個類似于社區的成熟村落,有他們獨特的起源、文化與信仰。那么,為何哈穆利亞的村民為黝黑膚色?他們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何關系?為什么穆萊·布拉伊穆的格納瓦藝人膚色較淺,他們之間又有何聯系?對于最初所見,筆者認為從膚色上看,哈穆利亞的起源很可能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密切聯系。
通過阿卜杜阿里以及對當地的格納瓦組織領導者扎伊德·烏杰阿(Zaid Oujeaa)的多次采訪,筆者對其起源也有了初步了解。哈穆利亞的格納瓦起源于與撒哈拉沙漠有著長期密切關系的黑非洲。他們的祖先作為奴隸,是通過跨撒哈拉沙漠貿易從中非和西非到達摩洛哥東南部的。而奴隸解放之后,他們作為游牧民族居無定所,四處尋找有利于他們生存的,能夠為他們的畜群良好供給的土壤。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格納瓦開始選擇在土地資源相對較好的地方定居下來,于是就出現了不大的村莊,之后,他們又和同樣以游牧為生存方式的柏柏爾人通過婚姻的方式融合,從此開始了從游牧到定居的生活,而哈穆利亞村莊就是由此產生的。當他們開始了定居生活之后,收入來源變成了農業、畜牧業以及最近開始發展的旅游業。

圖1 哈穆利亞村莊的泥瓦房(筆者攝于2015年)
哈穆利亞的“沙漠之鴿”組織的領袖扎伊德·烏杰阿①告訴筆者,古城西吉爾馬薩是中世紀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異常繁榮的原因就在于它位于跨撒哈拉沙漠貿易的路線上,并且是Caravan(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隊)的停靠點。而對于村莊哈穆利亞來說,跨撒哈拉沙漠貿易②影響到的一點就是,跨撒哈拉沙漠貿易中販運而來的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作為奴隸被大量地留在了西吉爾馬薩(即如今的哈穆利亞村子一帶),而隨著奴隸解放,這批解放的黑奴組織起來,在這一地區建立了自己的社區,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立起來的黑人社區與柏柏爾人、阿拉伯人以通婚的形式相融合,由此產生了一個特殊族群——格納瓦(即被奴役過的蘇丹非洲人的后裔),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有著共同的黑奴身份以及跨撒哈拉沙漠的苦難歷史。哈穆利亞村莊的村民阿卜杜勒阿里告訴筆者,這就是哈穆利亞村莊的起源。他說:
我們的村莊(已知)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村子居住著柏柏爾人、阿拉伯人以及來自撒哈拉以南的不同部落的人。在哈穆利亞村莊,最出名的就是班巴拉人,我們也稱之為格納瓦。我們是起源于黑非洲的奴隸的后代。
在哈穆利亞這個緊靠撒哈拉沙漠、人口約為三百七十的小村莊,卻有兩個格納瓦音樂組織,他們距離不遠,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的一個獨立院落,兩個組織分別名為:
沙漠之鴿(Pigeons du Sable)
德斯·班巴拉(Des Bambara)
在下文中,筆者將通過在哈穆利亞的所見所聞所感,對這兩個格納瓦音樂組織之一“沙漠之鴿”進行較為細微的描述,由此探尋如何對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進行一個合理、準確的定位。
二、初探“沙漠之鴿”
咨詢人穆罕默德·馬祖茲陪同筆者走在混著沙漠的路上,雖是早上,但這里的溫度已經高達四十多度,在這令人煩躁的炎熱中我們都沒有說話,安靜地沿著小路不知目的地走著。筆者時而轉過頭看向不遠處的茫茫沙漠,時而低頭看著這發黑的土路,心里感嘆那些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是有多么強大的耐受力,能夠忍受這種生存環境。一早的溫度已經讓筆者滿身的粘膩,而通常,在哈穆利亞的午后,大部分時間筆者都躲在屋里整理采風資料,不愿出門,就在這胡思亂想間,筆者看到了路邊兩個緊挨著的牌子,白底黑字,上面有不同顏色的圖像,這兩個牌子在幾乎空無一人的路上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筆者走進看到牌子上的字分別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簡單的兩個牌子卻同時包括了三種語言,很顯然,如果單純從這一角度來看,而非深入探究,那么,可以說這個組織是針對游客的。
左側牌子上的字分為六行,分別寫著:
社團(Association)
哈穆利亞(Khamlia)
發展(Developpement)
團結一致(Solidarite)
財產(Patrimoine)
混合學校(Ecole Mixte)
這六個時而英文時而法文的詞匯(前三個為英文,后三個為法文)是對這個組織極為簡略的概括。對于前面五個詞語很容易理解,筆者對其作了一個大略的解釋,即這個格納瓦組織是哈穆利亞的社團,目前致力于發展,其社團成員類似于兄弟會,團結一致,是當地的文化財產。而需要注意的是最后的“混合學校”(Ecole Mixte),為什么在這個筆者所認為的格納瓦組織中會出現學校?而且寫在了大牌子上?對此筆者當時不得其解。
再看右側的牌子,上面分別寫著:
扎伊德的組織(Groupe Zaid)
格納瓦音樂(Gnawa Music)
哈穆利亞(Khamlia)
沙漠之鴿(Pigeons du Sable)
右側的牌子也是簡單地寫著幾個詞語,筆者同樣對其進行一個大致的解釋,即這個位于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音樂組織是扎伊德的,名為“沙漠之鴿”。
三、扎伊德與“沙漠之鴿”
為何會起名為“沙漠之鴿”?沙漠,自是由于其所位于的撒哈拉沙漠,而“鴿子”則是由于其所象征的是和平,而這正是哈穆利亞的格納瓦族群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故這個組織名為“沙漠之鴿”。
“沙漠之鴿”組織的領導人扎伊德告訴筆者,哈穆利亞的音樂是格納瓦族群的精華,音樂是從他們的祖先那里流傳下來的,而純粹的格納瓦音樂正是保留在他們的家園哈穆利亞村莊,并以這種傳統的方式留存著。扎伊德是“沙漠之鴿”格納瓦組織如今的領袖,他告訴筆者,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音樂一直都是父傳子承的教育方式。扎伊德·烏杰阿是哈穆利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在他19歲的時候,他的叔叔赫達·烏波拉(Hda Oublal)——一位出色的格納瓦樂人,向他介紹了格納瓦音樂的風格,并傳授給了他尕布瑞的演奏技能。當他的叔叔赫達去世之后,將哈穆利亞村落的圖標——尕布瑞傳給了烏杰阿,由此,烏杰阿成為了“沙漠之鴿”樂團的領導。如今,烏杰阿已有52歲了。他帶領“沙漠之鴿”格納瓦音樂組織參加了很多國際音樂節,曾前往阿爾及利亞、德國、蘇丹等地,他告訴筆者,時間的演變并沒有影響哈穆利亞格納瓦音樂的純度與真實性。他說:
我們音樂的主題是對上帝、先知以及看不到的靈的祈禱。每一個音調、歌詞、手勢以及節奏都回想起黑人的苦難,他們被釋放之希望的主要力量就是:真主安拉。
而值得一提的是,扎伊德不僅是“沙漠之鴿”組織的領導,還是村子中協會的負責人,而這正解釋了我們在村口所看到的左側牌子之意:
社團(Association)
哈穆利亞(Khamlia)
發展(Developpement)
團結一致(Solidarite)
財產(Patrimoine)
混合學校(Ecole Mixte)
正當筆者對這個小村莊的“學校”“協會”有所不解時,扎伊德非常驕傲地為筆者解釋了他所創建的這個協會。

圖2 哈穆利亞“沙漠之鴿”組織的領導扎伊德·烏杰阿(筆者攝于2015年)
協會(association)其實就是給哈穆利亞孩子們的學校,是在他們正常的,有政府資助的公共教育學校基礎上的補充。村子的孩子們在這里學習阿拉伯語、法語和數學。共有四個課室,三間是在村子中有圍墻的院子里,而另外一間則是在“沙漠之鴿”組織的旁邊,如圖3所示:

圖3 哈穆利亞的“Ecole Mixte”(筆者攝于2015年)
圖3中的建筑物即混合學校,包括三間簡陋的教室和一個足球場,在外墻上有一些壁畫,另一間在“沙漠組織”旁邊的第四個教室則常常有孩子演唱格納瓦歌曲。孩子們可以選擇去上哪種課程,因為正如村民們常常對筆者說到的,在撒哈拉沙漠這個如此炎熱的地方,孩子們在戶外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扎伊德成立的學校激發了孩子們學習的熱情。如此,扎伊德在哈穆利亞村莊備受尊重。而他所領導的“沙漠之鴿”音樂組織的盈利方式也并不是固定的。只有當游客購買他們的CD或者自愿在觀看表演后給予金錢時,才能夠獲得收入。其實,在筆者幾天來的觀察來看,很多游客僅僅只是聽聽音樂,滿足獵奇心,有些甚至聽了不到一分鐘便離開,而格納瓦樂人們則要在悶熱的屋子里隨時準備表演。這些樂人們始終隨叫隨到,每一天有不同的人,但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這一重要角色卻基本不變。沒有表演任務的樂人在院子中的地毯上或玩牌或休息,他們的表演基本是從早到晚。同時,扎伊德告訴筆者,有時他們的組織也會受到邀請前去表演,比如村中某人的生日或婚禮,抑或摩洛哥節日之時,他們并不會在開始之時便談好報酬,而是前往表演之后,由主人隨意支付。同時,有些喜愛音樂的游客在回國之后,會邀請他們去歐洲演出,雖然這個機會非常少。
扎伊德的格納瓦組織有18人左右,但是當筆者問道他們分別的身份之時,他們卻無法回答,之后,阿卜杜勒阿里告訴筆者,在他們這個組織里,不會稱他們為舞者、尕布瑞演奏者、塔卜鼓演奏者或克恰克演奏者,原因在于他們需要學習所有的樂器。所以并不能告訴你說5個人演奏克恰克或7個人是舞者,因為僅僅是在這場表演中是這樣的形式。但是尕布瑞演奏者是個例外,因為尕布瑞在格納瓦音樂中是最重要的樂器。阿卜杜勒阿里的原話是:
唯有智者能夠演奏尕布瑞。
在“沙漠之鴿”這18人的組織中,只有3個人能夠演奏尕布瑞,而這3人的任務就是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而另外15人則輪流表演跳舞、克恰克以及塔卜鼓。這18個人都為男性,當筆者問到是否有女性成員時,阿卜杜勒阿里告訴筆者:
在哈穆利亞村子,女子做家務,男人掙錢。通常這個組織是沒有女人的。但是當薩達卡節日時,她們會加入進來。在這個節日中,女性跳舞,并向真主安拉祈求賜予巴拉卡。
正如阿卜杜勒阿里所說,這個村莊有一個一年一度的節日,人們稱之為薩達卡(Sadaka),筆者以及游客所看到的平日里的格納瓦音樂是從來都不會有女性加入的,如果不是筆者在這個村中待了數日,在這個組織中是沒有機會看到女性村民的。

圖4 哈穆利亞“沙漠之鴿”格納瓦組織路邊的兩個牌子(筆者攝于2015年)
如今想來,第一次與“沙漠之鴿”這一組織的實地接觸并不成功,經歷了穆萊·布拉伊穆毛瑟姆,并感受到了其中的格納瓦音樂后,再看這個組織,筆者開始懷疑,是不是其已經變成了進入撒哈拉沙漠的游客必經之路?其純粹性是否還有所保留?
順著之前的路牌,筆者來到了一個院落的門口,大門和兩邊墻上顏色鮮艷的字與畫,讓這個地方在一片泥磚房中脫穎而出。門的左邊墻上畫著三種樂器,這三種樂器中的克恰克和塔卜鼓在穆萊·布拉伊穆中出現過,而另外一個則是低音域的三弦琉特——尕布瑞(Gumbri),而右面墻上則是一名身著白色杰拉巴的男子在演奏尕布瑞。
剛剛踏入院子大門,便聽到里面傳出的熱鬧的音樂聲,熟悉的克恰克和塔卜鼓配著尕布瑞低沉的旋律,筆者走進屋內,看到了一個呈長方形的簡陋的房間,房頂由稻草和木頭搭制而成,由兩個泥土砌成的柱子支撐著,墻面全是由泥土砌成,早已出現了太多裂痕。但就是這樣一個極其簡陋,甚至房頂都會隨時塌陷的房子,卻被用心地布置了。四方墻上掛滿了他們演出時的照片以及獲得的表彰,而兩個泥柱上也精心地圍著柏柏爾風格的地毯,泥土堆成的泥臺環繞著屋子的三面,上面簡單地鋪著花紋各異的布以及一些靠墊,方便人們坐靠。同時,有些泥座前還擺著小桌子,桌前放著當地用以招待客人的柏柏爾茶。正對著桌子的一面就是格納瓦藝人表演的地方,地上鋪著黑色花紋、紅色底面的柏柏爾風格長布,5位格納瓦藝人席地而坐,中間的演奏尕布瑞,同時是歌者,一人演奏塔卜鼓。
連續數日的相處讓筆者對哈穆利亞的這個格納瓦組織有了更深的認知,而初次所見的誤讀也消失殆盡,筆者分別對這個組織的領導者扎伊德·烏杰阿,樂人阿卜杜勒阿里(Abdelali)、薩拉姆(Salam)、赫謝姆(Heeshem),哈穆利亞村民烏薩馬(Usama)、伊迪(Idi)、阿里·歐巴那(Ali Oubana)等人進行了采訪,并在阿卜杜勒阿里的幫助下,分三次觀看了這個格納瓦組織的表演,每次約為40分鐘至一個小時。
按照受訪人的說法,哈穆利亞村莊中的格納瓦音樂保留了其最初的形態,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奴隸在被迫的移居過程中帶來的音樂。
四、演出過程
“沙漠之鴿”的格納瓦組織為筆者分別單獨演出了三次,筆者選擇了以其中的一場對其進行細微描述,選擇哪場也是在與受訪者的溝通下進行的,首先這場是相對最為完整的表演,其二,這場所選擇的是哈穆利亞最為經典的音樂。故筆者通過現場看到并攝錄下來的表演為對象,對其動作、音樂以及歌詞內容進行一個全景式描寫。筆者將演出過程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開場舞蹈、主體歌唱、結束部分。

圖5 哈穆利亞“沙漠之鴿”格納瓦組織的開場舞蹈(筆者攝于2015年)
1.開場舞蹈
表演一般有12人左右,最初,樂器尕布瑞并沒有出現,首先上場的是4位手持克恰克的舞者和兩位塔卜鼓鼓者,鼓者站在屋子的右側,給4名格納瓦舞者騰出一個較大的空間,他們穿著白色杰拉巴,頭包白色頭巾,鼓和克恰克的節奏隨著舞蹈動作的變化而同時發生改變。首先,4名舞者邊演奏著手中的克恰克邊圍城一個圓圈,在節奏的配合下,輕快地挪動著步伐,他們左右腳不斷交替,輕輕移動,但始終都保持一個圓形,在移動的過程中,他們不時做出一些動作,諸如蹲起、旋轉等,一般情況下在三次蹲起之后會緊接著一個快速的旋轉。
大約5分鐘后,開場舞蹈結束。
2.主體歌唱
隨后,舞者坐回了屋子右側的石臺上,而尕布瑞演奏者盤起腿來席地而坐,坐在了柏柏爾花紋的地毯上,四名樂者分坐其兩旁,從左邊起,分別是塔卜鼓演奏者、克恰克演奏者、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以及兩名以手拍打節奏的樂者。而原本的舞者坐在石臺上,也用手拍出節奏型,此時石臺上坐著6名格納瓦樂人,一齊配合歌者的演唱。如圖6所示:

圖6 主體歌唱部分的座位圖(筆者攝于2015年)
隨著半分鐘由克恰克、塔卜鼓、拍手等節奏融合而成的前奏,歌者邊彈奏尕布瑞邊開始了演唱,其實這時彈奏的尕布瑞還不能稱其為旋律,說是彈奏旋律不如說這時候歌者是在以撥弦的形式撥出固定節奏型,此時的歌聲在低沉的尕布瑞、聒噪的克恰克聲音、清脆的拍手聲以及穩定的鼓聲之配合下,顯得尤為穩重,又稍顯無奈。歌者兼尕布瑞演奏者唱一句,其他所有樂人重復一句,典型的一領眾和形式。據之后薩拉姆告訴筆者,一直重復的歌詞為:
yalwaliwaliy Allah.
意為:神圣的阿拉。
在循環演唱了兩分鐘后,一名身著白色杰拉巴,頭包藍色頭巾的男子阿里·歐巴那走上前去開始跳舞,藍色頭巾是當地柏柏爾人的特色,馬祖茲我們常常稱他們為藍色柏柏爾。他并不是黝黑的皮膚,而是較淺的柏柏爾人的膚色。旋律和節奏都沒有變化,這名藍色柏柏爾循環做著一些簡單的動作,他保持著緩慢的步伐,雙手時而在胸前不斷漫無目的地揮動,時而在身體兩邊大幅度擺動。隨著舞者的步伐,尕布瑞的旋律停止了,變成了純粹的節奏。
整個演出就在節奏、旋律、歌唱、舞蹈中來回變換,演唱方式一直都是一領眾合,而很典型,這種音樂風格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關。為了方便分析,筆者通過與樂人的溝通,為每首歌曲都起了名字,按照不斷重復的歌詞中常常出現的詞語。筆者將其中幾首列舉如下:

圖7 尕布瑞演奏者兼歌者(筆者攝于2015年)

表1 “沙漠之鴿”格納瓦表演的歌曲
單純看列表中筆者選取出的歌曲名稱,可以發現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音樂的主要內容是贊美安拉、追溯過往。這兩點內容很有趣,前者是確定自己的伊斯蘭信仰,后者是標明自己黑非洲奴隸的身份,這兩種類別的歌曲構成了“沙漠之鴿”組織的主要內容。不論是主唱的歌者,抑或是應和的樂人,在演唱這一連串的歌曲時,在這循環重復中,始終保持著平靜與安詳,與穆萊·布拉伊穆以及筆者后文中所提到的索維拉私密儀式中的格納瓦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其實,如果不是通過格納瓦樂人,就連馬祖茲都很難為筆者翻譯歌詞,對于之后索維拉格納瓦私密儀式,筆者與馬祖茲幾乎用了三個整天的時間去翻譯,原因就在于這些歌曲不是簡單的摩洛哥阿拉伯語,而是摻雜了其他的非洲語言,比如上面列表中的《蘇丹尼》就是格納瓦復合語言。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創造出已經不屬于阿拉伯語或者非洲語言的新詞。這些零星出現的詞使得分辨歌詞成了異常艱難的事情。他們沒有歌本,亦沒有曲本,為了在最初階段即對哈穆利亞的格納瓦有相對全面的認知,故筆者希望對歌詞有所記錄,最初筆者與馬祖茲一起聆聽錄制下來的旋律,希望將歌詞記錄下來,但很快就發現這樣所耗費的時間太多,其實歌詞本身并不復雜,因為哈穆利亞格納瓦音樂的重復循環,導致一句歌詞在一領眾合的情況下能夠重復很多次,但是馬祖茲和筆者卻每一句都要倒回去重復很多次才能將其準確記錄,于是筆者還是以馬祖茲作為中間人,通過格納瓦樂者的解釋,由馬祖茲翻譯給筆者,筆者再總結下來。但就是因為這項工作,讓筆者能夠對其內容有充分的了解,在這里,筆者將這場演出中對他們而言最常演唱的歌曲《蘇丹尼》為例,將歌詞記錄、展現出來:
Soudani yallah lah Soudani
Soudani yallah lah Soudani yallah
Soudani ya boaalam Soudani
Soudani ya boaalam Soudani yallah.
Soudani baba mimoun Soudani
Soudani baba mimoun Soudani yallah.
譯:(筆者整理的馬祖茲的解釋)
安拉,我們來自于蘇丹,
安拉,我們來自于蘇丹。
布阿拉姆,我們來自于蘇丹,
布阿拉姆,我們來自于蘇丹。
彌牟,我們來自于蘇丹,
彌牟,我們來自于蘇丹。
這是一首一領眾合式的分節歌,單獨看歌詞,有些詞會有些困難,不理解其意,不只筆者,包括馬祖茲對“布拉阿姆”“彌牟”亦不知其意。這是一首悲傷的歌曲,通常筆者會在格納瓦歌曲中發現一些詞語,以訴苦的形式對安拉、對他們的圣人、靈表達一種被迫遷移的創傷以及失去家園的痛苦,這首歌所表達的正是如此。薩拉姆告訴筆者:
每個詞對我們來說都非常有意義。每個音調都是反對奴隸制的證詞,同時(我們)向真主安拉、向圣人禱告,為了從鐵鏈中釋放出來。
這句話,也解釋了很多筆者所看到的表演中的動作和服飾,可以說釋放和奴役經歷是他們的共同創傷,也是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音樂的主要內容。再次回到《蘇丹尼》這首歌曲,蘇丹尼(“Soudani”)其實指的正是蘇丹(“Sudan”),此蘇丹并非現在的蘇丹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udan),而是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又稱為黑非洲)的廣闊的熱帶草原地區和幾內亞海岸的熱帶草原以北。這種格納瓦特有的語言,也證實了其在摩洛哥阿拉伯語的基礎上融入的非洲語言,也是導致歌詞在能夠熟練運用阿拉伯語、柏柏爾語、法語、英語的馬祖茲眼中都艱澀難懂的原因之一。歌曲每一句都唱到了他們的家鄉黑非洲,表達了一種悲苦的思念。而每一句的變化都是出現在他們訴苦的對象上,訴苦對象分別為真主安拉、布拉阿姆、彌牟。真主安拉是伊斯蘭教徒眼中唯一的主宰,無須贅言。布拉阿姆全名應該為穆萊·阿卜杜勒卡德爾·吉拉里(Moulay Abdelkader Jilali)或布阿拉姆·吉拉里(Boualam Jilali)。薩拉姆對筆者解釋道:
在摩洛哥我們稱其為穆萊·阿卜杜勒卡德爾·吉拉里或布阿拉姆·吉拉里。他是一個受歡迎的穆斯林圣人,是白色的超自然實體。
而他們另一個訴苦對象則是巴巴·彌牟(Baba mimoun),是來自于撒哈拉以南的超自然實體,筆者稱之為“靈”,彌牟所屬的顏色是黑色。真主安拉、布阿拉姆、巴巴·彌牟同時在一首歌曲中出現,并成為格納瓦群體所訴苦、傾訴的對象。歌詞提供給了我們三點信息:
1)格納瓦族群源自蘇丹(撒哈拉以南非洲,又稱為黑非洲);
2)歌曲表達的是思念家鄉之苦;
3)他們有自己的信仰體系,雖然他們堅稱自己為伊斯蘭教徒。
“沙漠之鴿”組織在主體歌唱部分演唱的歌曲正是表現了這種對族群起源的追溯以及對安拉的贊頌。
3.結束部分
“沙漠之鴿”組織的結束部分非常簡單,既沒有演唱,也沒有舞蹈,尕布瑞、塔卜鼓、克恰克以及手掌拍擊的聲音形成一個固定的節奏型,并逐漸減速,最終一齊結束。
五、所用樂器
在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音樂中,尕布瑞、克恰克和人聲形成了一個鮮明的音層結構。其中,尕布瑞營造出三種音色(a,b,c),克恰克營造出一種音色(d),人聲營造出另一層音色,筆者簡單呈現如下:
1)撥弦而發出的低沉的旋律音調;
2)在尕布瑞的駱駝皮上用指尖輕輕敲擊節奏產生的高/低音;
3)由系于尕布瑞頸部的“色塞拉”發出的共鳴的叮當聲③;
4)克恰克發出的稠密而連續的節奏型;
5)一領眾和的人聲:
馬勒姆(組織領導者)富有激情地大聲獨唱,召喚靈;
其他格納瓦樂人濃厚響亮的唱和。
以上五個音層結構是格納瓦音樂中最常見并持續時間最長的結構組合,也是能夠召喚靈的最為核心的結構。
1.尕布瑞
尕布瑞,是筆者對“guembri”的直譯,而“guembri”的拼寫按照的是采風對象索維拉馬勒姆阿克哈拉茲和哈穆利亞馬勒姆扎伊德·烏杰阿給予筆者的寫法,在摩洛哥進行田野工作之時,對于尕布瑞有諸多的叫法、寫法,筆者所得到的有以下幾種:gimbri,sintir,hejhoujis,hajhouj。可以說,尕布瑞是格納瓦的靈魂,是格納瓦音樂中唯一具有低沉的和音音域的樂器,筆者認為,它的聲音有些類似于西方的低音吉他,但其所呈現的音樂有著更深的對比度、深度和活力。尕布瑞是無品的低音三弦彈撥類琉特,據烏杰阿介紹,尕布瑞由單峰駱駝皮(現在有時候也會使用山羊皮)、羊腸(現在多以尼龍繩代替)以及木頭(白楊木、桃花心木或胡桃木)制成。尕布瑞的演奏技術同時包含了旋律性的聲音和敲擊的聲音,它如竊竊私語,又能引起悲傷;它贊美安拉,又召喚靈。現今,為了方便,很多尕布瑞的弦都由羊腸變成了尼龍繩。

圖8 格納瓦樂器尕布瑞(筆者攝于2015年)
2.克恰克
qraqab(又可記為karkabu,krakebs,chkacheks),筆者將其直譯為“克恰克”,是格納瓦音樂的另一件樂器。樂器的名稱是從阿拉伯語根Q-R-B中延伸而來,意為“接近”或“附近”。這影射了奴隸的回憶和他們痛苦的歷史,也與虔誠的信仰有關。粗略一看,克恰克就是簡單的金屬片,相對比尕布瑞,非常簡陋,兩個成對兒的大的金屬響板組合在一起,由多名格納瓦樂人一齊演奏,每個格納瓦樂人左右手各持一對兒,通常為2-6個樂人。克恰克約為25厘米左右,形狀有點像杠鈴,兩個金屬響板的頂端由金屬釘串在一起,另一端是自由、分開的。直桿兩段連接著兩個類似于鍋蓋的圓頂,連接在中端的繩子(或皮質帶子)圍繞著拇指并同時和其他兩個手指環繞,以方便在拍打后快速地將自由的那一端分開。每一對都被一個小金屬扣固定在一起,如此限制了每一對金屬響板能夠開合的距離,格納瓦樂人每只手握著一對兒金屬板,金屬板中間的繩子分別綁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上,基本演奏技術為通過同一只手兩個金屬板打開閉合產生的相互碰撞發聲,聲音是一種響亮的、金屬的“shakashaka”的聲音。

圖9 手持克恰克表演(2015年筆者攝于哈穆利亞)
3.塔卜鼓
塔卜鼓(tbal)是一種帶有一條較大的肩帶的大型的低音桶狀鼓,用于格納瓦儀式中的列隊游行環節和開場環節。這種塔卜鼓更適合于戶外場地的表演,故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其在戶外的列隊游行環節中擔任的角色。塔卜鼓有兩種奏法:
1)右手持一個鼓槌擊打加左手拍打的演奏法;
2)兩個鼓槌擊打的演奏樂。

圖10 哈穆利亞沙漠之鴿組織中的塔卜鼓(筆者攝于2015年)
結 語
在哈穆利亞的這段時日,筆者盡最大可能去觀察、記錄格納瓦族群及音樂,對于哈穆利亞的格納瓦,阿卜杜勒阿里對筆者說:
一個月前,一些來自蘇丹的人在尋找格納瓦村莊,他們之前去過索維拉。當他們來到哈穆利亞時,他們說我們的格納瓦是最原始的格納瓦音樂。
其實,在筆者看來,哈穆利亞的格納瓦指的既是一個族群,又是指這個族群所表演的音樂。格納瓦族群起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以奴隸身份在跨撒哈拉沙漠貿易過程中遷至摩洛哥東南部,并在奴隸制廢除后與當地柏柏爾人融合建立了自己的族群。格納瓦音樂為這個族群所表演的音樂,使用樂器為尕布瑞、克恰克、塔卜鼓,多為帶有歌唱、舞蹈的表演,內容以追溯起源、思念家園、贊美安拉為主。在哈穆利亞地區用于日常生活與薩達哈節日中。
在哈穆利亞之時,有時候筆者會聽到他們嘴里冒出的“Ismkhan”這個詞,穆罕默德·馬祖茲告訴筆者,這在柏柏爾語中即奴隸之意,他們會用其來形容自己,這令筆者十分驚訝,在筆者看來這個詞其實是一個帶有歧視之意的貶義詞,但他們卻時而用其來形容自己。扎伊德告訴筆者,他們并不在乎用帶有輕蔑之意的“奴隸”一詞來形容自己,相反他們努力所做的是將這個詞在他們身上轉變成一種積極的授權。其實,雖然筆者一直提到他們黑非洲的祖先,但真正追溯過往,在哈穆利亞格納瓦之祖先很可能來自于不同的地區、說不同的語言、屬于不同的民族,作為移居人口,他們是通過語言、物質文化、音樂等為自己塑造一個身份,創造出團結的族群精神。
注釋:
①由于當地村民完全不懂英語,對哈穆利亞村民的采訪均是通過咨詢人穆罕默德·馬祖茲的翻譯完成,以下村民所說的話為筆者通過咨詢人馬祖茲的口頭翻譯,進行一定的書面整理。
②跨撒哈拉貿易界于北非地中海沿岸國家及西非國家之間,是條從8世紀到16世紀末間重要的貿易路線。7世紀以后,阿拉伯人來到北非并控制了撒哈拉商道貿易。8-11世紀為商道貿易的發展時期,11世紀中葉-16世紀末為全盛時期,此后走向低潮。
③ 一般在尕布瑞獨奏時能清晰地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