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趙“建武四年”銘鎏金銅佛坐像“束發肉髻”辨析
文 圖 / 王趁意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后趙“建武四年”(338年)銘造像(以下簡稱建武四年造像)被認為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鎏金銅佛坐像。關于該造像的發式,一般被描述為“束發肉髻”,但事實真的如此么?為什么看起來更像是漢式道教的發髻?我們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結合畫像石、銅鏡等實物資料對其進行辨析。
“束發肉髻”也叫頂髻,原本是印度苦行僧的發式,后被納入佛教藝術體系中來。在印度,佛教藝術可分為犍陀羅與秣兔羅兩大風格。犍陀羅(漢代文獻中多稱為大夏)位于現今新德里西北方向的兩河流域,這一地區深受古希臘文化的影響。其特征在佛頭像及發髻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頭發紋路呈波浪式翻轉,向上或向后梳理,上、下發髻之間有明顯的束發線(帶),比較重視寫實。生活在犍陀羅地區的人們,更傾向于認為佛陀是現實世界里出類撥萃的優秀人物,人的本質要大于神的成分。他們是以描繪人的藝術手法來表現佛陀的精神世界,這種自然寫實的藝術造型,對人有著更強烈的感染力。秣兔羅在現今新德里東南部140公里的恒河流域,這一地區的信徒認為佛陀是天上世界的神,在佛像創作上,更多的是把佛陀當成超現實的神來描繪。秣兔羅風格佛像的發髻,是由眾多的螺旋形的小發髻組成,也被稱作“螺發(髻)”。秣兔羅地區的人們是把佛陀當成神來膜拜,在發髻的表現上,要彰顯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異像”,突出人對神的尊崇和敬畏。

秣兔羅風格佛像(《印度及犍陀羅佛像藝術精品圖集》,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
建武四年造像的發髻可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平頂高聳饅頭形,發絲向下梳理,余發似劉海式下垂,發梢線顯著,覆于寬大額頭上,中間有明顯的呈倒“V”字發際線,在前額正中把頭發分為兩部分,右邊六綹平行右旋,左邊六綹平行左旋,很規整。與印度佛像發髻相比,首先是外形上有很大差別,看不出明顯的異域特征;其次是印度佛像頭發,都是向后或向上梳理,上、下發髻之間有束發線(帶),而建武四年造像,其發際走向,都是向下梳理,且額頭正中均有發梢和分發的界線。此處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即表現的是不同的文化底蘊、背景,顯示出審美觀念的差異。
不難看出,建武四年佛坐像發髻既與鍵陀羅佛像儀軌相異,更難符合秣兔羅佛像儀軌,可見和印度佛像的發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類型,是一個獨立的藝術體系的產物,換言之,建武四年造佛坐像發髻是漢代道教發式的表像。除建武四年造像外,涇川、西安、石家莊等地出土的多件十六國時期銅造像與其屬于同一類型,囿于篇幅所限,在此僅將圖片列出以供進一步對比研究,未能一一詳考。上述造像盡管都多少具備了一些佛飾內容,但作為佛像的手式、坐姿、發髻特征卻體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特別是發髻特征顯示出漢式發髻群體的統一性,與印度佛像發髻截然不同。
山東沂南北寨村東漢晚期畫像石墓出土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其中左側戴峨冠、穿博服、俯身下跪者為孔子,其身后捧書冊者為孔子的弟子。對面站立身穿寬大袍服、手執曲龍拐杖者為老子,在該墓考古發掘簡報中也肯定了這一點。老子無冠,頭飾高聳饅頭狀發髻。眾所周知,老子被奉為道教的鼻祖,其發型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道教的流行式樣,高聳饅頭狀發髻被后世認為是典型的道教發式,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發式和建武四年造像頭上的發髻應屬于同一類型。
山東微山縣兩城鎮西漢畫像石墓出土有“西王母”畫像。西王母穿衽領大衣,雙手收于袖中,肩部伸出粗大肩羽,末端生出云氣紋,呈正面端坐狀,右側有“西王母”銘文。西王母頭上無冠,頭發分兩部分梳理。正中部分是饅頭狀高聳發髻,上下梳理,發痕清晰可見,頭上臥一神鳥。從西王母的發髻上,似可找出和建武四年造像發髻的內在聯系與傳承關系。

后趙建武四年鎏金銅坐佛側面發際

甘肅涇川出土十六國銅佛

西安出土十六國佉盧銘銅佛

石家莊出土鎏金銅佛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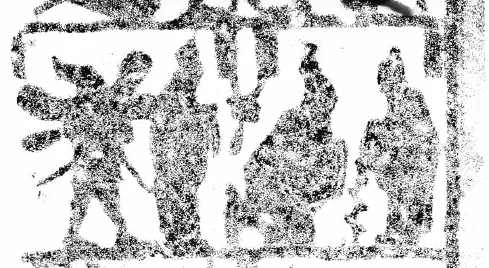
山東沂南北寨村畫像石墓出土“孔子見老子”畫像石拓片

山東微山縣兩城鎮畫像石墓出土“西王母”畫像石拓片
四川安縣出土漢魏搖錢樹上的樹葉佛畫像,其造型也為正面端坐,頭有雙弦線圓形背光,發髻呈上下重疊雙層、向下梳理,上唇有上翹八字鬍髭,大眼隆鼻,身穿圓領披肩式博衣,右手上舉施無畏印,左手握博帶舉至胸前,臉頰兩側各有勻稱的三個圓圈。若以微山縣兩城鎮畫像石墓“西王母”畫像為基準,與此尊樹葉佛像作為參照,兩者的發髻如出一轍。加上建武四年造像,上述發式的特征都是二層臺布局、向下梳理,除細節稍有區別之外已趨于同一風格,與印度佛像肉髻有本質的區別。
另外,三國吳永安五年(262年)銘神獸鏡上神人發式引人關注,5位神人皆不戴冠、束饅頭狀高發髻,這與沂南北寨村東漢晚期畫像石墓出土“孔子見老子”畫像中老子的發髻完全相同。如圖所示,鏡鈕下方兩尊主神像大眼隆鼻,大耳橫眉,唇上有髭,頭上梳饅頭狀發髻,肩生掃帚狀雙羽,端坐狀。鏡鈕兩側的主神可以看得更清楚,皆為典型的饅頭形發髻。這五位神人的發式很容易讓人將其與建武四年造像的發髻聯系起來。
山東沂南北寨村漢畫像石墓“完璧歸趙”畫像拓片中,藺相如和孟犇二人均穿褒衣博帶,佩長劍,藺相如著峨冠,孟犇頭上無冠。值得注意的是孟犇的發髻,可以清楚的看到孟犇頭發被束結為上下兩層,下部為大饅頭狀,上部為小饅頭狀,腦后似有巾幘。梳發痕跡為上下走向,這樣的漢代發式在畫像石里不勝枚舉,并與建武四年造像發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沂南北寨村畫像石墓出土“完璧歸趙”畫像中的藺相如和孟犇

四川安縣樹葉佛像(何志國先生 提供)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得愈發清楚,如果說在此之前所舉各例神人發式和建武四年造像發髻還僅僅是類似的話,那么孟犇頭上的發式已經和建武四年坐像發式別無二致,說明東漢三國時期,這種神人的發髻有著自己的模式,其源流與印度佛像的所謂“肉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類型。
孔子在《孝經》中提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因此發髻(型)在兩漢以前是中國人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身份等級和社會地位的象征。歷史上(清朝除外)漢人的頭發再長,也不能輕易剪毀,只能束發成髻、梳發為辮或披發在肩,如果損毀了頭發,將是大逆不道的事。若王公貴族犯了法,毀傷其頭發就是對他的懲罰。于此,兩漢還專門設立一種刑法叫做“髡”,即割發。此外,在中國歷史上,還有割發代過(命)的典故,如曹操馬踏麥田以割發代命的故事。漢魏兩晉之際,道、佛文化進入了全面相互交融的歷史時期,在漢式神人形象的基礎上,在完善、充實道教造像時,會有一個對印度佛像借鑒的過程,例如巫鴻在探討包括畫像石在內的漢代藝術中的佛教因素時,認為這些因素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功能和意義,僅僅反映了漢代藝術對佛教題材的偶然借用。但是在印度佛像眾多的藝術要素中,“肉髻”要素是最不容易被漢人借用、接受的,截至建武四年,中土尚沒有發現一例真正的印度佛像風格的肉髻造型,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搖錢樹樹葉佛的所謂“佛”發髻,和印度佛像肉髻完全相悖,卻和西王母的漢式神仙發髻完全類同,其中的內涵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三國吳永安五年(262年)銘神獸鏡(《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16》)

日本京都博物館藏佛獸鏡(【日】樋口隆康:《古鏡》,新潮社,1979年)
日本京都博物館藏畫紋帶佛獸鏡,經王仲殊先生考證,認為其流行時期為三國西晉,是東渡倭國的中國人所造。鏡上十尊佛像,不管是坐佛或是立佛,其佛飾特征或坐蓮座,或執蓮花,或穿“U”形衣,甚至頭后有典型的印度式蓮花項光,基本上已完全“佛飾化”了,但唯獨發髻仍有六尊佛像固守著漢式高聳雙發髻造型。這一固守,首先守的是漢人的國家形象,其次守的是孝,是對父母的尊重。無獨有偶,在日本學術界命名的一組流行于三國中晚期的三角緣佛獸鏡上的“仏像”(佛像),其發髻為雙髻或三髻,與《古鏡今照》一書中所收錄銅鏡上的“雙髻老子圖”相比較,表現出典型的漢式發髻類型,很難看出與印度佛像的束發肉髻有何關聯。

日本學術界命名的雙髻或三髻佛像造型(【日】福永伸哉等:《三角緣神獸鏡》)

雙髻老子圖(《古鏡今照》,文物出版社,2012年)
通過對建武四年造像“束發肉髻”的辨析,再結合此前對“禪定手印”的溯源和“結跏趺坐”的考證,基本可以作出推斷:建武四年造像是一尊借鑒佛教因素(披了袈裟)的道教造像,是東漢以來老子化佛觀念演變的必然結果。
從東漢中晚期開始,道、佛二教進入了以“老子化佛”為背景的互為融合、滲透的歷史進程。印度佛教造像藝術元素開始被道教造像所借用,這是一條循序漸進的,由少及多、由淺入深發展的軌跡。我們決不能因一件造像有了部分佛飾因素,或手執無畏印或穿件袈裟,或有了背光,或坐蓮花座,或手執衣角等單一元素,就忽略其他諸如形體、手勢、服飾、坐姿、發式等沒有佛飾特征的因素,不加分析考證,強行貼上“佛”的標鑒,這種緣木求魚的論證方法,是不合邏輯、有失縝密的。
坦誠地講,建武四年造像穿了件袈裟(通肩大衣),確實是印度佛飾文化的一部分,但把這些佛飾內容無條件地外延,卻是與事實相違背的。建武四年造像的坐姿、手式、發髻是漢魏以來漢式神仙文化體系有機的組成,換言之,古人是借用了佛教因素來塑造本土道教造像,而非佛教造像,這恰恰體現的是“老子化胡”的思想內涵。原來對建武四年造像的“佛”的命名,是名實不符的。至于這尊道教造像為什么要穿一件佛教袈裟來裝扮自己,正是需要我們今后要結合老子化佛的歷史背景認真考慮的,并通過對造像基座上的云氣紋、三個神秘的圓孔以及發愿文的考證,最終揭開建武四年鎏金銅造像“他是誰”的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