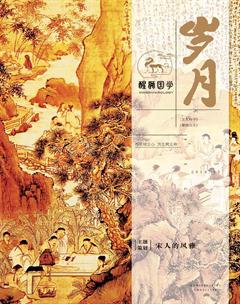利字當(dāng)頭——韓非的統(tǒng)治術(shù)
商鞅只是法家的實踐家,真正將法家治國實踐上升為理論的,是韓非。
公元前233年的一天,秦國首都咸陽的中央監(jiān)獄,來了一位大員,他是秦國的廷尉,也就是司法部長李斯。李斯此時已經(jīng)成了秦王的心腹大臣,權(quán)傾朝野,炙手可熱。
李斯來到監(jiān)獄里的一個監(jiān)室,這里關(guān)押著他的老同學(xué),大名鼎鼎的韓非。
這位韓非本來是韓國王族,在韓國時,一心想著使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為韓王出了很多好主意。但是昏庸的韓王有眼無珠,拒絕采納韓非的主張。韓非被邊緣化,壯志難酬,寫下很多文章抒發(fā)胸中的苦悶,宣傳自己的政治見解。其中很多名篇如《孤憤》《說難》等等,看文章的題目就知道韓非郁悶得很。不料秦王嬴政,也就是那位后來成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看了韓非的文章后,竟然成了他的大粉絲。一邊讀著文章一邊由衷地贊嘆:“哎呀!能見見這位,和他成為朋友,真的是死而無憾啊!”
為了得到韓非,秦王竟迫不及待地發(fā)兵攻打韓國。韓王迫于秦王的威勢,只好將韓非送到了秦國。秦王見到了韓非,相談甚歡。韓非的同學(xué)李斯出于嫉妒,就想辦法陷害韓非。由于韓非建議秦王先不忙著攻打韓國,而應(yīng)該首先攻打趙國。李斯就進了讒言,說韓非畢竟是韓國人,心還向著韓國,不可靠。秦王一怒,就將韓非投入了監(jiān)獄。
韓非已經(jīng)成了階下囚,李斯還不放心,怕秦王再赦免韓非,他畢竟十分欣賞韓非的才華呀!只有盡快將韓非置于死地,才能防止翻盤。秦王確實很快就后悔關(guān)押韓非,但是就在他下達釋放命令之前,李斯來到了監(jiān)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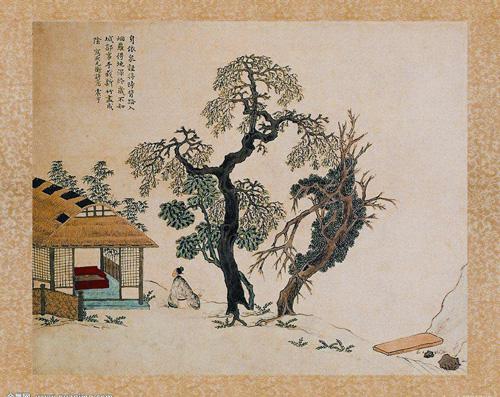
李斯來到監(jiān)獄,自然不是探望老同學(xué),更不是營救老同學(xué),而是給老同學(xué)送來一杯毒藥,逼老同學(xué)自殺。可嘆韓非,此時還央求李斯給自己一個申訴的機會,見上秦王一面。李斯怎么可能給他這個機會!李斯正是來斷送這個機會呀!毒酒下肚,七竅流血,一代思想天才,就這樣悲慘地送了命。
李斯當(dāng)然無論如何也想不到,25年后,他也從這里被押赴刑場遭受腰斬,死得比韓非還慘。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一位最無情最清醒最冷靜又最悲哀最倒霉的思想家,那就是韓非。韓非思想的無情清醒冷靜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人性的分析。他分析了人性之后,得出了一個結(jié)論,那就是,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每個人都是利字當(dāng)頭。
利字當(dāng)頭
在韓非看來,人的本性都貪得無厭,爭名逐利是生活的唯一動力,普天下都圍著一個軸心轉(zhuǎn),這個軸心就是一個“利”字,人和人之間的全部關(guān)系,歸根結(jié)底都是算賬關(guān)系,整個社會其實就是一個大生意場。
例如他說:“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備內(nèi)》)
做轎子的盼人富貴,做棺材的盼人死,并非是做轎子的心地善良,做棺材的心腸狠毒。人不富貴,誰還買你的轎子?人不死,誰還買你的棺材?因此希望人富貴也好,希望人死也好,動機都在一個利字,無所謂善和惡。
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diào)布而求錢易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則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亦云也。(《外儲說左上》)
雇人耕田的地主,對雇工好吃好喝,熱情招待,工錢優(yōu)厚,不是因為這個地主心眼好,是慈善家,而是這樣厚待雇工,雇工才能好好為他耕田。反過來,雇工賣力的耕田,也不是由于勤勞敬業(yè),而是好好工作,才能獲得優(yōu)厚的待遇。
韓非的意思是說,不能用仁義友愛這類道德標準來理解人們行為的動機,人們的行為根據(jù)全都在一個利字。社會上是這樣,官場上更是這樣。
例如他非常欣賞田鮪教導(dǎo)兒子田章的話:“主賣官爵,臣賣智力”。
政治就像做買賣,國君出賣官爵,臣子出賣智力而已。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shù)之所出也。”
臣子盡心盡力和國君交易,國君用高官厚祿和臣子交易。君和臣的關(guān)系,并非父子之親,完全是一種利害盤算。
其實就是父子關(guān)系,在韓非子看來也沒有什么親可言,也不過是一種算賬關(guān)系。
“父母之于子也,產(chǎn)男則相賀,產(chǎn)女則殺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韓非子·六反》)。
父母和子女,生男孩就奔走相告地慶賀,生女孩呢,居然把她殺掉了。男孩女孩都是父母的親骨肉,為什么對男孩那么好,對女孩那么狠呢?原因就在于父母考慮的是長遠的經(jīng)濟利益。這樣看來,父母對孩子,也不過是一種算賬關(guān)系。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yǎng)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yǎng)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己也。”(《外儲說左上》)
兒女小的時候,父母不太疼愛,長大了肯定怨恨父母。兒女成人后對父母不盡孝心,父母肯定也責(zé)罵兒女。父子之間親骨肉,不也完全以利益為轉(zhuǎn)移嗎?
父母和子女這樣,夫妻之間又怎樣?
“衛(wèi)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韓非子·內(nèi)儲說下》)
衛(wèi)國有一對夫妻跪在神靈前虔誠地祈禱,三跪九叩后,妻子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仁慈的神啊,請保佑我們平安,賞賜我們一百個小錢吧!”
丈夫在一旁埋怨:“怎么求這么一點點錢?”
妻子回答:“太多了,你就會拿去討小老婆了!”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外儲說左上》)
人和人之間,對他有利,再疏遠的人也可以走到一起,對他有害,即便是父子也會生分結(jié)怨。
更可怕的是,利也好,害也好,都是經(jīng)常變幻不定的。天下就沒有確定的客觀的道理,一切都圍繞著關(guān)系而轉(zhuǎn)移。人心難測,世道兇險,是非善惡美丑都是相對的。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筑且有盜”,其鄰子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韓非子·說難》)
宋國有位富翁,天下大雨把他家的墻淋塌了。他的兒子說:“如果不把墻修好,恐怕夜晚有賊來偷東西。”
鄰居的老父也這樣說。到了晚上,果然家中財物被偷。這位富翁呢,贊賞自己的兒子聰明,卻懷疑財物是鄰居的老父偷的。
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wèi)君。衛(wèi)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余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后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dāng)而加親;見憎于主,則罪當(dāng)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后說之也。
衛(wèi)國有位彌子瑕,是位帥哥。衛(wèi)國的國君有點斷背傾向,同性戀,喜歡上了彌子瑕,彌子瑕因此就成了衛(wèi)君的寵臣。一次,彌子瑕的母親病了,彌子瑕十分著急,也沒向衛(wèi)君請示,就私自駕著國君的專車連夜趕回家看望母親。按照衛(wèi)國的法律,私自駕駛國君的專車是嚴重的罪行,要判處刖刑,也就是砍掉腿和腳的酷刑。但是衛(wèi)君聽說這件事后,非但未懲罰彌子瑕,反而贊揚他:“真是個大孝子呀,為了探望母親不惜冒遭受刖刑的危險。”
還有一次,彌子瑕陪伴著衛(wèi)君到果園里游玩。彌子瑕摘下一顆桃子咬了幾口,覺得這桃子特別甜,就不假思索地遞給了衛(wèi)君。衛(wèi)君非但沒有責(zé)怪彌子瑕不衛(wèi)生,不尊重國君,反而贊揚他:“彌子瑕對我真好啊!這么甜的桃子自己舍不得吃,留給我吃。”
后來彌子瑕色衰失寵,一次得罪了衛(wèi)君。衛(wèi)君就不客氣了,居然翻起老賬:“這個家伙真是討厭。曾經(jīng)私自駕著我的專車外出,還居然給我吃他吃剩的桃子。真惡心!”
同樣一個人,同樣的行為,前后的評價卻判若兩人。人心難測如此,不是很可怕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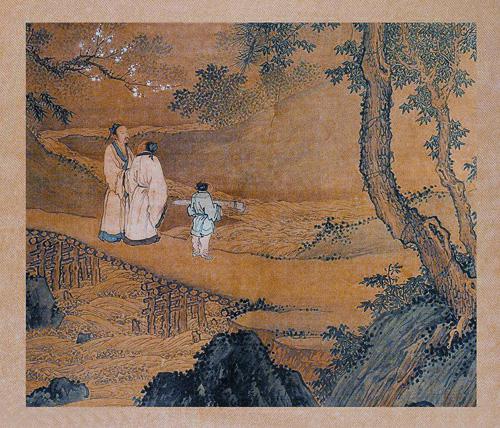
犀利,冷靜,清醒,真的好像無可辯駁。溫情背后是冷酷,美妙隱藏著丑惡。韓非最能直面這個殘酷無情的人生。因此后來劉備曾經(jīng)讓自己的兒子讀韓非,認為韓非的著作能夠“益人神智”,使人清醒。
韓非的看法一方面絕對是大實話,另方面又太絕對,把整個人間全都浸泡在冷冰冰的利害計較的寒流中。
從對人性分析出發(fā),韓非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學(xué),他的政治學(xué)換句話說,就是一種統(tǒng)治術(shù)。
編輯/書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