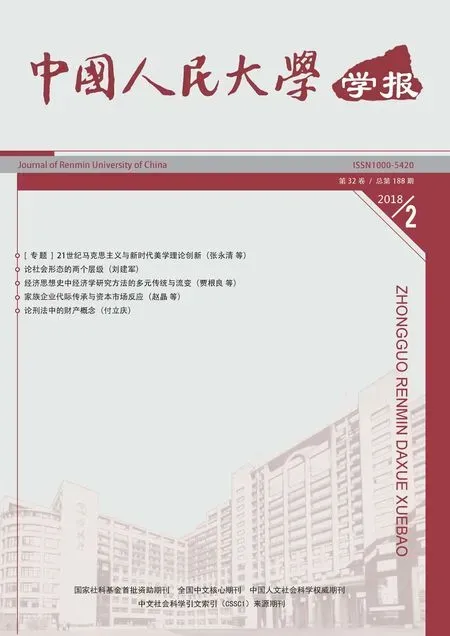國家治理的階段性演化:一個貫通的政治學模型
柳亦博
國家主體視野下的治理邏輯變遷問題,始終是國家治理的研究重心,學者們不僅致力于發掘那些能夠使國家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成功地轉化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基礎性理論*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 Verso/ New Left Books, 1983, pp.5-8;Joyce, Patrick, & Chandra Mukerji.“The State of Things: State History and Theory Reconfigured”. Theory and Society,2017,46(1):1-19.,同時也關注那些維系并幫助國家走向繁榮的應用性理論*Garner James Wilford.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1928,pp.238-246.。由于國家的內涵在不斷更新,治國理論也在相應地變化,一代代學者從不同角度剖析國家治理的運行,提出了主權論、法治論、契約論、階級論、法團論、多元論、互動論等諸多解釋。*Abrams Philip.“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1988,1(1):58-89.面對卷帙浩繁的文獻,唯有對底層的治理邏輯抽絲剝繭,才能發現隱藏在國家形態更迭背后的兩次具有繼起關系的治理邏輯“轉向”——由疆域主義轉向生產主義,進而轉向制度主義。歷史地看,兩次治理邏輯轉向均率先發端于官僚系統,隨后漸次蔓延至社會。雖然治理邏輯的出現有先后之分,但無優劣之別,生產主義并不比疆域主義更高級,只不過比前者更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且后一種邏輯總是以前者為基礎,在整體演進上呈現出階段性、非還原性特征。隨著20世紀末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權和治權不再高度合一,在世界范圍內國家治理實踐中,僅憑制度建構無法維持國家治理有序運行,這引發了學界對傳統國家治理的普遍反思——如果不理解丹麥本身是如何由家族制過渡到現代國家的,又如何幫助其他國家“到達丹麥”呢?*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21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審慎地考察當前學界流行的幾種代表性國家治理理論不難發現,它們或多或少存在解釋的盲區,例如:“出走—尋回”框架要重塑韋伯式國家,但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韋伯的理論卻頻頻陷入失靈窘境;新加坡的國家治理經驗雖然可以納入“強—弱對峙”框架的闡釋范圍,但面對泰國或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問題時,這一框架則顯得蒼白;而“中央—地方”框架適用于言說日本的央地博弈情境,但用它解讀印度的現狀就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國家間權力結構、制度形態、政府規模、經濟體量上的差異,都會削弱一個理論模型解釋力的廣延性,但我們不能因畏難而放棄在普遍性意義上揭示大多數國家治理邏輯演化的努力。本文力圖在政治學視角下建構這樣一個貫通的模型。
一、第一次轉向:由“陷阱”進入“軌道”
今天人類棲居的世界被兩百余個國家和地區劃分開來,幾乎所有國家都是以16世紀的現代國家為雛形搭建起來的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的壟斷性、強制力、權力主張等制度性特征,奉行一種“制度主義”的國家治理邏輯。*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Politics as a Vo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78.其實,國家治理進入制度主義階段是相當晚近的事,在此之前,國家治理是被長期統攝在“生產主義”或“疆域主義”邏輯下的。因而,要想理解當下的國家治理及其未來朝向,必須在梳理歷史的基礎上考察曾經發生過的治理轉向過程。疆域主義是一個巨大“陷阱”,雖然它是國家治理邏輯演化的起點,提供了國家認同和存續的必要空間,但也令大量國家被長期困在領土紛爭中難以脫身。這是因為,在治理關注國家生產和創新能力之前,國力與領土面積被認為是線性相關的,國家治理會自覺走向開疆拓土。通常來說,疆域主義階段的出現即標志著國家機器已經啟動,治理行動正在形成。許多學者在定義國家這一概念時都強調了“疆域”的重要性。邁克爾·曼定義國家為“一定領土內”壟斷具有約束力和永久的立法權的實體*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Volume 1.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37.,必須在其領土上才能建立科層制和軍隊的機構組合。米格代爾則稱國家為一個權力的場域,而且必須在其“領土內”方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才能代表著生活于領土之上的民眾。*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變與相互構成》,6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而在韋伯對國家的經典定義中也出現了“特定疆域內的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這樣的描述*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78,p.54.,指出國家暴力準備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統治別的領土和共同體的政治權力”,因而國家享有的專制性權力及其官僚、軍隊展開行動的合法性邊界均在國境之內。*曾毅:《超越韋伯主義國家觀——從亨廷頓到米格代爾》,載《教學與研究》,2016(7)。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可能表現為多種形態,例如古希臘的族群國家化模式、古羅馬的族群擴張模式、歐洲中世紀的宗教—封建整合模式以及東亞的軍事帝國模式,但是在國家形態異質性的背后則是疆域主義治理邏輯的同一性——它們都是在掠奪土地、擴張版圖中實現了內部凝聚和實力增長。當然,擴張也是一柄雙刃劍,歷史上很多帝國因戰爭拖累致使自身長期處于以戰養兵、不戰即亡的惡性循環之中,其他的帝國則因過度擴張以致統治技術與所轄領土出現了不匹配的現象,最終被自身臃腫的體量壓垮。
領土完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果國家治理的全部實質被疆域主義所局限,那么就容易忽視某些重要的價值,最終走向“霍布斯式的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293.結合考古證據,政治學與歷史學研究普遍認為亞歐大陸上早期國家發展的一大動力是指向暴力的。一個國家戰勝另一個國家,隨即產生了掠奪、擴張、等級和奴役。蒂利認為,歐洲君主發動戰爭的需求驅動了歐洲的國家建設,因此戰爭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國家發展。不止6世紀至7世紀墨洛溫治下的高盧紛爭頻仍,更早期的亞述、波斯、羅馬、秦、漢、拜占庭等大帝國的統治歷史也均可濃縮為一部擴張領土的戰爭史,封君、采邑、屬臣、世襲都是疆域主義的衍生物。*Greg Melleuish.“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State: A Historical Critique”.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2012 (112).疆域主義階段的國家壟斷了戰爭,并著力宣傳戰爭的重要性。如果一個國家與其鄰邦均秉持疆域主義,那么接壤之處就成為兩國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其中任何一方試圖擴張都會誘發戰爭。“戰爭造就國家,國家又發動戰爭”*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169.,這就是蒂利所描述的這一階段國家建構的過程,唯有確立界碑之后方能開啟下一階段的大門。對于國家治理而言,國土防衛將始終處于最優先處理的任務清單上,一旦遭遇外敵入侵,絕大多數國家不會綏靖退避而是啟動動員機制予以還擊。然而,戰爭未必總是發展的助燃劑,有時反而拖曳著整個國家及其周邊地區都陷入戰亂的泥潭,與此有關的大量實例見諸中東、拉美、非洲南部的近代歷史之中。
當然,有少數國家基于種種原因能夠最終跳出疆域主義陷阱,其治理的重心也得以迅速轉向生產,開始強調戰爭擴張以外的生產能力,即進入我們定義的“生產主義”階段,也有學者稱其為發展主義或發展型政治。福柯采用了與眾不同的命名方法,為了區別于“城邦名義的治理”及“國家名義的治理”,他將這一階段稱為“牧領治理”,其特征是“精英統領”以及“生產與知識緊密結合”,此時的“權力”也將不再表現出壓制性或消解性,而是釋放出生產性。*Michel 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Inqui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777.盡管稱謂各異,但描述的階段大致相同,即普遍在生產能力和組織協調的延展性技術(extensive technology)*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1: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7-94.上獲得提升之后,國家政治權力愈發集中的階段。雖然疆域主義階段也會組織國家生產,但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或軍工業,生產主義階段則強調惠及民生的公共品生產。文化的不同導致國家治理方式的差異化表達——那些殘留著封建屬性的國家,會因市場交易的蓬勃而逐漸聚合,在聯系中逐步開放并發育出官僚、衡平、晉升以及常備軍征募制度,隨后政策重心將移向免稅減役、輪作休耕、興修水利、鼓勵生育;對于那些已經立憲的國家而言,則可直接建設大規模社會分工—協作體系,將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都圍繞在“如何解放生產力”這個核心問題上。
布羅代爾將生產主義階段的人類活動描述為“仍停留在或淹沒在物質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8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在這一階段,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默認一個觀點:只要生產了足夠豐沛的農產品,則政權無虞。生產的富余創造了更多交易,這種聯系編織出了細密的社會網絡,令政治結構愈發穩定,因而生產與統治是相互充權的;相反,若是天災導致生產停滯且政府無力賑濟,則政治也很難穩固。在農業社會,黎民只求豐衣足食,并不關心這個國家由誰來統治,也不關心國家是大一統還是封建,治理終歸是由“肉食者謀之”。生產技術(農耕、紡織、冶煉、馴化)的革新則備受矚目,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生產主義階段的娛樂商貿業從業者普遍不被尊重,因為他們的工作無法產出新的物質產品。在脫域化出現之前,國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系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兩者之間所出現的對抗遠未激化到足以撕裂國家的程度,此時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決定了其國民能否安居樂業,更關系著政權的穩定。對生產主義政權威脅最大的無疑是生產性危機,它有可能將剛剛脫離戰爭泥潭的國家重新拖回疆域主義階段,諸如洪水、干旱、疫病或過度攫取自然,對于國家初期的脆弱生產能力都會造成致命的打擊。*參見戴蒙德:《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170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重視生產能力,首先激活的是國家官僚系統對生產技術的熱衷,隨后這種熱情蔓延開來,社會生活開始關注那些自我生產和轉化的行動,強調生產中更具外部性的創造力。進入生產主義階段的國家治理必須不斷提高國民物質生活水平,否則就要面臨各種反對浪潮。換言之,生產主義階段的國家會被發展邏輯鎖死,治權的合法性基礎需要在快速發展和國民福祉提升中尋找,此時的國家就仿佛進入了一個“軌道”,無論速度快慢都只得在既定路線上前進。其后,無論國家治理的邏輯如何轉變,均需建構在國家生產能力持續提升的基礎上,那些面臨經濟崩潰、產業凋敝的政權難言穩固。這幅圖景在之前的疆域主義階段是不可想象的,彼時的統治者們更關心土地和頭銜,這意味著稅收和權勢*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149.,而生產主義階段的統治者們則顯然更關注對生產資源和統治機構內部職位的爭奪,哪怕任期有限,哪怕充滿競爭和問責壓力。
如果治理長期滯留在疆域主義階段,國家難免因戰亂與動蕩導致國力枯竭,因此國家治理的第一次轉向其實是源于人類社會演化進程中避免同類相殘的自然選擇,成功轉向的國家走上生產主義道路。進入生產主義階段后,幾乎所有國家都將被鎖死在發展邏輯的“軌道”上——生產技術提高養活了更多人口,而人口的密集又成為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Boserup Ester.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A Study of Long-Term Trend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我們在此之所以使用“幾乎”一詞,是因為人口增長對生產力的發展作用機制十分復雜,可能引發效果截然相反的斯密機制或馬爾薩斯機制,并不是每一次人口增長都會帶來技術進步。*參見趙鼎新:《加州學派與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載《學術月刊》,2014(7)。與技術進步相呼應的是政府也表現出對物質進步的普遍興趣,而國民們則更是強烈依賴于這種發展帶來的福祉提升。因此,很多國家可能長期滯留在疆域主義階段,但極少會在生產主義階段止步不前,除非外敵入侵打斷了其正常發展。生產能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建構一個各領域都井然有序、預期穩定的社會被列在政府工作清單的首要任務一欄,此時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第二次轉向,而這次轉向出現了兩種可能:轉向制度主義,或者轉向結構主義。
二、第二次轉向:由“軌道”抵達“模板”
多數轉向結構主義的國家,不幸步入了另一個死循環,因為結構主義強調國家和社會的功能性因素,認為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的關鍵在于優化結構,這種整體性視角使得所有行動者都被結構調整所遮蔽了。結構主義者彼得·埃文斯就試圖揭示“不同的國家結構會造成不同的國家行為能力”這一規律*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p.11.,現在看來這種所謂的“規律”是虛假的,事實證明結構相同的國家無法保證具備同樣的治理能力。換言之,結構主義在理論層面存在著自反性,它無法回答“既然結構至關重要,那為什么兩個國家在權力、資源、制度和文化結構幾無差別,但在治理能力上卻表現得判若云泥(如菲律賓的政治結構完全復制自美國,但美國政治對話的工具是語言,而菲律賓使用的卻是子彈)”這個問題。唯一合乎結構主義邏輯卻又非常荒謬的答案只能是“人種差異所致”,當然,種族主義的結論早已為全世界所唾棄。在實踐層面,結構主義的國家治理總會懷著“不斷迫近最優結構”的決心,在反復調整結構的過程中開始分別賦權并進行區域性分工。這種賦權與分工帶來的是公共性的持續擴散,于是治理領域出現了更多主體,它們在結構化的治理系統中獲得的任何發育,都意味著國家權威的弱化,最終導致諸如“強地方弱中央”(西班牙)或“強社會弱國家”(印度)的治理失衡,嚴重時甚至會撕裂國家共同體,將其重新拖回疆域主義陷阱中。進入結構主義階段的國家并不是沒有機會步入正軌,若能在治理衰退之前成功轉向制度主義,則依然有可能發育出“市場經濟”與“法治”。
不同于結構主義的歧途,制度主義在實踐中獲得了極大成功。制度化的過程與米歇爾斯提出的“寡頭政治鐵律”*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pp.204-208.不同,它是由市場力量而非政黨權力推動的,除非掌握治理權力的組織領袖刻意追求一種牧領式治理。普遍意義上,國家生產能力的發展會導致產業結構向工業轉型,而工業化和官僚制的發育則造就了一個行政國家,這也正是制度主義存續的最佳空間。制度主義將國家視為一個基礎性的制度存在,為其他政治制度的生長和運作提供了政治法律的依托、強制性權力保障和必需的政治制度空間。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的每一次生產技術進步,都會極大地惠及社會底層民眾,從而萌發樸素的平等思想,而支持這種平等轉變為現實的正是隨后的一系列制度建構。在嵌入論看來,作為社會的一個蔓生機構,國家具有既脫胎于社會之中又高懸于社會之上的獨特性,在如何規范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方面,近代學者們給出了答案——將國家的權力關進制度的鐵籠,即建構一種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米格代爾將現代國家的目標定義為“制定有約束力的規則來管理公眾的行為,或者至少是授權其他專業機構在特定領域制定那些規則。通過這些規則,國家官員就可以采用強制手段按其意愿強行處理”*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變與相互構成》,6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制度主義在近代影響甚廣,米格代爾之前的眾多學者,如斯密、韋伯、洛克、托克維爾、亨廷頓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構想了一個制度覆蓋的國家。雖然他們的理論并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承襲或引申關系,但在他們各自的理想世界中,不難發現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旨歸,即對基礎性秩序的追求。追求社會穩定性催生并強化了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建構行為,在工業革命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上地區性的制度差異也確實成為各國或欣欣向榮或殘破衰敗的主要原因。*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Foreword by Francis Fukuyam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pp.145-160.無論精英主義還是民主主義、新現實主義還是多元主義,均可被歸為“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都是試圖通過制度建構去形塑、控制、引導或改造國家,所不同的只是價值取向。制度主義試圖將國家建構成一個被制度高墻環繞的、特殊且自治的共同體*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309.,由法律、規章和道德構成的制度是國家建構自身和維持組織穩定的支點,也是一切治理行動開展的前提。
強大的國家生產能力為統治者們錨定了一種秩序穩定的政治環境,他們高呼“必須有商品”,因為社會的存在依賴于這些商品的不斷生產和消費。*馬爾庫塞:《工業革命和新左派》,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6。關于第二次轉向的出現,一種解釋認為,人的經濟關系并非始終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39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而是隨著交易活動重要性的不斷上升,市場經濟從社會中“脫嵌”進而支配了社會關系*張銜、魏中許:《如何破解人類合作之謎——與黃少安教授商榷》,載《中國社會科學》,2016(8)。,最終交換生產剩余的沖動催生了脫域化現象,國家為了規范這種人和物的流動性,于是開啟了制度主義。另一種解釋是,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人們所依賴的生活資料中實體物質的比重不斷下降,對制度的需求則不斷上升,國家治理重心向立法轉移,一個依賴制度的行政國家逐漸崛起。無論何種解釋,其共同點在于當國民生活中的物質需求基本滿足之后,國民渴求在穩定的規則體系下調整資源分配,生產主義將迅速讓位于制度主義。在制度理性的推動下,立法行為從最初旨在規范交易行為的市場領域廣延至公共領域,并最終統攝了全部的公共生活,將國家治理塑造為“一套在特定領土范圍的社會中施行的更加非個人化的公共規則體系,人們通過一套復雜的制度性安排和機構運用這一體系”*Roger King.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ology.London: Chatham House, 1986,p.30.——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法治國家,法律規約所有的社會行為主體,即使對最強大的政治參與者也具有約束力。現代國家的出現與制度主義誕生在時段上大致重疊,二者的意涵也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任劍濤認為,在國家的發展中,那些能將“工業革命、市場經濟與立憲國家”貫通起來者可發育為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凡不能貫通者則發育為畸形的現代國家,而其未明言的“貫通的方式”,正是用制度來覆蓋和聯結生產、交易與政治活動。*任劍濤:《工業、市場與現代國家》,載《思想戰線》,2016(3)。
制度主義當然不是治理邏輯演化的終點,自20世紀中后期至今,諸如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都對其存在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制度主義存在刻板僵化、反應滯后、扼殺創新、易陷悖論、制度維護成本過高等弊病。同時,制度主義在意識形態兩極化中卷入了論爭漩渦,不同陣營的政治學者陷入了“無法說服對方,也不會被對方說服”的拉鋸戰。爭論加劇了對抗,導致了制度建構實踐陷入一種極化的純粹追求中,而這無疑是異化的肇始。意識形態之爭的勝者會化身為制度主義的標準“模板”,主流治理觀點認為所有現代國家都應以此為參照設計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該模板被唯一化為“民主制”,并在全球掀起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的國家利用制度形塑了一個“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處在中心位置的國家具有制度賦權的支配性力量*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5-7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而民主制度又被這些處在中心支配地位的國家所吸納,于是邊緣國家只有兩種選擇:或是通過非民主手段以某種依附方式參與民主世界,或是為爭取自身的獨立和發展而進行激烈斗爭。*圖海納:《行動者的歸來》,18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但無論何種選擇,想要成為被國際社會接受的一員,最終都不得不向這個制度模板臣服,自1974年至今已有92個國家使用了這個模板,但至少32個國家經歷過民主崩潰。*劉瑜:《兩種民主模式與第三波民主化的穩固》,載《開放時代》,2016(3)。
三、逐漸清晰的第三次轉向
近半個世紀以來,學者們為超越制度主義提出了許多思路,如新制度主義學派就是在反思制度主義的基礎上誕生的。但遺憾的是,新制度主義沒有產生出統一的理論內核,反而出現了取向的碎片化。又如,歐洲學者為了解決歐盟在共同體治理中遭遇的諸多困境,提出了所謂“元治理”理論*S?rensen Eva, and Jacob Torfing.“Making Governance Networks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Through Metagoverna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 87(2): 234-258.,其本質即在超國家共同體層面“尋回國家”*Bob Jessop.“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 Remarks on Regulation,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7, 4(3): 61-81.,在理論脈絡上與之前埃文斯、斯考切波等學者同出一流,所不同的是元治理強調在大共同體中突顯一個“上位治理者”(即英國)對整個治理網絡的監管功能,隨時準備著對治理失靈進行治理*Louis Meuleman.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Metagovernance of Hierarchies, Networks and Markets: The Feasibility of Designing and Managing Governance Style Combinations.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8.;而“尋回國家”則強調改變當時行為主義“國家過時論”一統天下的學術狀況,認為多元理論、功能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等行為主義統攝下的國家治理在“社會中心”的方向上走得太遠,是時候要求國家重新回歸到中心位置了。*曹海軍:《 “國家學派”評析:基于國家自主與國家能力維度的分析》,載《政治學研究》,2013 (1)。為了實現國家的回歸,必須在治理中強調國家的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追求公共建構的國家能力意涵。但是“尋回國家”關注的是如何建構國家而非如何治理國家,揮之不去的對抗邏輯令社會與國家始終徘徊在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中。至于多中心治理、多層級治理和網絡治理等,皆與元治理理論有著相似的背景。顯然,這些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無法令國家治理掙脫制度“模板”的束縛,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來涵括當前國家治理的實踐及其趨勢。
盡管制度主義治理一度是善治的代名詞,成為政治文明與國家現代化的標志,但這種對制度主義的美好想象只持續了不足20年就宣告結束了。制度主義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20世紀后期興起的行動主義,以拉圖爾、圖海納、費埃德伯格為代表的一眾學者在各種社會運動中察覺到了“行動者歸來”現象,并將這一過程描述為“行動者的歸來并非天使的歸來,而是老鼴鼠的歸來”*圖海納:《行動者的歸來》,3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這意味著行動者的任務不是救贖,而是為了打通邊界、實現合作。行動主義嘗試著回答制度主義無法解釋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制度同構的兩個國家(例如英國與牙買加)為什么會表現出迥異的治理水平。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復雜,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多元化問題,所以制度預設所形成的按圖索驥式治理無法有效回應瞬息萬變的現實問題,最終國家治理系統不得不尋找一種有別于制度主義的變革思路。正如張康之教授所強調的那樣,“行動是要解決問題的,而不是必然要恪守某些普世性的原則”*張康之:《對合作行動出發點的邏輯梳理》,載《學海》,2016 (1)。,也即是說,要打破制度之于行動的優先性。行動主義在事實上改變了“依法治國”的傳統格局,在法理與治理的碰撞中,唯有能夠更好地提供國家治理服務的行動者才能在民主化浪潮中贏得更多支持,從而在眾多行動者中顯現自身,組織和領導集體行動。行動主義的興起,必然引發一系列國家治理的結構性變革,如去中心化和去主體化*張康之:《論合作治理中行動者的非主體化》,載《學術研究》,2017(7)。,也就使得國家自我建構中幾乎所有的環節都與制度主義下的國家理論截然不同。
除了剖析制度主義隱含的謬誤,行動主義還指出了其在組織化運行中的弊病——枯燥。枯燥導致的倦怠問題其實早已有之,我們在20世紀的官僚體制中經常可見,制度主義下的人過著一種幾乎機械的政治生活,他們只需按規章行事而無須自主思考,很快就被乏善可陳的煩瑣日常生活磨掉了熱情與責任感。此時的人已經走到了“行動者”的反面,成為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很容易表現出一種平庸之惡,而通過行動創新帶來的一系列不期然結果,在對抗了制度呆板的同時也抑制了重復的單調,這恰恰令國家治理系統重現生機。隨著治理主體多元化、新社會運動勃興和大量行動者的歸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公共行政*張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動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社會治理*張乾友:《行動主義視野中的社會治理轉型》,載《江漢論壇》,2016 (6)。、組織理論*姜寧寧:《論組織研究的行動主義轉向》,載《學海》,2016(5)。以及社會運動理論*Silas F.Harrebye.Social Change and Creative Activism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Mirror Effect.Hampshire :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25-43.均表現出了朝向行動主義轉變的趨勢,國家治理也隨即呈現出第三次變革趨勢:由制度主義轉向行動主義。這次的“行動”絕不是要喚醒一個無情碾壓個人自由的“碎顱者”,它不像曾經的社會革命那般暴烈,而是旨在塑造一個將人們從層層的制度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碎鐐者”,在整體上表現出倫理的特征。換言之,行動主義并不是對抗性政治的沃土,它并不以組織各種形式的抗議、抗爭或革命為目標,而是尋求以創造式行動化解原有的矛盾結構。同時,行動主義也不是制度化政治的延續,而是一種具有探索進取精神的實驗性政治,而這種探索建立在德政的基礎之上,可視作軸心時代的哲學啟蒙與18世紀的法學啟蒙之后世界范圍內的一次新的倫理啟蒙運動。
從行動主義的視角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馬克思認為“國家形態終將消失”——正是這一預言令他飽受后世爭議——因為全球化強勢地將國家理論整合到一起,這一過程令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在形式上保持了相對的一致性,全球化對世界所做的終極改造即消除國家共同體。但是,將這種終極改造變為現實的,應是大量實質性和建設性的國際行動,以及由此所帶來的“行動主義”思潮。需要強調的是,行動主義(activism)與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截然不同,行為主義主張以個體行為的加總來理解集體行動,行動主義則更關注國家在回應公共問題時所展現出的具體能力,要求打破制度框架之于治理行動的重重束縛,強調“干中學”的持續漸進和靈活權變,強調“非期然后果”帶來的革新可能。行動主義是一種旨在有序地組織合作的治理變革構想,它無關20世紀后期的新自由主義,亦非一次對“去國家化”或“無政府主義”的過激回退(rolling back),而是治理行動者在對制度主義國家實踐進行理性的反思之后,基于理論推導與實際觀察兩方面所形成的最終判斷。通過考察20世紀末以來歐洲、東亞、東南亞等地崛起的非資源型國家的治理發展歷程,會發現它們均掙脫了制度主義的牢籠,沒有將自身嵌套在“比較優勢理論”所形塑的傳統世界體系之中,而是著力提升國家自身的行動能力,從而在近20年間引導國家走向繁榮。
四、階段性演化模型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站在歷史質的層面抓取國家治理演化的總體性特征,從而建構一個用以解讀國家治理邏輯轉向謎題的貫通模型——“階段性演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國家治理的階段性演化模型
在該模型中,國家治理的演化遵循著“疆域—生產—制度(結構)—行動”的理路,其中每一次轉向都伴隨著治理模式的嬗變。羅斯托曾基于西方國家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傳統社會、準備起飛、騰飛、成熟和大眾消費”五階段模型*Rostow W.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用以闡釋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的模型關注的則是政治學視野中的國家治理演化。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歷時開放的、時序單向度的模型,它遵循的不是福柯所反對的“歷史還原主義”,而是對歷史主義的反思性闡釋。因此,為了避免該模型重蹈梅耶(John Meyer)文化演進模型的“時代錯序”(historical anachronism)之謬,我們刻意保留了該模型在時間線上的開放性,即其中任何一個階段均不會對應于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或社會形態,也不會有時間跨度的下限,即某一個階段既可能是白駒過隙的一瞬,也可能蔓延千年。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定義的開放性意指治理階段起始點和轉折點在時間軸上的長度擁有很強的彈性,但這些“階段”在順序上是不可逆的,也無法跨越。國家治理行動的外延見表1。

表1國家治理行動的外延
“階段性演化模型”之所以是階段性的,是因為每個階段的國家治理都需要充分的內構和衍生,方能順利過渡到下一個階段。例如,日本的疆域主義階段是經由幕府統治的封建時代歷經一千余年,才通過明治維新逐步開啟了生產主義階段。新加坡則大不相同,它在經濟基礎、政治形態、地緣格局、時代背景以及領袖特質等因素的輻輳之下,國家治理從疆域主義快速進入了制度主義,僅耗時不足十年。而在如此高速奔跑的過程中,新加坡亦未能躍過生產主義階段,它照樣需要大力發展石化、造船、機械和物流等特色產業。當然,其中還涉及殖民問題,但這只是促進性而非決定性因素。又如,早在西歐諸國的貴族們控制土地和剝削農民的中世紀一千余年之前,古代中國就已出現了生產主義的國家建構主張,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秦完成了已知版圖內的國家統一,制定了規約全國的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標準。對于綿延兩千余年的古代中國(公元前2世紀的東漢至18世紀的清朝)而言,無論是其國家生產的基本特征,還是政治制度的性質,都沒有跳脫出生產主義的國家治理邏輯。但是,在隨后的兩個世紀中發生的變化,遠超此前兩千年變化的總和,且這種快速變革的步伐一直持續到今天。因此,國家治理的邏輯演化是階段性的,但不同國家在每個階段停留的時長可能千差萬別。
其次,該模型是不可逆的。即是說,特定階段所出現的治理問題無法通過回退到前一個階段的方式來解決,只能將矛盾暫時轉移而已。例如,當民主制度出現問題時,政府無法通過市場結構性調整或者擴大生產規模來減少民主不暢所積累的矛盾,也不可能通過制造一個比“失業”更可怕的外部敵人來長期轉移國民視線。生產主義面臨的諸種問題需要更好的制度設計來解決,制度主義面對的問題則需要通過有效的治理行動來解決,在這個模型中,只能向前進,無法向后退。對此,俞可平指出:“盡管總有一些學者懷疑人類社會的政治進步是否不可逆轉,盡管就某個國家或地區來說,政治進步的進程可能會暫時中斷,甚至出現某種倒退,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以及就某個國家或地區的長遠發展趨勢來看,人類的政治進步確實是不可逆轉的。”*俞可平:《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義》,載《學術月刊》,2017 (4)。階段性演進模型的不可逆性決定了疆域主義永遠是基石,這一階段不只是確立國家的空間邊界,同時也是確立內部各子系統權界、厘清自由與責任的過程。但是,在其后的發展中,疆域話題就從國家治理的中心游移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組織生產、發展市場。開啟了生產主義階段,對于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而言,就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再之后就是建構一種綱領性的、能夠將國家的一切活動都納入進來的“制度”,國家一般會選擇當時世界上普遍認為最正義的制度改造自身。進入制度主義階段,意味著國家行動極大地依賴于法律,并且會盡一切可能去維護這一規則體系,即便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
最后,這個模型適用于解釋大多數國家(但不是所有國家)的治理演化,更不具備拓展至超國家共同體或微縮至社區治理的廣延性,其解釋力無法覆蓋所有國家,尤其是被殖民后又獲獨立的國家。同時,這一模型在解釋治理模式時不涉及任何機制問題,因為機制研究掩蓋了治理的行動過程,將預設與結果視作是符合因果邏輯的,好似一旦制定了數種機制,所有制度就會相互銜接、自動運行一般。機制研究往往對解釋一國內部各區域間制度嵌入程度的差異性不感興趣,對同一機制下公共政策不同程度的扭曲也視而不見。因此,我們提出的階段性演化模型關注治理邏輯嬗變以及隱藏在結構與制度背后的治理行動。與邏輯嬗變息息相關的是國家治理重心的遷移,每個階段治理重心如表1所示,這種重心遷移一者是受外部的社會復雜性變化的拉扯,再者是受內部官僚系統變革力量的推動,其目的在于引導治理者實現最終的目標。與直覺相左的是,變革力量最早往往不是出現在歷史學家們強調的社會“邊緣”地帶,而是萌芽于“中心”區域的政府內部,這是因為官僚系統是制定和開展治理行動的最前沿組織,能夠充分接觸信息、及時獲取反饋,最有可能具備康德所謂的實踐理性。
國家治理的邏輯轉向過程非常復雜,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量變積累引發質變的新舊更迭,更難準確找出所謂臨界與亞臨界狀態,因此沙堆模型是不具解釋力的。不同國家治理邏輯轉向的差異性極大,耗時千年者有之,不逾十載者亦有之。邏輯之間的轉換往往不是在劇烈變革和動蕩中完成的,而是以漸進、消解、融合、覆蓋或疊加等多種形式的復雜組合呈現出來。舉例來說,由自然空間向政治空間演變的過程中,領土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不僅具有功能性,更擁有權利內涵。當國家治理的重心轉向生產主義時,政府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拋棄疆域主義,迄今為止尚未觀察到任何一個國家會在無視領土邊界的情況下,安然組織國民從事勞動生產、征稅、基建或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基層動員行動。即使在進入工業社會之后,領土依舊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任何試圖徹底摒棄疆域主義的努力仍然需要承擔撕裂國家的巨大風險,因為國家的公民認同是構筑在領土認同之上的,缺乏認同的治理是很難啟動的*周光輝、李虎:《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構建一種更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載《中國社會科學》,2016 (7)。,相反,一旦擁有了民族或文化上的認同,即使不接壤,也可成為一國領有的飛地。
貫通模型說明了國家治理階段性轉向是層累的過程,后一種治理邏輯必須構筑在前一種邏輯的地層之上,需要前者的所有知識和養料。即是說,需要學術界提供豐沛的知識生產,也需要儲備充足的物質基礎,任何主動(如理想主義的“躍進”運動)或被動(如殖民者的高壓強迫)尋求的“跨越”,或者任何試圖打破貫通模型繼起關系的嘗試,均會遭遇失敗。例如,那些“顏色革命”成功后沒有及時回頭補課的國家,無一能維系其民主政體,最終會因治理系統與社會現實的嚴重不匹配而導致國家走向衰落。
將中國的現實放置在貫通模型中不難看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和民主法治建設的完善,中國正處于國家治理“雙重轉向期”——制度轉向尚未完成、行動轉向業已開啟。更復雜的是,中國的行動轉向是在除馬克思主義外的行動哲學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摸索前行,如果不夠審慎的話,這種前行極容易陷入一種決定論,即特定的制度結構與行動主義轉向存在線性關系,這種線性關系是虛假的。事實上,回歸結構是無助于治理走向行動主義的,結構化的行動不能謂之行動,它只是選擇取舍、權衡利害,會將中國引向“計算社會”的深淵。而且,能夠支撐結構的是制度秩序,在當前中國基層政府的“穩定邏輯”和“規劃性政治”夾逼下,制度秩序很難為行動主義提供生存空間。中國要順利度過國家治理的“雙重轉向”并最終進入行動主義階段,既需要在中央政府層面堅持深化服務型政府的改革,又需要在基層治理中靈活使用“發包”“借道”和“吸納”等彈性的治理機制*黃曉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機制轉型與社會組織發展》,載《中國社會科學》,2017 (11)。,利用體量和規模優勢快速在多個層面上積累治理經驗,通過大量的實踐喚起知識界對宏大理論的關注,最終將經驗與理論結合起來,從而開創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話語體系*李友梅:《中國社會科學如何真正從“地方”走向“世界”》,載《探索與爭鳴》,2017(2)。,用自己的治理理論回應和指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