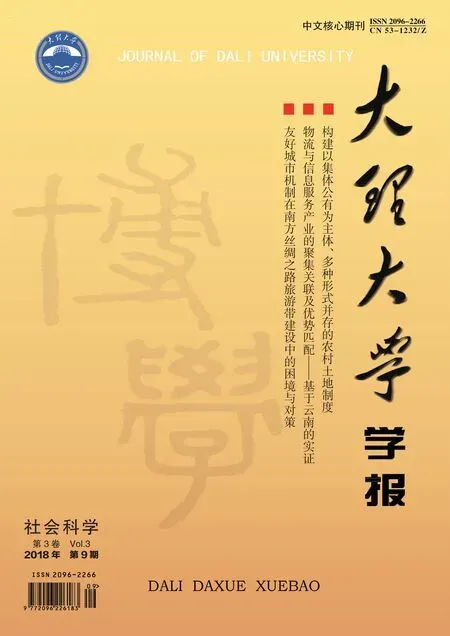父母訓導的意蘊、原則及實施策略
馬月成,楊 斐,李學才
(滇西科技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云南臨滄 677000)
盡管不同群體與兒童的互動模式、教養理念存在客觀差異,但是父母在兒童撫育方面有著本質的相同點——支持和促進兒童健康成長和發展。在整個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父母的支持和限制構成了維護和促進兒童幸福與發展的兩大主要維度。本文探討的是在不損傷和削弱兒童的好奇心、主動性和自我效能感的前提下,父母如何通過家庭系統內部規則和控制,發展兒童自我控制的意識和能力。
一、訓導意蘊的回歸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將“訓導”一詞理解為使用懲處來應對被管理者或兒童的不當行為。事實上,在英語中“訓導”一詞discipline的詞源是disci?ple,意指兒童或弟子。在漢語語境中,“訓導”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指明清時期的學官名,二指教育訓誡。因此,作為家長若要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提供適宜有效的訓導,他們就需要重新審視訓導原本的涵義。
第一,訓導的目的是期望兒童的行為表現符合他們的撫育者或教師的標準。訓導作為兒童建構行為規范、價值觀和信念系統的手段和策略,有助于兒童成長為優秀的人。
第二,訓導涵括著兒童的自主選擇,訓導有助于兒童逐步學會控制他們沖動的情緒和行動,使得他們在行動前通過分析推理比較和權衡,進而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訓導也有助于兒童“去自我中心”,兒童經過權衡和選擇可以知覺到他人的需求,進而發展出適宜的人際交往技能。
第三,訓導作為教育手段,其實施必須是積極的、合理的、適宜的、適度的,訓導的使用要建立在維護兒童自尊的基礎上。作為父母可以試問自己:“我的期望是否超越了兒童的年齡及其能力?”“與兒童互動的過程中是否包括了過多的禁令和否定”。
第四,訓導必須建立在理解兒童及其需求的基礎之上。有時兒童問題行為的出現,實質上是他們期望引起成人關注或是表達自我需求的方式,此時成人的訓導很容易成為兒童不良行為的強化手段。
最后,訓導通過家庭系統內部的規則和契約進行建構。這些規約可以使家庭中的每個人了解行為準則及行為的后果,有助于兒童責任意識的建立。在民主型家庭系統中,規約由家庭成員集體協商制訂,尊重和平等有助于讓兒童意識到規約的制訂是為了維護他們的自由。當兒童的某些行為問題出現時,父母不應該向兒童展現他們盡職的權威,而是基于平等協商和給予兒童表達和辯論的機會。
二、父母訓導的價值指向
父母作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可能支持和滿足了兒童生理的、社會的和心理的特殊需求,使兒童得以健康的發展;也可能因父母消極的教養態度和行為使兒童生理、心理的發展處于危機和挑戰中。由于社會文化、家庭及個體存在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很難提出一種具體而普適的訓導方案。因此,下文主要探討父母訓導的價值指向,以期能幫助父母重塑發展兒童及家庭系統本身的訓導理念。
(一)禁止使用虐待身體的懲罰和侮辱性的責罵
人類的社會交往常常缺乏理性的指導,人們傾向于拒絕和懲罰非合作行為的另一個人,并試圖強制他人服從社會規則和規范非合作人〔1〕。在家庭系統內部亦是如此,父母常常把毆打虐待和責罵訓斥作為令兒童順從其意愿的有效手段〔2〕。反觀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家長對兒童采取毆打和責罵的訓誡方式似乎也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親子關系研究專家比格納(Jerry K.Bigner)指出:“父母反應的強度和懲罰的程度常常與兒童不當行為頻率的逐步升級有關。”〔3〕
更為嚴重的是,父母的體罰和責罵不僅難以抑制兒童的不當行為,甚至會對兒童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嚴重長期的消極影響:首先,嚴厲的教育方式容易傷害到兒童稚嫩的身體,尤其是在父母處于極端的情緒狀態之下(如發怒),如2016年中國青年網就曾報道一起“父母體罰女兒致死反捆手腳手段殘忍”〔4〕的極端虐童事件;其次,父母的強迫、嘲諷、批評、否定甚至威脅、恐嚇容易對兒童自尊的發展造成極其消極影響,兒童為刻板限制束縛,使得他們在未來缺乏足夠的信心自己做出決定,兒童會認為自己在個人問題上沒有發言權甚至不該有發言權;另外,懲罰容易對兒童的行為模范和記憶造成消極強化作用,兒童長期遭受嚴重的身體虐待,他們容易將暴力行為和責罵理解為解決沖突的有效手段,并導致他們在學習、生活的各個發生人際沖突的場域頻繁地、習慣性地使用暴力行為〔5〕。在精神分析學家眼中,個體早年遭遇傷害,極為可能會在其成年后的親密關系或其他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而事實上也確有研究證實——“父母體罰存在代際傳遞性”〔6〕。因此,作為父母,有必要考慮采用更加適當的訓導方法,如正強化、負強化、代幣獎勵等更為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理解兒童行為的動機
的確,心理對行為具有支配和調節的作用,因此很多家長將兒童的不當行為推演、解讀為:不當行為源自兒童蓄意傷害他人的動機。而事實并非如此,兒童的不當行為通常來自他們生活場景的模仿和學習,而這些行為表現吻合其行為邏輯,如他們曾經看到那些具有暗示性或者不被懲罰不良行為。當兒童表現出不當行為的時候,如果父母將兒童的不當行為視為惡意攻擊,進而對兒童產生失望、憤怒的情緒,這將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如果父母責備或處罰自己不認為有過錯的兒童,不僅不能使兒童從過錯中獲得教訓,反而容易引起兒童對父母的不信任和敵意。若是父母將角色轉變為孩子的伙伴,嘗試著以理解、關愛的態度面對兒童,引導兒童參與秩序的恢復,使他認清所發生事情的本質。這樣不僅可以降低和減少雙方的敵意,也更為容易采取更加理性適宜的方式,使兒童萌生三思而后行的責任意識。
顯然,家長將注意力集中在問題行為本身并不利于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家長首先應該理解兒童不當行為時的動機。給兒童自我表達的機會,認真地傾聽兒童的言語和非言語表達,并將自己對兒童行為的感受反饋給兒童。父母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問題,憤怒和沮喪常常妨礙了成人正確的理解、思考和解決問題,成人報以關愛、尊重兒童的態度有助于成人移情和理解兒童行為產生的原因。父母也可以嘗試引導兒童用自我澄清和移情訓練的方法幫助兒童認識不當行為的原因,從而幫助兒童對其行為做出必要的調整。
(三)給兒童思考和行為選擇的機會
父母頻繁地為兒童做出選擇和決定,不僅不利于兒童自主性的培養,也不利于兒童責任感的養成。如果父母過度地越俎代庖為兒童提供全部答案或是解決方案,甚至代替兒童選擇,只會養成兒童的依賴性。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專制型家庭,父母常常宣稱為兒童的幸福著想,實則源于父母自身的恐懼,他們常常對兒童發出禁令和威脅(如你必須……,不準……),兒童在此過程中深感壓迫、氣憤、恐懼、不被信任、無能為力,選擇的剝奪同時扼殺了兒童的獨立精神和自我知覺。
將行為的決定權讓給兒童并讓其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有利于兒童從中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父母在謹慎輸出自己觀點的同時,也認真考慮兒童的需要和觀點表達,并讓兒童感受到被關注、接納和支持,那么父母的支持性態度和積極回應就會傳達給兒童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你能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務。當兒童有機會自己做出決定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兒童就更容易獲得自理能力、成就動機以及較高的自尊水平。父母的溫暖關愛和合理控制,也有助于青少年自主探索各種角色和意識形態,進而促進其同一性的發展和形成。
(四)理解并尊重兒童的個體差異
兒童只有試圖擁有自己的世界,發現自己,認識自己的想法,創生作為自我主體的世界,想表達有著自身原因的行為,他才會有存在感、自尊感、幸福感。而父母的支持、尊重與理解使得兒童獲得安定愉悅的情緒以及發展自我的內驅力和能力〔7〕。因此,將個體差異看作個人成長中有趣、積極的因素,接納和理解兒童的個體差異,也就是尊重兒童作為主體自己的世界。
很多家庭重視所有成員的同一性或一致性(如父母要求弟弟也應該像哥哥一樣熱愛打籃球),“一元化”的發展觀、人才觀往往將差異化的價值觀、意見、想法或自我表現方式視為思想和行為的偏差甚至問題。在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典籍中,充斥著大量的祖訓家規,祖輩和父輩期望兒童在家規的訓誡下產生一致性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模式,并形成相同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顯然,對于一個有思維能力和自主意識的兒童來說,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同一性的要求的家庭系統中,他們的自主性、獨立精神和自我意識將會遭到扼殺。當兒童面對家庭系統中同一性的要求時,兒童可能會為避免沖突而否定自我;他也可能不愿遵守同一性的規則而堅持自我,這些兒童常常表現出反抗父母權威、違背父母的意愿行事,面對行為結果,兒童也往往不會承認是自己的問題,而將錯誤推卸給他人。如果父母頻繁地采取過于強硬的態度或責罵、體罰,很容易造成兒童與父母的情感脫離。
(五)維護兒童自尊
父母運用訓導策略必須清醒認識到,訓導應該以促進兒童發展及維護兒童自尊為基本條件,訓導的目的并非是基于或者加深兒童的恐懼和羞愧感。如果父母通過不當行為(如斥責、體罰)來糾正和改造兒童行為,帶來的后果是促使兒童內心產生消極體驗(如羞愧、內疚),兒童的自尊將遭受嚴重損傷。頻繁長期的負疚感會使兒童建立起“壞孩子”的自我形象。而且通過打擊、諷刺、自責、內疚、羞恥建立起的兒童內部控制,實質上不僅有礙于問題的有效解決,而且也不利于兒童自律行為的形成和發展。
規則的學習在兒童認知結構和社會性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規則”不僅意味著行為限度,同時也蘊涵著行為權力。適當規則的學習和使用,有利于兒童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發展,也可以使兒童構建起個人界限和被許可的行為限度。另外,規則應該是可協商的考慮兒童需要的,可協商的規則使兒童認識到行為時可以思考、協商,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都要得到重視。而且規則協商的過程增加了兒童理解這些規則需要家庭系統內部所有成員匹配適合的需要和行為,進而發展出兒童的行為責任意識。
(六)創設關愛溫暖的家庭氛圍
父母與兒童的互動方式和行為通常基于滿足他們所感知到的兒童的需要,父母通過滿足兒童需要,為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做準備。在養育兒童的過程中,父母無條件地向兒童輸出他們的注意、傾聽、理解和關心。尤其是在嬰兒時期,面對嬰兒的需求和表達,母親及時的回應容易讓嬰兒產生呼風喚雨的“全能感”。然而,那些制訂毫無協商余地規則的父母,通常對孩子要求過于嚴苛和專制,常常使用體罰來壓制兒童批判性思考能力進而強化對孩子的監控。父母如此嚴厲教養的后果,一方面,父母建立起對兒童的需要置之不理的強迫性的規則,如果兒童期望得到父母和規則的認同、接納,規則就會成為助長兒童依賴性的推手;另一方面,兒童反復長期地遭受情感虐待(如罵孩子:“你這個蠢貨!”“你太讓我失望了”),他們就會獲得痛苦的情感信念,進而建立起對家庭和親密關系的消極自尊感受,而這種情感傷痛就像藥物成癮越想減輕痛苦,結果越加讓人感到愧疚和痛苦。養育過程中,不管是基于父母專斷性地判斷兒童的需求,進而表達出的注意、傾聽和要求,還是依據兒童自主表達需求基礎上提供的照料和回應,父母無條件的愛傳遞給孩子的信息是——你愛我是因為我自己,這將有利于兒童健康自尊和積極人格的形成和發展。
三、父母訓導方法的應用分析
如果家庭訓導的理想是培養獨立、自尊、自我控制和勇敢的兒童,那么家庭系統內部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有關人類行為和親子交互方式的研究豐富和推動了家庭教養方法的發展,在父母與兒童交互過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可能運用了不一樣的訓導方法,但就結果而言都達到異曲同工的效果。
(一)行為矯正
行為矯正技術源于行為主義理論,強調行為發生與行為背景環境之間的關系,理解和控制行為由刺激物的性質或情境條件決定。行為矯正的理論基礎是:①任何行為都來源于學習;②行為的后果會強化或者削弱行為發生概率;③如果行為的結果得到強化,將支持或鼓勵了該行為;④某一情景中獲得的行為方式可泛化到類似情景中;⑤經強化建立起來的行為模式,如果后續缺失強化作用,會發生“消退”作用。行為矯正法的理論假設是——通過行為結果的反應∕反饋來調整(增強或者削弱)兒童的行為。使用行為矯正技術,父母可以通過對兒童做出的期望行為加以強化,對非期望行為進行弱化,進而塑造兒童認可的行為。父母通過回應兒童的方式,有意無意地激勵和塑造兒童的某些行為。
根據操作性條件作用原理,如果兒童的行為方式實現了其所期望的目標(如得到父母肯定、夸獎或是物質獎勵),那么兒童將習得這個行為方式。強化包括兩類:正強化和負強化。正強化指的是當兒童表現出期望行為后,給予他一個令其愉悅的強化物(獎勵),以增加該行為再次出現的概率。如兒童摔倒自己爬起來,然后得到父母的表揚或是物質獎勵。負強化是指當兒童表現出期望行為時,消除一個令其感到厭惡的刺激。如兒童某日拾金不昧將錢物交給警察,于是家長免去兒童當日的家務勞動。有時候,兒童表現出的非期望行為如果沒有得到強化也會逐步消退,如果父母多次忽視了兒童的某些不當行為,這些行為可能會終止。因此,應對兒童的非期望行為(如大聲吼叫),如果父母不做出任何反應,兒童的大聲吼叫可能慢慢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父母面對兒童的大聲吼叫采取責罵、體罰的手段,可能會使懲罰變成兒童不當行為的強化物。如果兒童采取不回應的方式應對父母的責罵,父母的責罵也會得不到強化。另外,決定行為矯正是否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強化物使用的頻率。通常來說持續性的強化具有短期效應,容易使兒童習慣化;而間歇性強化更容易獲得最優的強化效果。如代幣獎勵方法,根據期望事件發生的頻率或次數累計“代幣”,一段時間以后兒童可以根據代幣獎勵規則進行兌換那些他所期望獲得的物品(如玩具或是周末到動物園游玩)。
(二)社會學習
傳統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在解釋個體語言、情感、態度、社會規范等學習現象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如不能解釋個體新行為的獲得、個體如何從榜樣那里獲得完整行為模式等等。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認為:“如果社會學習完全是建立在獎勵和懲罰之結果的基礎上的話,那么大多數人都無法在社會化過程中生存下去。”〔8〕班杜拉通過著名的“Bobo Doll Experiment”有力地證實了即便是沒有獎勵或強化物時,學習依然可以發生。這一理論可以有效解釋,兒童如何習得建立在家庭系統內部規約基礎上的那些適宜行為。社會學習理論研究認為兒童通過觀察學習或者模仿他人學會暴力、侵犯與合作等社會性行為,如2013年兒童模仿動畫片《喜羊羊與灰太狼》中暴力畫面燒傷小伙伴的新聞報道〔9〕。社會學習理論對個體社會化的發生(如人們如何獲得社會角色、態度、價值觀、行為方式等)亦有很強的解釋力。兒童通過對成人或同伴的行為進行模仿,進而獲得相應的行為。另外,社會學習還可以引發“社會性促進效應”(Social Facilitation)〔10〕,即個體即便未產生新行為,亦可以通過替代學習強化、削弱或是消除已有的行為方式。后續研究表明,如果兒童的模仿行為得到獎勵,類似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就家庭系統內部而言,民主的家庭規約是基于家庭所有成員集體協商制訂,同樣對規約的踐行也應該適用于所有家庭成員。班杜拉認為:“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宮’是孩子成長的內部環境。”因此,父母作為兒童成長的重要他人或者說“第一任教師”,必須謹慎對待自己的行為并以身作則。首先父母要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和睦的家庭精神氛圍,在和諧民主的家庭中,幼兒切身體驗到家庭成員間的相互理解、接納和關愛,家庭成員通過自己的行為向孩子傳遞愛和尊重,同時家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也為幼兒樹立了榜樣。在家庭愛的氛圍中,孩子產生安全感、歸屬感、價值感和自尊感,進而助于他們將愛、接納和尊重“泛化”到同伴群體中,并通過人際交往實踐活動促進自我合群心理的健康成長。
(三)民主式兒童訓練法
民主式兒童訓練法是Rudolf Driekurs于1950年提出的一種家庭教養策略,該策略強調民主的家庭文化氛圍,如成員間的相互尊重、集體協商決策、鼓勵和合理的限制。Dembo等〔11〕和 Krebs〔12〕的研究發現,民主訓練法對教養目標的實現更為有效。民主訓練法的假設前提是:①行為的產生并非偶然發生,必然有其原因;②對行為的解釋需要與行為情景聯系在一起;③行為產生的原因就在于行為動機或目標;④對兒童行為的理解應該傾聽兒童的解釋;⑤群體認同感、歸屬感是每個個體的基本需要〔13〕。這些假設構成了親子互動的理論基礎,使得父母發展與兒童的互愛互尊的有效關系獲得強有力的理論支持。秉持民主規則的家長很有可能在訓導兒童的過程中,首先考慮兒童不當行為的背景和邏輯,并認真耐心地傾聽兒童的訴說。如父母看到孩子和鄰居家孩子發生沖突,他可能先去制止沖突行為并安撫沖突雙方,然后引導兒童講述沖突的原因,而不是采取專斷的態度和行為進行訓誡批評。
民主式訓練法基于發展父母與兒童之間友愛關系為基礎,將兒童的不當行為的原因解釋為出于兒童自我表達的需要,力求通過兒童體驗自我行為的邏輯后果學習自律。民主訓練法反對使用獎勵和訓誡,反對父母的專制獨裁主義,認為通過兒童行為的邏輯后果來教育兒童,使兒童學會為自己行為負責。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倡采用自然后果法讓兒童體驗自己行為帶來的消極后果,進而調整先前不當行為方式。民主訓練法的支持者認為,危險的行為后果會威脅和傷害到兒童,如父母教導兒童若穿越馬路應當左右觀望確定安全方能過馬路,顯然自然后果有時會危及兒童生命安全。因此,父母需要用邏輯后果替代自然后果。邏輯后果的使用前提條件是家庭所有成員協商制訂契約(包括行為方式守則和違反規約的后果),進而使兒童學會思考、計劃、權衡和自主選擇行為,并承擔行為責任。例如,如果兒童發生攻擊他人的行為,晚上將不得觀看他喜歡的動畫片。如果嚴格執行攻擊性行為的邏輯后果,兒童最終為避免失去看動畫片的令其不愉快的結果而終止攻擊性行為。
民主式訓練法還強調內部激勵對于培養兒童期望行為的重要性,認為鼓勵是比獎懲更為有效的行為塑造手段〔14〕。民主訓練法認為,獎懲作為兒童外部激勵手段所起到的作用會使兒童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尋求成人的許可、支持,這將無益于兒童自尊水平的改善。因為當兒童行為表現得不到環境的回應反饋尤其是支持時,那些父母所期待的行為很容易發生“消退”或者“去條件化作用”。另外,過度頻繁地使用獎懲,無論獎勵和懲罰都將逐步失去意義。對此,Curry和Johnson做了形象有趣的比喻——“孩子需要的是導師,而不是拉拉隊隊長。”〔15〕比如兒童每做一件事情父母都說:“你真了不起!”這顯然成了一句空話。另外,過度嚴厲的懲罰只會更為嚴重地打擊兒童的自尊心。鼓勵而非表揚兒童,關注兒童合理的行為,注重對兒童行為的縱向、過程性評價,將兒童的行為與過去的行為表現進行對比,而不是與其他兒童進行強調橫向對比。如評價兒童:“你這次比上次做得更好”,而不是“你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孩子”。
通過家庭會議賦予兒童平等參與家庭決策的話語權,這將有助于解決家庭成員內部的分歧。當兒童感知到被關注、他的需要及時得到環境積極回應、擁有表達機會和權力時,他就更容易建立起健康的自我概念和自我價值感。專制型的家庭往往將兒童視為“幼稚無能的白板”或者說“自私而不明事理的受教育者”,這些家長在家庭決策或是家庭規約建制過程中完全忽略兒童的需求,甚至認為兒童的意見是無理取鬧和自私的。本質上,對兒童需求和話語權的忽略本身就是一種消極的虐待。如果兒童的表達或意見常常被家庭忽視,兒童從其他家庭成員那里獲得的信息是“我是不重要的,我是無能力的,親近的人是不可靠的和家庭是沒有安全感的”。兒童深感自我能力被削弱、被壓迫、被否定、被貶抑。習得性無助實驗告訴我們,當兒童屢屢遭遇挫敗和某種剝奪,在他的感知常常為阻礙他的事物所限制和控制,而喪失對實際情境理性思考。兒童從家庭中獲得的消極信念容易泛化到他生活、學習的各個場景,并逐步在錯誤的認知中建構起低自尊感和低效能信念。
綜上所述,基于家庭所有成員平等協商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家庭規則,有助于兒童自我界限感的形成,并使其學會調節和控制自身行為以避免侵犯他人的需求。父母考慮兒童需求,并給予兒童表達、理解、支持、關愛、尊重,有助于兒童自身發展他們健康的行為方式、思維習慣和良好的人格品質。健康的親子互動方式,同時也為兒童提供了健康的安全感、自我效能感、自尊感和責任感,在此基礎上兒童個人潛能得以積極迅速發展,并使得兒童成長為具有健康完滿人格品質的獨立個體。
很難找到一種普適所有家庭的訓導方案,“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時刻置于一定社會文化的培育熏染之中,是一定文化的模仿者與復制品,社會文化制約與決定著他們的心理活動與行為模式”〔16〕。因此,當某些規則、價值觀融入某個家庭系統,必然受到家長性格、價值觀、經濟狀況、教育背景、社會地位、職業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某種訓導策略是否有效,可能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檢驗和修正,而且有效的訓導應該是發展變化的,父母應該根據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做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