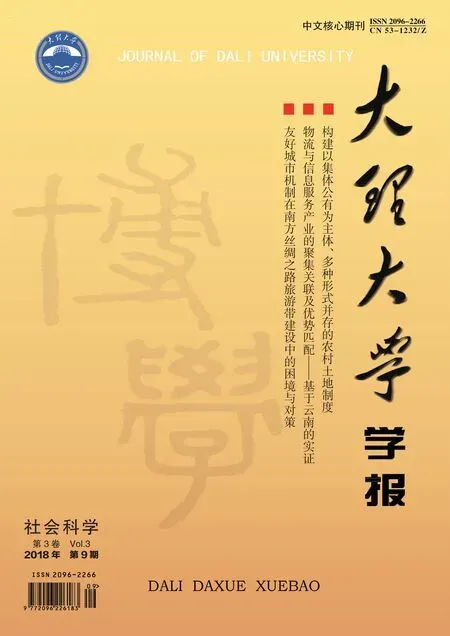友好城市機制在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中的困境與對策
趙建軍
(大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一、問題的提出
南方絲綢之路古稱“蜀身毒道”,又稱西南絲綢之路,起于四川成都,經云南進入緬甸,再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到達歐洲和非洲,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史記》《三國志》等歷史文獻和四川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等考古發現業已證明,南方絲綢之路始于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對外貿易線路,也是中國與西方交通史上最早的陸路交通①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記載:“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南方絲綢之路在國內形成了西南及南方地區的巨大交通網絡,在國外則與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中亞、西亞連接成一個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網絡。在漫漫歷史長河中,這條通道一直是中國連接南亞、東南亞的重要紐帶,促進了區域內國家間的經貿文化交流,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的貿易,最早讓西方了解了中國,也最早讓中國了解了西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相關國家積極響應。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中,旅游具有先聯先通的天然優勢。共建“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倡議,激發了國內外對絲綢之路旅游的廣泛關注,為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旅游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會上進一步指出:“應該發展絲綢之路特色旅游,讓旅游合作和互聯互通相互促進。”〔1〕2015年,國務院授權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提出了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國際精品旅游線路和旅游產品,提高沿線各國旅游便利化水平,推動旅游合作的發展思路和建設目標〔2〕。根據國家旅游局相關預測,“十三五”期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迎來1.5億人次中國游客,旅游消費超過2 000億美元;中國也將吸引8 500萬人次沿線國家游客來華,帶動旅游消費1 100億美元〔3〕,這將極大促進絲路沿線各國、各地區的旅游業發展。南方絲綢之路是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打造沿線旅游文化帶,形成資源互享、互利互惠的區域旅游文化共融發展格局,將積極推動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
旅游是旅游者經由旅游通道往返于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間的活動,根據現代交通的特點,直接表現為旅游者在城市之間的流動,受制于城市間往來的便利程度。在跨境旅游活動中,城市間的互動能力和合作水平是影響和制約旅游發展水平的關鍵。友好城市是指將地域上或政治上無關的城市和城鎮進行配對,以增進城市間社會交往與經濟往來,其目的是為了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并為兩國的經貿發展提供紐帶和平臺。目前,國際上已經有20 000多個城(鎮)結成友好城市關系。從我國城市對外合作與交流的實踐看,友好城市建設機制一直是地方政府開展城市外交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相關報告,截至2017年5月,我國各地(不包括港澳臺)共與海外國家城市締結友好城市關系計2 451對,其中,與“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中的53個國家締結友好城市關系707對,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文化交流與人民往來提供了重要基礎和保障〔4〕。但在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友好城市數量及城市間的互動能力和合作水平明顯滯后于其他地區,對沿線地區城市間經濟文化交流和旅游的促進作用體現得尚不夠充分。
二、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相關地區友城建設情況
傳統上,南方絲綢之路指起源于四川成都,經雅安、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楚雄、大理,或經四川樂山、宜賓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再經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后到達印度和中東的古道。“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南方絲綢之路泛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南段,涵蓋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不丹、阿富汗、馬爾代夫、尼泊爾、孟加拉等八國,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文萊等十國和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我國西南地區的省市和自治區。根據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的相關資料統計,截至2017年5月,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友好城市707對,其中,與南亞地區國家建立45對,與東南亞地區國家建立183對。南亞、東南亞地區除了不丹、阿富汗沒有與我國建立友好城市外,其余十六國共與我國建立友好城市228對,其中,與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區省份的城市結對49對,占南亞、東南亞地區與我國友好城市總數的21.5%。
在南亞、東南亞十六國與我國建立的友好城市中,東南亞十國與我國建立友好城市183對。其中,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等七國與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區南絲路沿線省份城市結對35對,占東南亞地區國家與我國友好城市總數的19.1%。除不丹和阿富汗外,南亞六國共與我國建立友好城市45對。其中,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等五國與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區省份城市結對14對,占南亞地區與我國友好城市總數的31.1%。根據上述相關資料,我國境內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等五個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省份共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建立友好城市49對,占我國與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南亞、東南亞國家友好城市總數的21.5%。與此同時,我國華南地區的廣東、廣西、福建和海南四省區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建立了91對友好城市,占我國與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南亞、東南亞國家友好城市總數的39.9%。其中,僅廣西一地就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建立友好城市53對,超過了西南五省市的總和。
可見,地緣上與南亞、東南亞相通相連的渝、川、黔、滇、藏等地,與同處于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南亞、東南亞國家建立的友好城市數量偏少,在我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建立的友好城市關系總量中占比偏低,與相關國家開展城市外交與旅游、經貿合作的互動能力不足,對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的支撐不夠,尚不能滿足面向西南地區對外開放高地和輻射南亞、東南亞中心建設的要求。
三、友城機制在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中的問題與困境
我國友好城市建設始于1973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發展。但囿于國情和國際政治環境,長期以來偏重于與歐美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締結友城關系,形成了“東多西少、重北輕南”的格局,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和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等相關建設中,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
一是地區分布失衡,對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欠發達地區的輻射帶動不足。從總體上看,我國與海外國家締結友好城市數量大,但東部地區城市對外結對多,西部地區城市對外結對少;與歐洲、北美和東亞地區國家間城市結對多,與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美等地區國家間城市結對少;與美澳日等傳統發達國家間城市結對多,與一帶一路地區國家間城市結對少。特別是西南五省市與同處于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南亞、東南亞國家城市間締結的友城數量少,在我國與南亞、東南亞地區國家間所締結的友好城市總量中占比低,與本地區擔綱的面向西南地區對外開放高地和輻射南亞、東南亞中心等發展定位不相稱,不能滿足對外城市外交與跨境交流合作的要求和需要。
二是層次多、結構關系復雜,“外交易行,商旅難為”。由于政治體制與國情差異,我國各地與海外國家締結的友好城市關系中,有我國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與外方的省、州、郡、縣、府、市間結對的友好關系,有我國的地級市(州)與外方的省、州、郡、府、市間結對的友好關系,也有我國的縣和縣級市與外方的郡、市間結對的友好關系。在這些友好城市關系中,由省級地方政府與外方省州級地方政府締結的友好關系對子占了我國對外友好城市關系總數的25.4%,而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西南五省市中,由省級地方政府對外締結的友好城市關系更是高達35.6%。這種層次交叉的友好城市關系,對開展政府間官員互訪等城市外交活動相對來說尚較為便利,但對帶動和促進民間商旅往來的作用不明顯。
三是友城機制“官”重民輕,文重商輕,對旅游等產業促進作用發揮不充分。盡管通過建立和發展國際友好城市關系,為當地的企業尋求投資的機會和發展市場,以推動經濟貿易合作、取得經濟和商業利益是多數城市締結友好城市最主要的動因,但在具體實踐中,雙方的往來互動更多地集中在官員互訪等行政交流和教師交流、學生互換、青年互訪等相對簡便易行的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方面。根據相關學者研究,即使是日本的東京都這樣經濟發達、現代化水平非常高的國際大都市,在其與各國友好城市的交流中,行政交流活動占52.3%,經濟(工業、商業、農業)等交流活動僅占6.3%〔5〕,體現出官員互訪和文化教育交流比重大,民間交流和商旅往來分量輕的特點。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總體尚較低的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友好城市間經濟交流薄弱的困境更突出,友城機制對旅游交流合作等產業促進作用發揮不夠,支持力不足的問題更明顯。
四是“偏心病”嚴重,區域輻射作用不強。西南五省市對外締結的友城對子不僅數量少,而且過度集中在省會城市。結對友好城市覆蓋面不夠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區域外交帶動作用的發揮。相關數據顯示,在我國華南地區的福建、廣東、海南、廣西等四個省份,不包括省級地方政府對外締結的友好關系對子,由省會城市對外締結的友城對子在該省城市締結友城對子總數中的比例為:福建18.6%,廣東24.8%,海南33.3%,廣西17.5%。同一數據,南絲路地區西南五省市的比例為:四川48.3%,重慶64.3%,西藏62.5%,貴州62.5%,云南39.6%①根據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相關統計數據整理。。可見,與東部地區相比,南絲路地區不僅對外締結的友好城市對子總體數量少,而且友城對子過度集中在省會城市,大多數地州及縣市一級城市還缺乏友好城市這一對外交流合作渠道和平臺,友好城市覆蓋不夠廣,輻射作用不夠強,通過相關機制帶動民間外交與經貿合作、促進商旅往來的作用體現得不充分。
五是缺乏規劃,盲目結對,可持續性不強。在西南五省對外締結的友好城市關系中,有相當一部分友城對子是由于地方政府領導之間的一次偶然會面,或是某個熟人的介紹,或是城市政府領導人的個人偏好等“偶然”因素牽線搭橋,促成的友好合作關系,一旦這種“偶然”因素不再存在,特別是當友城政府高層人員更替時,友好城市關系的維持和發展就會缺乏動力。這些由“偶然”因素牽線,盲目結成的友好城市對子,往往缺乏系統規劃,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聯系不緊密,針對性差,互補性不強,相互間缺乏經濟合作交流與商旅互動往來的基礎和條件,難以開展務實合作交流,象征性大,“保鮮期”短,友城關系容易因人事變動而受影響,甚至名存實亡成為“僵尸”對子②2015年,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清理注銷40對友城關系。,可持續發展難度大,對旅游等民間往來互動的促進作用極為有限。
六是弱弱攜手,經貿商旅互動量能不足。南絲路地區城市總體上規模小、欠發達,盡管各方在締結友好城市關系時,都有通過友城關系促進經濟合作與商旅往來的強烈愿望,但友城間商旅往來互動交流量能不足,對商旅、人員往來的促進作用較為有限。根據國家旅游局發布的相關數據,2015年,我國接待亞洲各國游客總數為1 622.03萬人次,其中,來華游客人數超過4萬人次的日本、韓國、朝鮮、蒙古、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十五國來華游客數達1355.22萬人次。在十五個亞洲主要客源國中,有九個為南亞、東南亞國家,占60.0%。但南亞、東南亞九個國家的來華游客數為512.28萬人次,僅占亞洲十五個主要客源國家來華游客總數的37.8%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游客總數的17.0%③根據國家旅游局相關統計數據整理。。這一數據表明,我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旅游合作水平還較低。作為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前沿和輻射中心,南絲路五省市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總體上城鎮人口數量少、城市化水平低,經濟發展水平低、產業體系單薄,城市綜合設施配套體系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城市尚無機場口岸等外聯通道,對外開放程度低。除極少數區域中心城市締結的友好城市間開通了直航和少量邊境城市間締結的友好城市間有地面水陸交通相連外,絕大多數友好城市間貿易往來和人員交流均需通過第三方轉運,綜合成本高,便利性差,開展對外合作的能力有限。境外關聯地區基本情況也大體相似,一些指標甚至遠遠弱于國內。因友城機制中外交對等原則等因素制約,結對的友好城市往往是各自國內級別相當的城市,這就使南絲路地區相當一部分締結了友好關系的城市對子呈現出經濟上弱弱攜手,規模上小門小戶,交通上無門無路(沒有機場、航線等直聯通道)的特點,總體上往來便利性差、成本高,交流互動量能不足,長期維持“一對一”高密度互動交流的難度大,客觀上制約了友城間經濟貿易和商旅往來等多層次合作交流活動的開展。
四、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中的友城機制創新策略
旅游是推進民間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通過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和城市間的旅游合作,形成旅游文化特色經濟帶,不僅可以極大地提升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經濟水平,更能促進國際、國內的民間交流與民心相通,服務“一帶一路”國家倡議的實施。旅游帶的形成需要以區域共同市場和地區國家和城市間持續、穩定的旅游流為基礎,南方絲綢之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部分,利用和發揮好友好城市這一國際城市之間的合作機制和人員交往平臺的作用,在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通過旅游經濟文化帶建設,形成資源互享、互利互惠的區域旅游文化共融發展格局,將有力推動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一帶一路”建設。
第一,盤活存量,加強溝通,促進流通。友好城市既是重要的民間外交成果,也是地方政府寶貴的外交資源。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西南五省市,友好城市建設相對滯后,友城對子數量少,又處于我國面向西南地區開放的前沿,承擔著面向西南地區開放輻射中心建設的任務,顯得彌足珍貴,這就要求我們要盤活地區內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城市間友好城市關系的存量,充分發揮好現有友好城市的紐帶作用和友城對子的平臺作用,來促進與南絲路沿線國家和城市的交流與合作。從實踐層面看,這些結對城市或處于區域中心,或位處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或坐擁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旅游吸引力強,旅游合作空間大。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必須激起和發揮好這些城市間的外交活力,密切聯系,加強互動,以交促流,通過加強人員往來,密切行政溝通,促進商旅流通。只有讓友好城市“動”起來,友城關系才能“活”起來,城市資源才能“流”起來,游客往來才能多起來。
第二,整體規劃,合理布局,加強友城建設針對性和系統性。建設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必須深化與南絲路地區國家、城市間的旅游合作,綜合衡量城市間的資源互補性、交通條件和區域輻射帶動力等因素,在國家和省域兩個層面對與絲綢之路沿線南亞、東南亞國家城市間締結友好城市工作進行系統規劃和整體布局。以突破一個點,打通一條線,輻射一個面,連成一張網為目標,增強友城建設的目的性和實效性,加大友城建設力度,優化友城網絡空間布局。通過頂層設計,從根本上解決西南五省市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友城對子數量少、“偏心”分布等問題,在加強省會城市與外國首府城市等區域中心城市間聯系的同時,密切絲路沿線廣大地區節點城市間的旅游聯系,以旅游資源聚集人氣,以旅游線路產品匯聚客流。
第三,建立省域友城協調機制,統籌各級友城建設。成立省級友城建設指導機構,建立協調機制,統籌省域友城建設。改革優化現行“下級報備,上級審批”的管理后置友城締結工作模式,強化對友城結對的前置指導和管理,改變省、州、市(縣)友城建設各行其是,盲目結對,省級友城對子與州市級、縣市級友城對子間互不統屬、關系混亂,聯動性不強等狀況。統籌協調,上下聯動,建立以省統州(市),以州(市)帶縣(市),省級對子之下有行政隸屬關系的州市級對子,州市級對子之下有隸屬關系的縣市級對子的多層次友城合作體系,加強不同層次對子間的互動聯系,發揮友好省、友好府等上層友城關系對友好市、友好縣等下層友城關系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在省域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城市間,構建起層次分明,統屬脈絡清晰的友城體系,引導航線建設、口岸建設等跨境合作基礎資源和保障條件的配置,促進南絲路區域旅游合作體系建設。
第四,建立友城旅游聯盟,構建多邊合作機制,打造南絲路旅游共同市場。南絲路地區城市規模小,發展水平低,友城間“一對一”開展旅游等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互動量能不足,即使是在昆明、仰光、加爾各答、曼德勒這樣的省會城市或首府城市間,也必須通過與北京、上海等城市聯程聯運,才能維持相互間的航班運營。南方絲綢之路旅游帶建設需要以沿線城市間友城關系為紐帶,設立城市之間旅游合作的共享機制和協調服務機構,通過友城聯盟建設,建立區域城市間多邊旅游合作平臺,變“一對一合作,點對點互動”為“一對多合作,多點互動”,整合多邊資源,強化南方絲綢之路文化主題,彰顯“南絲路旅游”品牌特色,共建、共享南絲路旅游共同市場。擴大友城合作的空間和深廣度,從整體上塑造“一帶一路”城市旅游的品牌形象,促進旅游產業全域輻射帶動能力,通過優勢互補、渠道共用、資訊共享,實現一方結好,多方受益,彌補雙城雙邊合作量能不足的局限,增強友城機制的合作效能。根據城市在區域中的地位、作用,確立友好城市旅游聯盟中的節點城市,通過加強會員城市間的交流,以節點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發展旅游業,開展跨區域旅游服務活動,以區域內旅游合作推動跨區域旅游合作,形成人氣旺盛的旅游文化經濟帶,帶動南絲路沿線國家、城市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