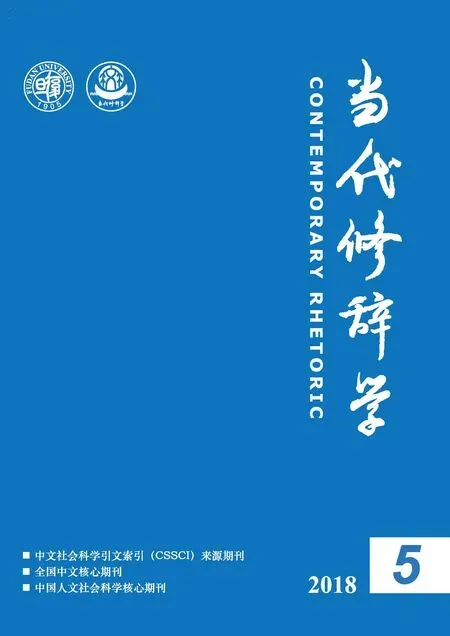發展陰陽修辭:從和諧互惠到異中互存
毛履鳴
(猶他大學修辭寫作系,美國猶他州)
趙燁冰 譯
(美國邁阿密大學英語系,俄亥俄州)
提 要 通過對陰陽修辭的論述并借鑒中國修辭實踐的實例,本文重新界定了對立術語 (terms of opposites),并對其蘊含的分層極性(hierarchical polarity)和價值判斷提出了挑戰。本文認為,對立術語應被用來傳達和促進相互依賴和相互關聯的關系,且異中互存關系(independence-in-difference)應該成為研究中國和歐美修辭實踐以及運用它們于寫作與修辭課堂中的普遍做法。
近些年, 在北美、中國講授中國和歐美修辭傳統的過程中,我遇到過很多使用對立術語來描述這兩種傳統并將它們置于對比或對立的關系中的例子。這些術語包括但不限于:直接與間接、演繹與歸納、邏輯與類比、存在 (being) 與成為 (becoming)、自言與借言。這樣的對立描述本身并非一定有缺陷或存在問題。畢竟,正如比較古典哲學與科學的歷史學家勞埃德(G.E.R.Lloyd)所言: “不管這些術語是否被分為‘正面’和‘負面’兩極,對立描述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定義基準(framework of reference),使各種復雜現象有了被描述或分類的可能性。”(1966:80)又或者,如寫作學學者彼得·埃爾伯(Peter Elbow)長期主張的,矛盾對立可以作為富有成效的而不是阻礙性的啟發式方法,如果培育得當,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建立一個更廣泛的定義參照體系,將舊參照系中的兩個被認為是矛盾的元素都包括進去”(1986:243)。這兩位學者顯然認可了對立描述的有用之處。然而,當寫作與修辭的教師在使用這些對立術語時,若沒有事先全面了解它們的實際含義以及它們實際認可的內容,問題就會出現。例如,成見與二元對立將加劇,而以此為代價的是修辭與文化現象本身的偶然性和復雜性被忽視。同樣存在問題的是這些對立術語被隨意地用來解釋所謂的中國和歐美修辭手法之間的差異。因為這些術語本身需要解釋,所以簡單地援引它們除了將這種功利性的解釋轉變為一個循環論證的過程,并不會對不同的修辭實踐提供任何有力的新見解。
如果沒有批判性地對待這些對立術語,不良后果將產生。比如說,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對立術語來描繪或解釋中國和歐美修辭之間的差異,其分層極性(hierarchical polarity)將凸顯。我所謂的分層極性即每對對立描述中的第一方比第二方或“次要(lesser)”方享有更多價值或特權,且兩者的關系總是建立在以一方為主導的普遍理解模式中。當中國的修辭實踐或其他修辭實踐在缺乏情境化分析(contextualized analysis)的條件下被描述為表達或偏好“次要”的溝通模式——間接的、歸納的、類比的或通過別人的聲音說話的——物化(reification)①或抽象化(abstraction)必然會發生。不論是物化還是抽象化,最終都將導致簡化、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和/或異域化(exoticism)。因此,中國修辭很容易成為或被視為歐美修辭的對立面。與此同時,物化也創造出了自己的文化與話語現實,從而進一步影響和決定人們隨后與中國和歐美修辭實踐的交會,導致更多的刻板印象、更多的虛假陳述或扭曲描述,以及更多的異域化,后果是物質性和象征性兼有(exoticisms with material and symbolic consequences)。
鑒于這些使用對立術語而產生的真實和潛在的問題,我建議重新思考和校準對立術語,以超越此前對其二元化和層級性的理解。為此,我轉向中國陰陽修辭。 我想借鑒它的動態性來發展對這些對立術語的新理解,并啟發在寫作和修辭課堂上教授中國和歐美修辭的方法。
陰陽修辭:顯著的異中互存
廣義而言,修辭指的是不同的文化利用各自的語言和其他象征手段進行意義創造活動的方式。作為人類,我們使用修辭來勸說、諫言,樹立關系和建立秩序,并促使旁人采取行動。修辭所采取的形式也是歷史性暫時的和不斷翻新的。那么什么是陰陽修辭呢?寫作與修辭學的教師該如何利用它來總體地啟迪極性的概念并具體地解讀那些特定的對立術語?
陰陽一直被視為中國科學和哲學史上的兩大宇宙學概念。公元前四世紀前,陰陽最初指的是山丘或河岸的背光和向陽兩側(Needham1956:227-273)。在公元前三世紀及公元前一世紀之間,陰陽開始有了更廣泛的含義,代表“空間或時間進程中任何配置的配對和互補分工”,并作為中心范式用來討論“主動和被動,生長和衰減,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相互作用”(Lloyd & Sivin 2002:197)。
根據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說法,陰陽表達了這樣一種中心思想:“一對對立而互補的存在,向內觀察,其現象可逐一被分析,而從外部查看,對兩者現象的整體統一認識將形成。”(1987:63)從這個角度看,陰陽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滲透的。這種關系也具有創造力,因為它總是在自己的時空環境中發展和變化。因此,某種情境下的陰可在另一場合中成為陽,沒有任何一方是可以獨立存在的。作為中國相關性宇宙論(correlative cosmology)的一部分,陰陽及其不計其數的表征形成了中國古代各種原始科學的概念構架,包括天文學、醫學、音樂、占卜、煉金術和風水學(Raphals 1998:139)。更重要的是,在被稱為戰國的一段關鍵時期(公元前479年—公元前221年),即當中國陷入社會劇變,不同封建勢力之間暴力合并,各種學說激烈爭奪霸權地位之時,陰陽開始被用來解釋并隨后用來塑造社會和文化現實。這種動蕩不定的環境為陰陽成為一種特色修辭提供了肥沃土壤——這種修辭在宇宙統一的力量之上展現出和諧與互惠,并使當時的統治者找到了他們所期望的用來證明其權威性和合法性的道德和政治依據。它塑造了一種流行新話語,并創造出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其中,個人、國家和宇宙由統治者用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調解和統一。這是一個以相互依存、和諧和完整性為標志的秩序。
與此同時,古希臘的有關對立的思想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且常被用來與中國古代的陰陽思想進行比較。例如,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考證,畢達哥拉斯對立表(Pythagorean Table of Opposites)即“sustoichia”中有十對相反的術語,每對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了關聯式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例如,在有限(limit)方面,有奇數、一、右、男性、靜止、筆直、光明、好、正方形。 而在無限 (unlimited) 方面,有偶數、多、左、女性、移動、彎曲、黑暗、壞、長方形。勞埃德(Lloyd)認為亞里士多德應該是借鑒了“sustoichia”的基本思想。 他寫道:“如此,(亞里士多德)將右邊與男性、正面、上面、熱相聯系,而相反的,左邊與女性、反面、下面、冷相關聯,這樣的思想在他的宇宙論中于各種情境下作了解釋,還被用于他的胚胎學和物理學中。”(1996:114--115)
然而,對立論在古希臘從來無關道德或政治問題,也從沒傳達過互惠或和諧的觀念。勞埃德(Lloyd)還指出,盡管希臘許多的對立術語對造就了希臘的某些最深層的本體論假設和價值觀,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互惠和相互依賴的”(1996:121)。因此,“成為(becoming)依賴于存在(being),而不是相反。表象(appearance)取決于現實(reality),但反之不亦然”(1996:121)。同樣,與陰陽修辭在戰國時期的使用和發展情況不同,這些關系從來沒有被提升為代表或促進政治、道德觀念,并為城邦提供一種可使用的連貫性和系統化的概念。古希臘整體的對抗和敵對的環境,以及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他們自己的競爭對手和同僚之間的競爭關系使得任何單一的一致統一的對立理論都不可能出現,更不用說一種統一的修辭有可能借力于政治權威或使某種議定的政治制度合法化。
此外,陰陽在根本上扎根于具體的經驗,它們指的是特定現象的各個方面,而不是“部分成分,組成力量,或純粹的抽象”(Sivin 1987: 63)。陰陽及其衍生的陰陽修辭有一個特點值得強調,即一旦它們被從特定的使用場合中抽象出來,或者一旦它們成為抽象的對立符號,陰陽很容易轉變成為兩個對立成分之間層級性的甚至不可逆轉的關系。例如,當女為陰男為陽被特定的實踐社群中抽離出來,他們無非會成為本質化或令人難解的特性。如此,會助長類似于 “男主外,女主內” 的分工理念,獨尊男性,并強化男性凌駕于女性之上的支配權。與此同時,若被放在具體的背景下或在相互依存和互惠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女為陰男為陽可被視為兩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方面或階段的體現。或者引用宋代(962—1279)著名的哲學家和新儒學思想家朱熹的話:“陰陽合一,氣亦然。陽退,陰生其中; 而非陽退,陰分離之而生……。”(Yin and yang are one and the same qi [energy]. The retreat of yang is the birth of yin; it is not that once yang has retreated, a yin separate from it is born…)(Sivin1992:64)②
還有一點,當陰陽在其具體處境沒有被充分調查的情況下被概括為兩極分化的成分或力量,價值判斷通常隨之而來,進一步加劇它們之間的極性。也就是說,陰以及與之相關的往往被刻板地刻畫為邪惡的,或者較弱的。而陽及其相關的則通常被認為是更好的、積極的。這些帶有價值判斷的關聯反過來又加強和促進了現有的權力失衡的社會結構。然而,這樣的聯想在中國古代公元前三世紀是找不到的。根據尼達姆(Needham)的說法,它們在中國陰陽理論中其實并不存在(1956:277)。
實際上,如果要充分運用陰陽修辭,那么寫作與修辭教師就必須考慮或重視空間和時間上任何過程的潛在和活躍階段,以及它們的連續變化性或相關性。理解這兩個階段是如何運作的,對有效地實踐陰陽修辭至關重要。例如,太陽的常規和可預測的每日周期可以用光線在中午達到峰值的階段和在午夜達到峰值的黑暗階段來描述。這樣做可以讓我們看到光與黑暗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不是本質化的極性。同樣的道理,在修辭的語境中,直接(direct)若從直接—間接(direct-indirect) 的話語關系(discursive relationship)的角度來看待,可代表這個話語關系中積極的階段;而若間接從直接—間接的話語關系來看待,也可以被視為推動變化的積極階段。換句話說,直接其實是直接—成為—間接(direct-becoming-indirect),而間接則為間接—成為—直接,以此類推。從這個角度看,對立術語不再指向毫無關聯的兩個相互對立的元素,而是作為其自身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整體的、不斷發展的和相互依賴的話語秩序的一部分。
雖然我想強調陰陽修辭相互作用的核心動力,但并不是在暗指陰陽之間的區分可以或應該馬上被消除,或者說,陰陽可以或應該馬上被結合起來達到一個穩定無縫的融合。相互依賴并不意味著任何一對對立物之間的差異或分裂的結束,認識和接受差異或分裂也一定不會阻礙相互依存或相互關聯的關系。總而言之,構成陰陽修辭的基礎應該是對立統一 (interdependence-in-difference) 的關系,即差異中仍保持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是必須強調的。
發展對立統一關系需要不斷培養和探索陰陽或對立術語的平衡點或制衡點。也就是說,寫作修辭學的老師必須學會辨別和培育這樣一些空間使得兩個對立物“時刻為積極的陽(active yang)和感應的陰(responsive yin)之間產生新關系做準備”(Sivin 1987: 69)。開放這些空間使它們能夠進一步發揮支撐陰陽修辭的生成性(generative)和變革性(transformative)特征。例如,人們在大自然中經常有這樣的一種體驗,即感受到時間周期中的兩個分點處的瞬間平衡,白天和黑夜無處不在且它們之間的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中。在修辭實踐領域,人們也可以在諸如“用一個類比來說明”或“允許我用歸納推理來說明陰和陽”這樣的元話語(metadiscursive phrases)中找到平衡點。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開辟了一個空間,其中,邏輯和類比、演繹和歸納都處于瞬間平衡狀態,隨后它們之間將啟動一組新的關系。值得認真關注的正是這些元話語時刻(metadiscursive moments),也正是因為它們,我們才有了有效參與和體現對立統一的意義創造機會。
重新定義對立術語: 把陰陽修辭運用起來
北美的一些當代修辭學家和信息交流學者最近已將陰陽作為一種修辭形式進行研究。然而,這些研究似乎通常只將陰陽修辭與道德經中的“道”聯系在一起。《道德經》這一哲學著作通常被認為是傳說中的老子(The Old Master)所寫,但它其實最有可能是很多人跨越一段時期共同編纂而成,并最終于公元前4世紀早期或中期(Ames& Hall 2003:2, 7)完成。例如,最近的一項研究將陰陽稱為無法描述的道,將它們形容為代表宇宙的節奏和設計(Combs 2003: 25--26)。另一項研究將陰陽視為《道德經》中最重要的符號,因為這兩個互補的元素反映了道的許多不同方面(Kowal 1995:367)。還有一項研究,為了從修辭的角度研究《道德經》,通過悖論(paradoxes)來關注陰陽的動力轉換,這些悖論通常包含諸如光明與黑暗、光滑與粗糙、高與低,以及說話與沉默之間的對立或對比(Xiao 2002:141--143)。
這些研究可能有其自身的價值,但它們大部分都集中在或只關系到《道德經》。同時,超越《道德經》領域的陰陽的修辭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正如我前面說過的,陰陽修辭在公元前三世紀被發展用來幫助國家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我在此也想探討陰陽修辭如何有效地被引用來啟發我們在寫作和修辭課堂中教授中國和歐美修辭手法的異同。特別是,陰陽修辭如何帶領我們超越以往對立術語所蘊含和推廣的層級分化和極化趨向。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傾向必須加以控制。那就是,發展和運用陰陽修辭的目的決不能被看作是試圖使陰陽合理化,或者說是用邏輯和因果論證來驗證對立統一關系。本研究也不應該被視為將陰陽浪漫化,好似陰陽修辭現已成為解決我們所有挑戰的終極要義。更直接地說,任何這樣的一種誤讀都將導致我們把陰陽構建在一個錯誤的情境中。相反,本研究想要實現的是將陰陽與它們相應的社會和政治環境聯合起來,從而帶出陰陽內在的人性化的因而也是修辭化的維度,使我們能夠在特定的情境中去體驗陰陽并與之互動,這其中最突出的情境就是我們的寫作和修辭課堂。
那么,在寫作和修辭課堂上將陰陽修辭付諸實踐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這意味著寫作與修辭教師通過相互依存和互聯互通的關系將對立術語概念化,包括直接和間接、演繹和歸納、邏輯和類比、自言和借言。在這種關系中,一個術語必然依賴于另一個術語,但仍與其他術語保持不同,并且任何一對對立術語中兩方的價值都是由它們所連接的交際語境構成的。因此,如果寫作與修辭教師選擇將某些中國或任何其他修辭傳統形容為以間接性或類比思維作特征,他們現在可以提醒學生這種刻畫實際上是依賴于直接性和邏輯思維,或以其作為參照點,若沒了這些參照點,這些特征將失去其意義或相關性。與此相關的,在寫作與修辭課堂中實踐陰陽修辭也意味著教會學生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個交際語境中被認為是間接或類比思維的實例可能在另一個交際語境中會被當成是直接或邏輯思維的例子,反之亦然。對任何對立術語的理解都必須被定位于特定的背景和特定的使用場合中,而對對立術語的討論實則基于對話語定位的背景和功能的考察。
教師可以借助于中國古典修辭實例進行說明。漢代(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匯編的《戰國策》從早期的資料(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21年)中收集近五百件歷史軼事,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說客為了說服統治者采取某些行動所使用的各種勸說技巧。其中一個說服技巧是“雙重說服”(doubled persuasion)(Crump 1996: 42)或“矛盾兩端論證”(dilemmatic argument)(Lloyd 1996: 76)。其中一種形式是,說服者在建議某種行動方案時,分別從它的積極和消極兩方入手,并展示沒有采取積極提議的后果(Lloyd 1996:76)。這樣的技巧在西方修辭學家看來可能太不直接或者說服力太弱,無法與競爭對手有力爭論。但是,如果將這樣的交流形式置于整個陰陽修辭語境中,它可能相較于其他的“較不”直接、“較小” 說服力的交流形式而言已經算是相當直接且有說服力的了。
在《戰國策》中,教師還會看到許多類比論證,這種論證方法可以用來闡明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關系。當使用這些類比例子時,教師可以首先幫助學生在論證中找出不同類型的類比物。這些類比物可以是歷史先例、實際或報道的事件集合,也可以是民間故事或寓言,有沒有明確的結論都沒關系。其次,他們可以專注于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類比是如何起到修辭功能的。請看下面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
“我聽說北方諸侯都害怕昭奚恤,”楚宣王問群臣,“果真是這樣嗎?”
除江乙之外,群臣無人回答。他說:“老虎尋找各種野獸吞食它們。抓到了一只狐貍,狐貍對老虎說:‘您不敢吃我,上天派我來做群獸的領袖,您現在如果吃了我,就違背了上天的命令。您如果不信我的話,我在你前面走,您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群獸見了我,有哪一個敢不逃跑的?’老虎信以為真,就和狐貍同行,群獸見了它們,都紛紛逃奔。老虎沒意識到群獸是害怕自己才逃奔的,卻以為它們是害怕狐貍。”
“現在陛下的國土方圓五千里,大軍百萬,卻由昭奚恤獨攬大權。所以,北方諸侯害怕昭奚恤,其實是害怕陛下的軍隊,這就象群獸害怕老虎一樣啊。” (Zhanguoce1996:226--227)
在這個例子中,以老虎和狐貍的民間故事作為類比,這位說客通過重新解釋誰是恐懼的真正對象來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
學生可能會認為這種情況缺乏(使用)邏輯。這種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會嚴重妨礙他們理解歐美修辭傳統上被描述為二元對立術語中的第二個或“較弱”方為特征的修辭傳統。其實,只要學生學會超越因果關系視角并關注相似點或差異點之間的相互連系,就能發現這些類比論證實際上是有邏輯的。畢竟,直接性和間接性、邏輯和類比,或任何其他的對立術語,都是流動連續體(shifting continuum)上的話語特征。它們的修辭地位——無論是活躍的還是潛在的——取決于它們如何在每個交際情境中與其他參與特征聚合在一起,以及它們如何相對于自己時代的價值精神(ethos)被整體地感知和實踐(Mao 2002:114-116)。因此,類比論證所運用的邏輯不一定要采取因果形式。相反,它可以通過共鳴、失調和其他有賴于情境的話語特征集合體(discursive alliances)的形式來實現。
這種定位給教師和學生帶來了兩個積極成果。一方面,他們不再需要迷信于直接與間接、邏輯與類比,或任何其他二元對立概念之間的分層級性。通過陰陽修辭的視角,二元對立概念現在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變動話語連續體上的話語特征,而構成它們修辭價值的不再是對立而是相互依存,不再是分裂而是共振與失調(resonance and dissonance),不再是等級而是流動性話語特征集合體(shifting alliances)。
另一方面,教師和學生從現在開始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和文化價值是如何維持和延續二元論的,并公開和批判性地質疑這些價值觀。他們還能認識到,直接性或邏輯思維不過是流動性話語特征集合所組成的連續體上的一種應時功能(emergent feature),又或許只是秩序和變革動態周期中(dynamic cycle of order and transformation)的兩個階段之一。當教師和學生在寫作和修辭課堂中使用陰陽修辭時,他們也可以學習制定策略和其他啟發式方法(heuristics)來識別或表達周圍的情境,并理解這些對立術語的價值既不固定也不可預測, 它們其實是連續體上流動變化的話語特征集合的產物。因此,什么是直接的或間接的,什么是邏輯的或類比的,都不應該是抽象的價值判斷,而是通過它們相應的交際環境來判斷其意義和修辭功效。
其次,如上所述,陰陽既不代表任何兩種特質或屬性是對立和抽象的,也不表示這些特質或屬性是固定的或難解的。由于陰陽深深植根于特定的使用場合,它們永遠不可能彼此分離,也不能與其相應的交際環境分離。因此,如果教師和學生要使用演繹—歸納的極性特征來描繪中國和歐美的修辭實踐,那么這種刻畫必須基于他們所處的每個具體的話語事件環境。他們還必須明白,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都可以很好地與中國或歐美修辭的任何一方聯系起來,盡管可能有一方在某種特定的交際時刻會比另一方更占優勢或更具顯性存在(importantly present)。
他們可以再次援引中國古典實例。《韓非子》中有一篇關于韓非闡述說服困難的著名篇章。韓非是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法家代表人之一,他一般采用演繹推理,從概述(聲明斷言)開始,然后再提供原因和論據。在討論說服術的成功關鍵點時,韓非先是做了一個總的闡述“說客須了解說服對象的想法,并且能夠投其所好”(1964:72),然后他繼續他的推論,并用他自己的事實論據來支撐他的言論。然而,在提供自身論據的過程中,韓非多次插入了歸納推理,因為這些事例中的某些部分引申出了新的觀點或聲明。因此,韓非不但通過演繹推理,還通過歸納推理來發展他的論述并對勸說的運作模式提供了一個復雜的分析。套用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對哲學和修辭之間的二元關系的描述,這兩種推理方式都不可能“獲得完整和持久的優勢,因為在任何一方表達勝利的時刻,它都在朝向另一方的方向轉化著”(1989:501)。
證明 用反證法證明。假設這3個三角形有兩個為窮的,第3個為半窮或窮的,在這里設第3個三角形為半窮的(當第3個三角形為窮三角形時證明類似且更加簡單)。設f=[v,v1,v2]是半窮面,v1是窮點,v2是富點,v3是 5+-點, f=[v,v5,v6]和f=[v,v7,v8]是窮面。由G的極小性,G-{v,v1,v2,v3,v4,v5,v6,v7,v8}有一個(3,0,0)-染色,將這個染色染回到G,從而推出矛盾。
同樣地,中國修辭實踐常被描述為具有通過別人的聲音說話并犧牲原創性和權威性的特點。然而,正如陰陽相互依存且兩極之間的交替由社會和文化條件決定的原理一樣,借言和自言從來不可能被完全分隔開,其中任何一方也永不可能完全退居后臺。例如,在傳統儒家思想強調儀式、和諧或集體主義的大背景下,我們還是能聽到宋代新儒學強烈而生動的中國式個人主義或中國式個性的表達。朱熹的“為自己學習”是表達“儒家個人主義,即肯定自我或個人作為更大的社會整體、生物連續體和道德/精神共同體的動態中心的重要性”的眾多例子中的一個(de Barry 1977:332)。
他們還可以舉一個更近的例子來說明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民族主義修辭的興起。文化民族主義修辭旨在恢復本土知識并重建代表著中國話語想象的儒家思想體系,它一方面有效地代替了近來破滅的意識形態(bankrupt ideologies),另一方面取代了各式各樣的東方主義。這種新修辭通過本土知識的發聲和重新構建的儒家思想確立了其權威性和原創性。與此同時,通過反對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和其他馬克思主義教條,力求擺脫對政治和其他激進意識形態的文化承諾和復興,它大聲而清晰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并且明確地傳達了自己的獨特性。也就是說,它的目的是要合法化和推進新的思維方式和存在,并構成一個獨特的中國話語,既適應又促進一個崛起和繁榮的新中國。總而言之,文化民族主義修辭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了兩種聲音:自己的和他人的。
第三,與陰陽一樣,直接與間接、演繹與歸納、邏輯與類比以及自言與借言這些對立術語也能夠創造出它們自己的平衡時刻,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為一系列新的關系和理解做出貢獻。因此,當寫作與修辭教師使用這些對立術語來討論中國和歐美修辭時,他們必須幫助學生尋求和培養這些平衡時刻,通過否決它們之間不可逆轉的對立差異并承認它們的共創能動性(co-constitutive agency)。 他們必須幫助學生學會辨別那些話語間隙(discursive interstices)或中間時刻 (moments of in-betweenness),以便他們能夠真正運用對立統一關系來加深對中國和歐美修辭實踐的理解。
例如,他們可以探尋中國的類比思維是如何嵌入或先行于邏輯思維,或者研究歐美自言行為與那些通過借言行為或套用儀式話語的修辭實踐有何共通之處。同樣,他們還應該進一步探索這些相互依賴的時刻如何變得可能且可取,以及它們如何發揮反作用力來挑戰現有的社會和文化范式或期望,并促進或鼓勵新的存在、思考和言語方式。例如,在《論語》中,孔子毫不掩飾地告訴他的學生,他想成為儒學傳統的傳承者而不是創新者(1979:57)。這種愿望無疑揭示了他對過去的或失去后才被珍惜的傳統的深切敬畏和禮儀化關懷。同時,教師和學生不應錯過任何機會去探索孔子的這種愿望是如何讓他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與傳統進行交流,豐富傳統,并發展和推進他與傳統以及他與門徒之間的新關系。換言之,孔子成功地通過過去的聲音(可解讀為他者的聲音)發表了自己的獨特聲音。
雖然這些平衡時刻總是不斷變化著,但陰陽修辭的確給寫作與修辭教師帶來了絕佳的機會。它讓教師們現在能夠運用這些對立術語來教導中國和歐美的修辭實踐,并把它們置于對立統一而不是等級和對立的范式中。此外,陰陽修辭能夠促使他們實踐和推動一種不同的話語秩序,這種新話語秩序既“承認歡迎修辭風格和說服話語的多樣性”,又“能夠在修辭思維的實踐和表述中同時遵從全球普遍價值觀和具體文化價值觀”(Lu 1998:308--309)。
結論:推進自我反思
本文提出的這三點教學思考都還很簡短有限。然而,它們確實代表了我對發展陰陽修辭并以此來參與和干預用來描述和解釋中國及歐美修辭實踐的對立術語所付諸的努力。更確切地說,我轉向中國陰陽思想的動力來源于我希望這些術語能夠在其自身的語境中,用自己本土的術語來被介紹和評估。我想將陰陽修辭和直接與間接、演繹與歸納、邏輯與類比、自言與借言等對立術語聯系起來,并試圖用陰陽和它們所傳達的思想內涵來重新構建這些術語,以便寫作與修辭教師能夠幫助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和歐美修辭傳統,并且讓他們能夠開始養成一個不以層級性和極性為標志的,卻重視共鳴和相互依賴關系的話語習慣。如此,我希望能對有關比較修辭以及中國和歐美修辭實踐的討論做出些許貢獻。這些努力還將幫助形成“共同的紐帶和認同感,這是凝聚社會或文化的粘合劑,也是幫助人們實現愿望和夢想的基礎”(Zarefsky 2006:386)。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還意識到這篇以陰陽修辭為主題的文章同時也啟發了我自身的研究方法,引導我避免用極化詞匯來描述和評估中國和歐美美學修辭實踐,而是去發展一個新的方式來討論和教授它們。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有助于我約束自身將兩種修辭傳統本質化的沖動,還為我們這些寫作與修辭教師提供一種反思自身教學實踐的批判性思維啟示。也就是說,當教授太平洋任何一岸的學生時,我們現在可以使用陰陽修辭來對我們自己的教育事業以及給學生的寫作閱讀實踐的反饋進行元評論(meta-commentary)。例如,我們可以問自己:我的教學是否受到陰陽修辭的指導和啟迪?它在何種程度上被定于自己的本土語境中進行談論?我對它的解讀又在何種程度上受到我自身所處的環境和持有的主觀立場所影響?我的教學實踐能否容許我自己開發新的交流探討術語或概念(terms of engagement)并思考新的關系和見解?我可以通過怎樣的方式帶領學生理解他們所熟悉的(可理解為那些舊的對立術語)和陌生的(可解讀為那些新興的探討術語)術語?如何讓他們所熟知的變為陌生的,而讓陌生的變為熟知的?或者更理想地,如何把陌生—熟悉的關系從對立轉變為相互依存?舉些具體例子,我們怎樣才能讓(我們較熟知的) 孔子和他的《論語》或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論修辭》變得更加陌生?又該怎樣使(我們較陌生的)中國古代的政見文(policy essays)或古代近東的女性哀歌 (lamentations) 變得更加熟悉?再者,我們要如何讓八股文或演講文(epideictic speech)變得陌生,而讓中國當代作品變得更為人所熟知?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將課堂內外所涉及的討論內容提升到更高且更有活力的水平上,使學生可以通過對立統一關系來全新地了解中國和歐美的修辭實踐,并使塑造自我與他人之間共同紐帶的前景變得更加明朗和迫切。
毛履鳴(Mao Luming),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英語博士,現為美國猶他大學修辭寫作系主任、教授。原為美國邁阿密大學英語系主任、教授。主要從事西方修辭、中西比較修辭、批評語言學以及英語寫作教學與研究。出版專著、編著七部;在美國修辭學核心期刊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和Rhetoric Review,現代英語文學語言研究核心期刊PMLA,國際語用學核心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大學英語修辭寫作核心期刊College English和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JAC,語言文學期刊Style等刊物發表論文五十余篇。
注釋
① 物化是使抽象的想法或概念具體化或真實化。
② 中文詞“氣”有很多英文譯文,包括:“能量”“以太”“蒸氣”,甚至是“呼吸”。Sivin定義了氣或其在中國約公元前350年的有關自然的描繪中的使用為“既是‘事物中促成事情發生的物質(what makes things happen in stuff)’又是(取決于上下文)‘促成事情發生的物質(stuff that makes things happen)’或是 ‘發生事情的物質’ (stuff in which things happen)”(47)。欲了解更多關于氣的豐富含義,請參閱Sivin(46-53)以及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