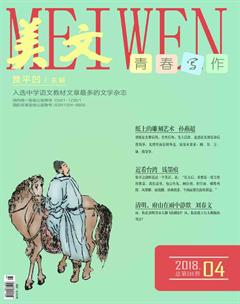歷史的復(fù)原者何時出現(xiàn)
徐丹彤
累累白骨,層層尸墻,悲慘過去不能忘;
輕薄一哂,何其不尊,敬畏之心應(yīng)長存。
游客在大屠殺紀(jì)念館前的搞怪留影,說到底是一種敬畏感的缺失,一種人為的失憶,一種自欺欺人的麻痹。
生而為人,都會對大屠殺紀(jì)念館中的凄唳心驚肉跳。那些令人窒息的殘忍,那些無所安放、無處訴說的苦難,一遍遍地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曾上演過的荒誕劇,為要阻止地獄再次降臨。然而,游客在這種情況下搞怪,分明就是刻意遺忘建立紀(jì)念館的初衷,遺忘沉重的歷史。這遺忘的背后是怯懦和軟弱,是不堪大任、不明事理的逃避和退縮。
選擇忘記歷史的人,就像只盯著遺產(chǎn)而不講痛感的遺孀。但是,罪,在一百年后仍然是罪,假寐的灰燼伺機還會復(fù)燃。
也許正是因為了然這一切,才會有美國“越戰(zhàn)產(chǎn)業(yè)”的出現(xiàn)。《野戰(zhàn)排》中人類的自私與嫉妒、《獵鹿人》中俄羅斯輪盤賭的荒謬與瘋狂、《現(xiàn)代啟示錄》中科茨的癲狂與崩潰,無不令人心有戚戚。好萊塢一次次地把曾經(jīng)的丑惡搬上銀幕,既是它勇敢面對歷史的體現(xiàn),也是它更深一層的良苦用心:把荒誕一遍遍地展示給人們,讓我們時刻警醒人類的欲望多么可怕,而和平、幸福、公義、良善這些詞匯,也絕不僅僅只是裝點門面的假大空話。
魯迅先生曾說我們是善于遺忘的民族,所以,對國人來說,“不忘記 ”意味著挑戰(zhàn)民族的劣根性。我們的同胞中不乏在大屠殺紀(jì)念館前搞怪的,不乏騎在英烈雕像上留影的,但我們的聲討力度相較之西方卻要小得多。
因此,國人要想撿回丟失的敬畏之心,更需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我們要收起怯懦的嘴臉,挺起胸膛,承受歷史的批評,反思未來的走向。另一方面,面對“忘記”,我們的批評聲潮應(yīng)該更兇猛、更浩大,讓忘記無所遁形。
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期盼著中國式的“越戰(zhàn)產(chǎn)業(yè)”,期盼著我們自己的《辛德勒名單》的出現(xiàn)。知識分子的良知是時候該蘇醒了。
我們何時有自己的歷史的復(fù)原者?也許在很遠的將來,也許就在不遠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