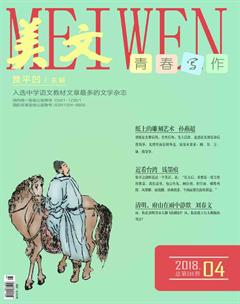功夫天使
何杰

1
盛夏,一天,我和我愛人去城外尤若瑪拉海濱游泳。
回來,從火車站通道剛走出來, 我們就糊里糊涂地卷進了跳舞的人群中,有人還把小甜點和糖果塞給我們吃,拉起我們手一邊走,一邊跳。車站外更是人聲鼎沸,音樂悠揚。琴聲、鼓聲以強烈的節奏鞭策著人們,你不想跳,也不由自主地跳。那音樂像我們的新疆樂曲,非常好聽。舞步也簡單,前進三步,后退兩步,出了通道就跳成了圈。
不過我那位在外從不茍言歡的“老愛”根本不會跳舞,不是撞了前面的人,就是踩后面的腳。而我們倆中間,不知什么時候插進來一個中年婦女,個子不高,也跟著歡跳。“老愛”踩她,她踩我。“老愛”穿的是大頭鞋,那婦女穿的是高跟鞋。哎喲!我們疼得“吱吱呀呀”又是叫,又是笑。擠出人群,我們便聊起來。原來,那是從以色列來拉脫維亞的旅游團,高興,他們就跳起舞來。那婦女叫Rosenbaumsky, 外國音記不住。 (多虧我帶著多語詞典,查了半天 ,德語翻譯為“玫瑰花”)。站定,“玫瑰花”打量我們,聽說我們是中國人,立刻高興地嚷起來:
“中國功夫!中國功夫!”
出國就知道了,外國人對中國了解寥寥,但最多的是“功夫”。我們告訴她,我們練太極拳。“玫瑰花”深陷的大眼睛一下飛出了火花。
她說,她和她的許多朋友正想學太極拳呢!
“玫瑰花”瞇起她的大眼睛,一副迷戀之情:
“中國功夫神秘!”
“玫瑰花”請我們一定要教她中國功夫。說實在的,在國外,寂寞的我們巴不得有朋友,巴不得到什么新鮮的地方去看看。去哪?
2
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只知道“玫瑰花”邀請我們去見她的朋友。
那是一棟大樓,里面有許多活動室。在樓下,我從一個房間敞開的門縫看見有印度人在佛像前燒香。周圍坐著好幾個人。那天,我又感到印度文化傳播做得真好。因為大街上常看到印度人在舍飯。我想排隊,沒好意思,主要是想看看他們吃什么。又一次,看清了:酸奶油拌米飯,而且用手抓著吃。我跑了。
那天,房間里又在舍飯,一股奶油香味。白給吃的,人不多。
上樓,好幾人出來迎接我們,其中有個中年婦女。
“呀,玫瑰花”!
幾天不見,怎么長高了?我正在糊涂,又來一個“玫瑰花”,深陷的大眼睛。她忙給我介紹,個子稍高的那位是她的妹妹Rosenbalmsky,“ 玫瑰樹”。“玫瑰花”“玫瑰樹”。天呀!外國人的名字我本來就搞不清,她倆長像又一樣!我很長時間都分不出她們誰是姐姐,誰是妹妹,而更暈頭轉向的還在后面。
上了二樓,他們的門都沒有玻璃窗。推開一個橡木大門,我和“老愛”真是“老豬上戲臺——愣住了”。
大房子里一排一排站滿了人,連屋角的桌后邊都是人。
那天才知道,“玫瑰花”帶我們來的地方是市里的文化中心。不少國家都在這里設立了活動室。日本人、印度人都在這里開展文化宣傳活動。
我們的房間最大,人真的都擠到門外來了。我們高興,又“砰砰”地心跳,真如大使囑咐我的:“你是中國語言、文化使者,做什么都事關重大。”沒想到我來支教,把“老愛”也拉進來了,而且一切都是那么意外。
自己祖國的文化在國內并不注意,到了國外才知道,中國功夫為什么淵源流長,那么富有魅力。我感慨良多。
流水下灘非有意,白云出岫本無心。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老愛”說他的學生何止是“柳成蔭”,那是“桃李滿拉脫維亞”——成林啦!
“老愛”的太極拳愛好使我們有了許多新學生、新朋友。
而這些新朋友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那么新奇。
3
和新朋友聚會,每次都覺得是在翻看一本文化大書。
一次,在文化活動中心鍛煉。
“喂!助教!助教!”
“老愛”對我的稱呼總是因地制宜。沒辦法,他是教練。此刻,我正幫他教老外們打太極拳。
你說,人家也不是請你上課,大家湊在一起散散心,樂呵樂呵,干嘛這么認真?他在前面教,還要叫我在下面給他的弟子們糾正動作。我喜歡比較劇烈的運動,打劍還湊合,打太極拳就覺得太慢了。自己打都糊涂著呢,還指導別人?
“干嘛?也沒人給你發工資呀。”
我還沒嘟噥出來。教練又在提醒我:
“喂!看,那姿勢可都沒到家。”
教練做什么事都較死理兒。打起招式來,就差用尺量了。教練一邊打著拳,一邊用漢語對我說。這幫朋友一個也不懂漢語,我們可以暢心所欲地用漢語:
“喂!老婆!助教!咱得認真點兒。注意!他們腳尖的方向!看兩姐妹的胳膊,那叫打拳嗎?用力!喂!手心向里……”
助教,還真難“助”。教這些西方人打拳,簡直是“土地爺抓螞蚱——亂套了”。“倒卷洪”像猴子抓耳撓腮。“懷抱琵琶”像抱個大木桶。我忍不住要笑。他們一邊打,還一邊喊救命:“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胳膊腿都不知往哪兒放。
放松,放松,不就行了唄。
不,還非想學會。尤其倆姐妹更把太極拳打成了舞蹈。打得那叫一個美呀!
我真不想糾正他們。確切地說,像以色列舞蹈。我有過一個比我還大的以色列學生伊妮。她給我講過他們的逾越節,也給我表演過他們的舞蹈。
我說,你們打拳像跳舞。
兩姐妹說,他們總跳以色列舞蹈。聊起來才知道,兩姐妹還有帶來的朋友,大多是猶太人。
猶太人。
出國前我只是從書中、電影中看到猶太人,當他們真的站在我眼前時,我完全分不出他們與其他民族的差別。兩姐妹伸出了胳膊:
“看,我們的皮膚有些蒼白,頭發比柳霞(俄族人)顏色深,大多黑棕色,男人的毛發更重。”
和他們在一起后,我才知道德國法西斯為什么能一眼就知道誰是猶太人。
他們的名字都有猶太人的特點。猶太人最早并沒有姓氏,大流散后,他們散居到各國,被強迫登記時,強加上姓氏,所以有許多姓相同,名也更隨意。愛因斯坦einstein,其實就是“一塊石頭”。兩姐妹的名字也是猶太人名。后面有“sky”。表示是俄羅斯的猶太人。
4
那天我也才知道,猶太非常喜歡跳舞。他們喜歡跳舞是有歷史原因的。相傳,猶太人在埃及受埃及人奴役,他們決心逃出來。經過千辛萬苦終于渡過紅海。女先知米利安拿起手鼓跳起舞,眾人也抑制不住快樂,高興地跳起來。從那時起,在海灘上、廣場上、街巷里,慶祝勝利、敬神、歡慶豐收、節日,甚至婚禮上都會跳舞。猶太人立國后,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民族如此熱愛跳舞,吉普賽人也難以相比。
一天,兩姐妹和她的朋友們特地為我們跳起他們的舞蹈。他們說,叫“功夫教練好好地休息休息,看看他們的功夫”。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些猶太人皮膚白皙,身材柔美,個個優雅。
看著這個優秀又受盡苦難民族的胞民,我真是五味雜陳。
大廳里沒有人穿鞋子,但能聽見心行走的腳步聲。舞在涓涓波涌,流水行云。柔軟的襯衣衣袖,云一樣,霧一樣,心魂都在舒緩、飄蕩。
那舞有很多的旋轉。
音樂旋律優美,悠長。我覺得有些哀怨,傷感。
那舞出自一個多難民族的魂魄,是在他們千百萬心靈的尋覓、撫摸下雕刻而成的。
他們旋轉著,身后是命運的拉扯。歲月的眼睛告訴我:
兩姐妹在二戰法西斯大屠殺時,隨母親在俄羅斯莫斯科大學,躲過死亡的搜索。蘇聯時期,兩姐妹大學畢業被分派到拉脫維亞,在一個發電廠成為電氣工程師。兩姐妹有過幸福的童年,卻都沒有幸福地找到她們的另一半。什么原因?
兩姐妹向我聳肩、搖頭:或許她們信奉猶太教,這里大多是東正教,或許她們來自那個大國俄羅斯?說不清。
拉脫維亞獨立了,她們卻失業了。她們和同胞朋友們錢袋拮據了,時間富裕了,聚在一起,溫暖一下彼此的心。
他們旋轉著,跳著祖輩就跳過的,尋找生路的舞蹈。
1997年,德國向二戰期間受難的猶太人道歉,并在德國設立猶太人救濟所。那時,兩姐妹聯系準備去德國。
5
這里的雪一下起來就像鋪棉絮一樣,給你鋪天蓋地的裝點。我家附近的庫庫莎山丘銀裝素裹。
教練——功夫天使,步履輕捷,身輕如燕。他揮舞著長劍在飛雪中作畫,瀟瀟灑灑。
手中的劍像飛流直下的瀑布?像劃過云天的閃電?像五線譜的高音弧線?語言在那真實的美中總是顯得蒼白。教練的劍在異國被這些崇拜者檢閱著、寵愛著,如此優雅、好看。
功夫天使那天打得格外動情。妹妹站在教練身旁,一招一式地錄著像,姐姐站在遠處,仍然在一招一式地模仿。
明天,兩姐妹就要走了,而我明天得帶著學生為國內從深圳來拉脫維亞的商展做翻譯,不能送她們。
此刻,我們只有緊緊地擁抱 。我告訴兩姐妹,開春我們也要回祖國了。
姐姐和妹妹的眼里都涌出了淚花。
“真羨慕你們,你們有祖國。”因為有兩姐妹這樣的朋友,我曾經叫學生幫我跑了十幾個圖書館——小小的里加竟有64個圖書館,雖然中、英文文獻很少,但我還是查到了關于猶太人的一些歷史。
猶太人祖先是希伯來人,“游牧民族”的意思。他們最早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后來遷徙到巴勒斯坦,成了埃及人的奴隸。公元前13世紀,他們逃出埃及。我的學生跟我講過以色列人的逾越節,就是為紀念這次勝利的出逃。后來他們在迦南(現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王國,定都耶路撒冷。公元70年羅馬帝國稱霸。耶路撒冷圣殿被羅馬人毀之一炬。絕大部分猶太人特被趕出巴勒斯坦地區,流散在歐洲各地,圣殿始終未能恢復。后來,在圣殿斷垣殘壁的遺址上修建起圍墻,雖然是伊斯蘭圣地圍墻西墻的一段,但猶太人仍然珍惜它,這段墻被視為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哭墻”。
兩姐妹告訴我,她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耶路撒冷。
猶太人反叛羅馬失敗,離散到世界各地,經過兩千年的流亡,1948年建國。
那天真冷,雪花都可以立在你的臉上和眼睫毛上,我的心也在結冰。
兩姐妹走了,不是去他們的祖國。
茫茫風雪中,兩姐妹走了,帶著許多的依戀和遺憾。
我還在拉脫維亞時,是那樣想念我的祖國,我的家。
6
高興的是,每次從來信中都得知她們很幸福。
她們先是在漢堡學些德語,一年后,將給她們安排工作。姐妹倆在學德語的時候教學友學起打太極拳。她們的朋友們竟叫她們是中國功夫天使。
那時我還在拉脫維亞。
后來,我回國,去德國開會,本約定相見,但由于會議時間緊迫,她們在波恩,我在漢諾威。沒見成。
但我收到她們的明信片。
她們寫給我們:“不要再為我們的分別而難過了。”
她們告訴我的最后一句猶太人俗語,叫我至今難忘:
“天上的云總會飄走,太陽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