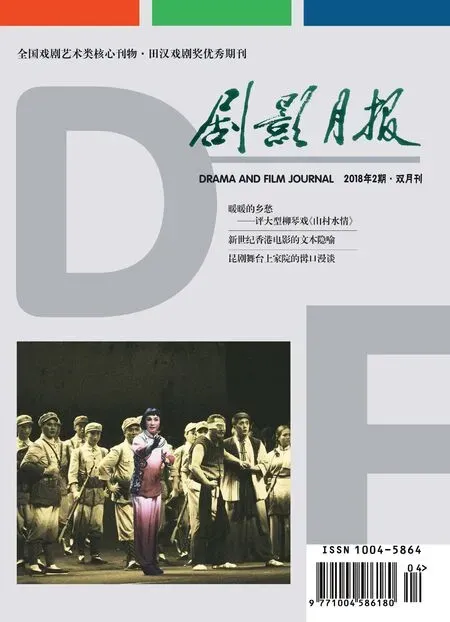二胡演奏的時代性
■ 朱小川

二胡,最早是古代胡樂樂器,“胡”是古代中原對我國西北部個別少數民族的稱呼,后來由于戰爭與大統一造就了文化的融合雜糅,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碰撞使胡琴應運而生。二胡則是胡琴家族的代表,是我們中華民族樂器的瑰寶之一,極具代表性。它從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起源到如今,前一千年的時間都是在一個民間底層百姓中流傳,它主要用于戲曲和說唱表演的伴奏,是社會最底層人謀以生存的東西,所以直到現在還給人“叫花子”樂器的印象。它是在沒有規范的方法和自由渙散的教育模式狀態下流傳存在的。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二胡發展緩慢。
二胡繁榮的起始應該是在20世紀初。我國優秀的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先生一改二胡前態,在演奏技巧等方面將二胡徹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讓二胡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十首二胡作品:“良月苦獨病,燭光悲空閑。”即《良宵》《月夜》《苦悶之謳》《獨弦操》《病中吟》《燭影搖紅》《光明行》《悲歌》《空山鳥語》《閑居吟》把他對二胡技法的大膽革新以及對民族音樂的自信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的47首二胡練習曲是二胡系統教學第一部教材,為二胡走進高等藝術院校成為一個成熟的專業起了鋪墊作用。演奏技法方面將二胡標準定弦和傳統把位的劃分規范起來,結合小提琴的技法大膽開創高難度技巧,如極高把位、轉調、一弦格、左手輪指、大幅度跳把,將表現力低下,技巧貧乏的二胡改頭換面。這堪稱二胡的一次大革命。并且這一時期的華彥鈞,憑著自己豐富音樂經歷和天賦鉆研,在音樂中糅合了絲竹、梵音、民歌小調、地方戲曲(錫劇)的特點,技法上繼承并延續了劉天華先生,譬如富有頓挫棱角的滑音,在一個把位中通過手指伸展擴大音域,浪弓等。劉天華的弟子們也繼承發展了劉天華的演奏藝術,如儲師竹、陳振鐸、劉北茂(劉天華胞兄)、蔣風之等。其中蔣風之的古樸典雅,濃重的文人氣息使得他的演奏藝術獨具一格。這一時期的人演奏二胡符合了時代性,那就是從民間狀態到專業學科的躍進,技法上不斷推陳出新,大膽而富有自信。且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存在著豐富的社會時代背景,寄托了作者演奏者的感情。
新中國成立后,二胡的發展又上一臺階。二胡曲的創作日益增多,演奏技法和新技法的拓展,快弓以及不同指法的變換,如《拉駱駝》《山村變了樣》等。張韶先生用講座的形式推廣普及二胡知識;專業性的賽事中脫穎而出的優秀作品和表演人才,如王國潼首演的《豫北敘事曲》《三門峽暢想曲》,高難度技法在現如今來看都是相當磨練人的。還有較多富有地方風格的曲目出現,如《秦腔主題隨想曲》《迷胡調》《河南小曲》等,這就給二胡的發展指出了一個鮮明且端正的發展道路,技術大膽開拓亦是為了更好地演奏中國民族音樂。可惜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對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二胡發展也不例外。但是它也富有時代性,那就是演奏樣板戲唱段,這一時期模仿戲曲唱腔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也應了閔惠芬老師提出的二胡聲腔化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之后,陳耀星的《戰馬奔騰》,朱昌耀的《江南春色》,尤其是劉文金作曲閔惠芬首演的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開辟了二胡長篇幅協奏曲、組曲的時代。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后,狂想曲、西方移植曲目盛行,全國的二胡整體水平大大提高,二胡開始高度普及化。這一時期是二胡發展的較成熟階段,這一時期的二胡演奏格局大,技巧難度突破,專業院校的二胡教學體系逐漸完善。與外界交流合作增多,讓世界更多人知道了二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熱潮使得外來的流行音樂文化如日中天地紅遍江南海北,我們的傳統音樂失去了往日的繁榮,專業院校開始流行學習演奏西方移植作品,或者我們本土的高難度二胡作品。近十年至二十年間,沿著這條路,二胡演奏在技法上又屢屢創造新高。

時間一久,傳統的東西漸漸趨于被動,甚至有被摒棄之嫌。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傳統文化的復興被提做重中之重。所以,現在的傳統藝術,戲曲的傳承發揚得到了提倡,國家下發相關文件大力支持。戲曲,這一中國古老的藝術表演形式,蘊含積蓄了多少歲月和智慧的結晶。優質的戲曲演出需要好的演員,更需要各方面素質都高的樂隊演奏員。戲曲伴奏和獨奏不一樣的是,他不僅需要有扎實的基本功還要對于劇情走向,人物內心獨白等有著敏銳的感知和恰當的潤飾和藝術處理。這是一個人的樂感還有對于作品的理解力。例如,我們熟悉的孟姜女的傳說,是一直被各劇種重用的題材。經歷過整場的伴奏,我們從演員的深情演出,還有自身全身心投入的伴奏,體會了孟姜女與范喜良從一開始的結識相愛成親的歡樂,到后來被逼迫的分開的煎熬,孟姜女千里探夫到后來得知丈夫死后崩潰哭倒了長城的人物心理,最終是對壯美的真摯不渝的愛情的贊頌。戲曲這一藝術形式有個特點是夸張,也正是這種夸張才能很大程度促成我們懂得怎樣去用自己的心舍身處地去投入劇情。對于理解一個作品要去了解它的背景,深層次剖析人物心理。這不得不使我想到二胡作品《新婚別》,這首大型敘事曲是根據唐代詩人杜甫的“三別”詩中的的“新婚別”創作的二胡敘事曲。講述了安史之亂時一位女子新婚的丈夫被強行征去當兵,女子對愛情忠貞不渝卻難逃封建勢力的壓迫。樂曲中她悲痛痛苦的地方的表現就用到了戲曲的哭腔、快板等。兩首作品講述的故事,時代背景都大同小異,伴奏過戲曲《孟姜女》然后再去理解完成《新婚別》,就會知道如何去抓住人物的特點,心理活動變化以及對整首曲目整體的線條與節奏,情節變化的尺度掌控。
二胡發展的長河從風平浪靜再到波瀾壯闊,生生不息,每個時代都每個時代的特點和標志,只有緊跟時代性的演奏才會浪頭一樣帶頭前進。如今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我們正在康莊大道上行走,終覺民族復興最終的意義乃是文化文明的復興,傳統與民族的根乃是我們前進的穩固動力與依據,我們認清這個時代的特點與標志,豐富自身,用藝術的勇創新高來做時代潮流的浪頭。
而二胡的演奏要符合時代性。一個地域一種文明,藝術植根于文明中,從萌芽到發展再到開花結果甚至流芳百世,每一個必經階段都有著各自的特點。先有傳承,在傳承中積蓄養分,通過研究才可談創新發展,如若操之過急,那么離經叛道,毀壞經典,歪門邪道的事就出來了。二胡演奏符合時代性,更重要的因素是音樂服務于大眾,每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不一樣,我們的二胡演奏也要順應時勢,這是一個生存或昌盛與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