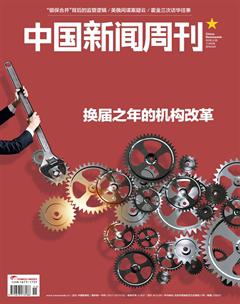李敖這只充滿斗志又自戀的“雄蜂”,終于停止嗡鳴
鄺海炎
3月18日,臺灣作家李敖因罹患腦癌離世,享年83歲。
這個“文化老頑童”生前曾開玩笑,“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夠死于別人丈夫的槍下!”他還奚落其師殷海光不該得胃癌死掉。“他是哲學家、思想家,結果得了這個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樣。這是不對的……”
李敖對大陸青年的影響,首先是他的“叛才人格”。20世紀下半葉,現代制式教育的弊病日益突顯,李敖高中退學,又自學考入大學,這對在現代制式教育中掙扎的中學生來說,仿佛黑夜里的明燈,當年韓寒退學不就有人說他是學李敖嗎?
在李敖看來,教育的病根是社會文化出了問題,教育現代化要從文化現代化著手。但文化解決太迂遠,李敖迅速由“文化”走向“政治”。他在《文星》第九十八期發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批評國民黨,導致雜志被封殺,自己入獄。入獄后,他以驚人的能量每月出版一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出獄后大量為黨外雜志寫文章,后來,又加出“萬歲評論叢書”及《蔣介石研究六集》,成為他一生最光彩奪目的時刻。
但天才與缺憾共生,少年成名、牢獄之災、婚戀之變……多重因素導致李敖沒有安全感,退縮于“斗士”人格一隅,其他方面就變得偏激。他認理不認親,妻子忘記解凍牛排就大罵“蠢貨”;他明白有錢的好處,打起前老板蕭孟能財產的主意;他自大,“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不可否認,李敖的文章有“魯迅的犀利,胡適的明白,陳獨秀的氣勢”,這對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很多青年經歷世事后,又不得不狂吐這口“狼奶”。我本人吐出這口“狼奶”,是根據對李敖學術思想的檢驗。比如,李敖曾說:“余英時用三萬字說清的東西,我用三千字就可以說清楚。”我高中時不知深淺,多年后才明白,說出一個觀點不易,論證一個觀點的成立更難,很多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因為論證了某一假說的成立。李敖觸及的中國思想史命題很多,但像余英時那樣滋養后學的學術思想少得可憐。
又如,李敖咬定“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謀劃的,而楊天石在《中山艦事件之謎》中指出,這是一次各派角力下的偶然事件,連胡喬木都信服;再如,李敖指責蔣介石學歷造假(讀的是振武學校,卻說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大陸學者陳紅民指出,李敖提到的那幾份材料雖是真的,但“很難找到蔣介石本人與那三份造假材料有直接的關系,它們既非蔣介石所作,亦非蔣介石授意寫作……不應讓蔣介石為所有介紹他的文字直接負責”。
李敖在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里感慨康有為“前半生維新變法,后半生維皇忠君”,但晚年李敖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也愈發傳統、愈發雞賊、愈發沒有英雄氣了。他曾批評胡適、梁實秋晚年“穩健”,比不上“當年那種生龍活虎意氣縱橫的氣概”,可胡梁晚年知識分子的風骨還是在的,李敖晚年則淪為“二丑”角色。
但仍要承認,李敖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眾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用政治學者唐琳的話說:“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從俗的、快樂的、嘻嘻哈哈的氣質,它表面上很隨意,但其實具有很強的斗爭性。”
我更認為,李敖是柏拉圖筆下的“雄蜂式人物”。柏拉圖對平民政體始終抱有成見,并認為,這種制度給有野心的政客以可乘之機,易使民主趨向極端。他稱這樣的人為“帶毒刺的雄蜂”,“坐在講壇后面,熙熙攘攘、嘁嘁喳喳地搶了講話,不讓人家開口”。單說善于搶占民眾眼球,李敖確是一只雄蜂。
俱往矣,那些捧讀《李敖大全集》被蜇疼的夜晚。李敖已死,“雄蜂”不再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