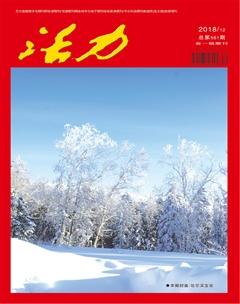余華非理性創作的批判意識
韓雪
【摘要】余華的作品具有先鋒小說典型的代表性。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非理性敘事是余華作品的鮮明特征,這種非理性敘事既是余華對現實社會秩序的解構,又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在新時期文學中具有典型性。
【關鍵詞】余華作品;非理性創作;批判意識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先鋒小說作為一種思潮,在現代文學作品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余華的作品作為先鋒小說的代表,非理性的創作方式是他的鮮明特征。在余華的世界里,現實的社會秩序被非理性的敘事解構,通過非理性的敘事策略,余華試圖對現代文明下的理性秩序進行反證式解構,這種解構姿態使得他的作品呈現出一種批判的意味。
一、對生存秩序的解構與批判
余華說:“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成了裝飾。”在余華的小說中,人的生存狀態與人的精神的理性邏輯是錯位的,人對生活所擁有的一種理性的期望與認識、接受和思考與現實的非理性的生存狀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與錯位。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我”興高采烈的出門,卻被汽車撞的遍體鱗傷。“我”的內心充滿對世界的渴望,但是世界卻給我無法接受的絕望。在《死亡的敘事中》“我”因為受到良心的譴責,想承擔責任救贖自己的時候,卻被非理性的人們給扼殺掉了。這是人生的錯位,是對現實的反諷與批判。
中國的現代性倡導的理性文明秩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混亂。面對這樣的現代性,余華在小說中運用非理性的敘事方法,揭示了人的理性文明秩序在現實社會中如何產生了錯位,從而對現代性進行了解構,也對現實進行了批判。
二、對精神世界的解構與批判
從《虛偽的作品》開始,余華開始追求一種內心世界的“真實”,余華這樣表述他的真實觀。他說,世界是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人的本質是欲望,而欲望充斥著人的精神世界,因此真實的作品應該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因為只有在人的精神世界里真實才是客觀存在。這是一種精神的真實而非現實世界的真實。因此,余華追求的所謂的“虛偽的形式”就是那種看起來“并不真實”的形式,也就是非秩序、非邏輯的形式。“虛偽”指文本形式層面,而“真實”則指文本的精神層面。
因此,從《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始,余華就執著地為讀者展示了一個非理性、充滿暴力而又沒有秩序的世界。在這里,暴力成了人的天性,人都卑微的生活在暴力的籠罩之下。《十八歲出門遠行》里的主人公“我”是一個剛剛步人社會的青年,由于涉世未深,所以在“我”剛滿十八歲的時候就在父親的安排下到外面去闖蕩,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但是對外面的世界懷揣著美好瞳憬的“我”,卻遭遇到了一系列奇遇,“我”為了找到賓館,搭上了司機的運貨汽車,司機對“我”的態度反復無常。當“我”好言相商的時候,司機粗暴地拒絕了“我”;而當“我”怒火中燒,沖他大吼大叫進行暴力威脅之后,他卻答應了搭“我”一程。這叫“我”意識到了使用暴力的好處。汽車拋錨,司機不慌不忙的到一邊去抽煙,汽車上拉載的蘋果卻遭到附近村民的瘋搶。“我”看不過去,上去阻攔,反而遭到毒打。而一旁的司機卻反而哈哈大笑,最后登上村民的拖拉機丟下“我”揚長而去。“我”只能一個人躲在破爛的駕駛室里獨自療傷。
現實的殘酷最終打破了“我”對現實世界的期待,“我”的第一次十八歲出門遠行只能是以失望而告終。小說告訴了讀者這樣一個事實,在成人世界里總是充滿著莫名其妙的暴力,暴力由于其形式充滿激情,所以格外的叫人心醉神迷,一切駛向遠方的文明汽車都會被其劫持和破壞。這部小說是余華嘗試進入非理性創作,對人的精神世界進行解剖和批判的第一次嘗試。
三、非理性創作的批判意義
余華執著于對人的非理性世界的表現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遇到了一個拐點。市場經濟之下,人們開始疏遠政治,逐漸開始正視和關注人的生存欲望和精神世界。但是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比如人的道德水平下滑,精神信仰危機。當過去的宏大敘事逐步退出的時候,人們開始關注直面自我的精神世界。西方現代文學思潮的適時涌入,又為作家提供了突破現實表現的哲學支撐和方法技巧。余華正是從卡夫卡那里得到了啟發,意識到作家的內心真實和敘事話語之間奇妙的對應關系,進而開始對人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進行真實書寫。從創作主體的內心出發,不再遵守客觀秩序和邏輯理性的力量,進行大規模顛覆性的主觀性敘事的嘗試。
余華認為,現實世界是不可信的,生活也是不真實的,生活事實魚龍混雜,只有當生活脫離了人的理性而獨立存在的時候,它才會顯得真實可信。因此,對于任何個體而言,真實只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在進入更為廣闊的精神世界之后,人才會體會到世界的無邊無際,在這里,常識意義上的一切既定價值都被邊緣化,一切舊物都將重獲生機。因為只有人的內心是真實可靠的,文學只有回到人類精神深處,才能獲得對于世界的思索和領悟,這也是幾乎所有像余華一樣的先鋒作家的共識。
客觀地說,這是一次極為有益的嘗試。之所以如此強調精神世界真實的重要性,是由于新中國成立以來,余華認識到現實秩序本身的荒謬和不可信。因此,他才試圖透過理性表象的遮蔽,回歸到人的內心,通過對人的非理性精神世界的關注和表現,去對現實秩序進行解構和批判,進而呼喚和重塑真實的理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