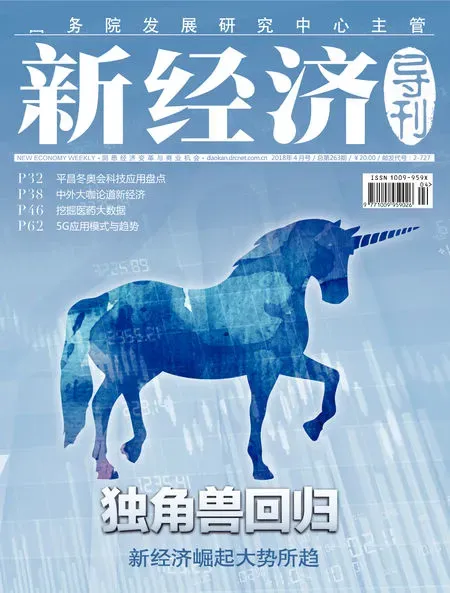產能合作何以是“雙贏”雙升級
文/呂昱江
過去在招商引資時,我們通常講“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現在,好像歷史在重演,只不過主體和對象發生了變化
當前我國政府正積極大力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實際上是世界經濟史上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一場更加深刻而復雜的國際經濟和世界發展格局的大演進。
國際產能合作符合國際產業和經濟發展基本規律,并不是中國的獨創。自工業革命以來,英、歐、美、日等都推動過產業國際轉移,國際產業轉移在世界經濟歷史的舞臺上一幕幕地上演。
國際產能合作和國際產業轉移,也是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發展。國際分工有兩種基本形式,一個是國際貿易,另一個是國際直接投資。當年,美國產業轉出的目的國家(或地區)是與其相同的發達經濟體,且以跨國公司水平投資為主導,是為北北范式;而日本當時產業轉出的目的國家(或地區)是與其不同的發展中經濟體,以由貿易帶動投資的方式逐步展開,是為北南范式。而我國當前正大力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產能輸出的目的國家(或地區)不僅有與我國相同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有發達經濟體,且兼有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方式,但以國際直接投資為主。顯然,中國正豐富著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合作的范式!
并且,在國際產能合作中,中國不會輸出什么過剩產能,也不會輸出污染和“兩高一資”,中國更無意輸出什么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是,可以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可以將中國的發展經驗向世界經濟推廣。
“雁陣模式”后的中國范式

我國正大力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實際上是新的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國際產業轉移并不是新鮮事物。就拿戰后的幾十年來講,曾經出現了西歐和日本承接美國產業轉移的現象,也曾出現了日本對亞洲鄰國(或地區)的產業轉移。
美國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通過“歐洲復興計劃”大量輸出過剩產能,不僅幫助歐洲經濟在二戰后的廢墟上迅速恢復,而且使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反彈,出口增速顯著回升,經濟從谷底進入了數十年的繁榮。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美國經濟學家費農構建了“產業生命周期”的國際投資和產業轉移范式。
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將其產能最先過剩的化學、鋼鐵等產業轉出至亞洲鄰國(或地區),“東亞四小龍”與東盟先后抓住了歷史發展機遇;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輸出產能的行業演變為化工和電器機械,國內則開始大力發展精密儀器、高端機械等設備,“東亞四小龍”則重點吸收美、日、西歐等發達國家轉移出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則由“亞洲四小龍”轉移到東盟國家和中國沿海地區。日本如此逐步依次地將國內過剩、夕陽產業向海外輸送,該國經濟學家赤松要和小島清用形象的“雁陣模式”來總結其成功經驗,描述東亞地區的投資—貿易格局。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優質產能如今業已具備了跨出國門、走向全球的雄厚實力。在中國,過去的30年,各級政府采取鼓勵出口、招商引資的發展模式,經常實現雙順差,外匯儲備規模相當可觀,這當然是體現我國綜合國力極大提升的重要指標。不過,長期的貿易和經常賬戶順差,會帶來人民幣面臨內向貶值、外向升值的嚴峻壓力,等等一系列問題,也會影響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現在,中國許多產業的企業被鼓勵“走出去”,到其他國家投資,目標之一就是減少貿易項下的順差,同時增加投資方面的收益。
而中國當前在國際產能合作中,產能輸出的目的地不僅有與其相同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有發達經濟體,且兼有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方式,但以國際直接投資為主。中國正豐富著國際經濟合作的范式!
內升級:投資為主,輸出和承接并重
從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的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重點行業在國際產能合作中的主要任務來看,可以得出我國政府力推的國際產能合作主要是以擴大對外投資的方式展開的結論。
過去,我國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對外貿易。當地人可能會認為中國把其當成了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從而會有一定的負面情緒,甚至抵觸。然而,投資可以解決當地的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實現工業化。當前,我國推進的國際產能合作主要是投資,那么當地人應該是相當地積極。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伴隨著政府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力度的加大,中國許多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大幅度增加,那么,這會不會對我國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出口,產生不利影響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的一個著名的經濟模型就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出口有替代作用。然而,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費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還有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之間,是互補的關系。
我國正在力推的國際產能合作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使我國具有一定優勢的產能“走出去”,而我們的優勢產能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產能向國外轉移,的確會使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受到影響。
不過,當前正力推的國際產能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境外先進的技術、工藝引進來,推動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我國在對外輸出產能的同時,一直注重承接先進產業國際轉移。
引資方面,《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修訂稿鼓勵外商投資現代農業、高新技術、先進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現代服務業等領域,鼓勵外資在研發環節投資,推動引資、引技、引智有機結合。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吸引外資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一大批新的對華投資合同誕生。聯合國貿發會近期對全球主要跨國公司的調查也顯示,中國繼續在全球十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當中排名第一。
進口方面,根據《關于加強進口的若干意見》和具體面臨的國內需求及產業發展情況,相關部門也一直積極引導企業擴大先進技術、重要裝備和關鍵零部件、緊缺資源性產品進口,進一步研究調整《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
同時,相當重要的是,對外投資往往引致東道國產生進口需求。推動鋼鐵、有色行業對外產能合作中,建設鋼鐵、有色生產基地,可以帶動鋼鐵裝備對外輸出和革新發展;而結合境外礦產資源開發,開展有色金屬冶煉和深加工,亦可以帶動成套設備出口和發展升級。
另一重要方面,我國在對外輸出產能的同時,亦非常注重通過跨國并購和對外直接投資延伸產業鏈,開拓自己尚不具有很強比較優勢的領域。在“走出去”方面,可以看出,不僅僅在從前我國對外投資經營已較成熟的亞非國家,當前包括歐洲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也都非常渴望中國投資的到來。以英國為例,已逾500家中國企業落戶英國,中國企業廣泛參與了英國機場、水務、空港城等基礎設施建設。
西方發達國家都是服務業大國,隨著中國經濟模式從投資、出口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西方國家的服務業,包括創意、藝術等產業都將迎來更多機遇。而對于我國自身來說,很多企業通過在海外尤其是發達國家和地區建立研發中心,可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資源和人才,許多企業通過并購國際知名企業的某個部門,可以獲得其成熟的品牌、渠道、技術等資源,從而反作用于國內的產業升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外升級:不僅僅是傳授技術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費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業的產品處于標準化階段時,逐步從產業輸出國轉移出來;而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產業轉移應該從產業輸出國的比較劣勢產業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那么,中國在推進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哪些產業會相對容易轉移出去,哪些相對來講會較晚轉出?
中國當前所處的時代跟費農、小島清等學者所研究的時代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要拋開實際來討論是不科學的,必須根據各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發展時期具體實踐的情況來研究。
費農、小島清時代的國際產業分工特點和現在的國際產業分工特點差異很大,當前,國際產業分工、工序分工比較深刻。可以說在最近十年當中,中國所有的產業,從農業到制造業到服務業,都在“走出去”,都在進行各種不同類型的國際產能合作。
如果說產能國際輸出有什么順序的話,從整體規模上來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可能相對“走出去”得更快一些,而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現在也在逐步推進。《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為重點行業,分類實施,有序推進。
可是,這些產業都是相對來講比較不容易轉移的行業,因為這些產業基本都屬于重工業這一類。按照已發生的產業轉移的情況來看,一般是先輕工后重工。輕工對產業配套的要求、對技術水平的要求,相對來講比較低一些,所以容易先轉移出去;而像石化、鋼鐵等產業,都需要當地能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和發展能力。
大工程、大項目必然需要相當多的中間環節的技術人員以及管理人員,可是這種需求,在中國推進國際產能合作中,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推進的過程當中,往往是非常難以得到滿足的。從中國帶過去不現實,成本太高且不符合東道國的政策和意愿,東道國愿意展開合作的初衷本就有解決其國內的就業,如果再過多引進中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則或會引起東道國許多人士的不滿,以及其他諸多相關問題。
“授人予魚不如授人予漁”,授人予技術不如授人予方法。在我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進程中,顯然不僅要將技術教會給對方,還要向對方展示成熟的管理經驗。
盡管我國各級政府和企業在國際產能合作具體項目的落實中,都非常積極、樂觀,效率也非常之高;然而,往往會發現對方的政府和企業效率可能會非常低,甚至幾乎無法和我方形成積極的協作和互動,這并非短期內可以解決的。中國在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戰略時,需要輸出自身有效的公共管理模式、成功的發展經驗。
在國際產能合作中,中國不會輸出什么過剩產能,也不會輸出污染和“兩高一資”,中國更無意輸出什么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是,可以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可以將中國的發展經驗向世界經濟推廣。
過去在招商引資時,我們通常講“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現在,好像歷史在重演,只不過主體和對象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