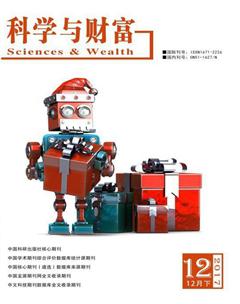DRM范式下青少年錯誤記憶的研究
摘 要: 目的 為了探究青少年錯誤記憶的水平及年齡對錯誤記憶的影響,進行了青少年錯誤記憶的實驗研究;方法 采用被試間設計,在DRM范式下,以漢語詞匯為學習材料,將被試青少年分為8歲半組、11歲半組、15歲半組進行實驗,使用SPSS19.0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 年齡對青少年正確記憶及錯誤記憶均有顯著影響; 結論 不同年齡階段青少年的正確記憶及錯誤記憶均有顯著的差異。
關鍵詞: 錯誤記憶;青少年;DRM范式
1引言
記憶是指大腦對其經驗過事物的識記、保持、回憶以及再現或再認,記憶是進行思維、想象等高級心理活動的基礎[1]。在19世紀末,德國心理學家Ebbinghaus開創了記憶的科學研究領域。1932年,Bartlett發表了《記憶:實驗社會心理學的一項研究》一書,指出了記憶研究的一種新取向:使用故事和圖畫等有意義的材料進行研究[2]。錯誤記憶的研究直到20世紀70年代左右逐漸進入學者們的視線。當一個人錯誤地聲明一個新詞或事物他曾經見過或經歷時,錯誤記憶就發生了[3]。E.F.Loftus等人提出了誤導信息干擾范式,考察干擾信息在錯誤記憶中的作用[4]。Roediger和McDermott結合了Deese的研究[5][6],提出的Deese-Roediger-McDermott(DRM)范式,則是基于單詞的錯誤記憶研究方法,這是研究錯誤記憶的經典實驗范式。一般而言,經典的DRM范式中包括36個詞表,每個詞表由一個未呈現的目標詞,也被稱為關鍵誘餌(如炎熱),和與它相關聯的15個學習項目(如夏天、出汗等)組成,結果發現被試往往在及時回憶測驗中以很高的幾率報告那些高關聯詞。近年來一些學者采用DRM范式及其多種變式,控制各種不同的實驗變量進行考察[7]。結果發現,錯誤記憶容易受到詞表容量、呈現方式、間隔時間、測驗效應、重復學習、預警提示、年齡因素、遺忘癥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從Piaget的認識發展理論來看,7、8歲至14、15歲正是思維由具體運算階段轉向形式運算階段并逐漸成熟的重要時期[8]。本實驗希望能夠更進一步探索青少年錯誤記憶發生、發展的一些規律。研究青少年的錯誤記憶現象,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記憶效率,提高學習效率。此外,對于青少年錯誤記憶的研究,也可以推廣到青少年目擊證詞等方面,能夠較好地避免錯誤的目擊證詞,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2研究對象與方法
2.1對象
本實驗選取了南京市某小學二年級某班(八歲組,實際年齡約為八歲半,因為在五月份做的實驗,成長了半歲)40人、五年級某班(十一歲半組)36人及某中學初三年級某班(十五歲半組)34人進行了研究。實驗前獲得了學生、校長、班主任及學生家長的同意。
2.2研究工具與過程
實驗采用被試間設計,三個班級即為三個組。實驗地點為各學校的計算機教室。實驗開始前,先給同學們展示實驗指導語:同學們好,下面你將參加一個記憶方面的實驗,請記住幻燈片上呈現的漢語詞,每個詞呈現5秒鐘,一組呈現完后會出現一幅畫供大家欣賞,六組詞匯全部呈現完畢之后,開始測驗,測驗的任務是在所呈現的詞表中,分辨出哪些是剛學過的,哪些是未學過的。請各位同學獨立完成,不要互相交流。
隨后,采用郝興昌編制的DRM詞表(該詞表中的詞匯經過二年級老師的確認,同學們完全掌握)進行正式實驗[9]:隨機將測驗詞的顏色設置為紅色或者藍色, 每種顏色各包含45個項目詞。DRM詞表用幻燈片的形式統一呈現,每個詞自動呈現5秒鐘,每組詞表呈現完會有個20秒的分心測驗。六組詞表放映結束后,給同學分發試卷進行測驗。試卷包含了90個學習項目、6個關鍵誘餌及54個無關詞,共150個詞,隨機排列。試卷有兩套,一套測驗詞全部為紅色、一套測驗詞全部為藍色,每個班各一半同學使用紅色測驗卷或藍色測驗卷。20鐘后統一收回試卷。
3結果
數據收集完畢后,采用SPSS19.0進行分析。
3.1 學習詞的再認率
表1 學習詞再認率的2×2×3重復測量方差分析
由表1可知:
圖1 記憶的年齡效應
(1)測驗詞顏色的主效應不顯著;
(2)年齡的主效應顯著,對年齡進行兩兩比較,結果見圖1。學習詞在8.5歲與11.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學習詞在8.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學習詞在11.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
(3)學習詞顏色的主效應不顯著;
(4)學習詞和測驗詞的交互作用顯著。簡單效應分析表明,當測驗詞為紅色時, p<0.01;當測驗詞為藍色時, p<0.01;
(5)年齡和測驗詞的交互作用顯著。簡單分析表明,8.5歲在測驗詞顏色再認上無顯著差異(p>0.05);11.5歲在測驗詞顏色再認上無顯著差異(p>0.05);15.5歲在測驗詞顏色再認上邊際顯著(p=0.06)。僅在15.5歲時藍色測驗詞的再認率高于紅色測驗詞。
(6)學習詞、測驗詞、年齡的交互作用顯著。對交互作用進行進一步的簡單分析可知,年齡為8.5歲時,測驗詞和學習詞的交互作用顯著(p<0.05);年齡為11.5歲時,測驗詞和學習詞的交互作用顯著(p<0.05);年齡為15.5歲時,測驗詞和學習詞的交互作用顯著(p<0.05)。
3.2關鍵誘餌的虛報率
表2 關鍵誘餌虛報率2×2單因素方差分析
注:*p<0.05, **p<0.01, ***p<0.001
由表2可知:
(1)對于關鍵誘餌虛報率進行探究,測驗詞顏色的主效應不顯著;
(2)年齡的主效應顯著,對年齡進行兩兩比較,結果見圖1。關鍵誘餌在8.5歲與11.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關鍵誘餌在8.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關鍵誘餌在11.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
(3)年齡和測驗詞顏色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3.3無關詞的虛報率
表3 無關詞虛報率2×2單因素方差分析
注:*p<0.05, **p<0.01, ***p<0.001
由表3可知:
(1)對于無關詞的虛報率進行探究,測驗詞顏色的主效應不顯著;
(2)年齡的主效應顯著,對年齡進行兩兩比較,結果見圖1。無關詞在8.5歲與11.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無關詞在8.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無關詞在11.5歲與15.5歲上有顯著差異(p<0.01);
(3)年齡和測驗詞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4討論
4.1年齡特征及認知發展水平對青少年正確記憶的影響
人類的基礎記憶能力呈倒U型發展趨勢[10],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大腦發育的完善,基礎記憶能力逐漸增強,成長到一定年齡(一般為12、3歲)基礎記憶能力達到巔峰,并且基礎記憶能力會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直到某一年齡(約為30歲)。實驗中,青少年的記憶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11.5歲青少年的記憶能力是最突出的,雖然在15.5歲時記憶能力不如11.5歲,但仍遠遠高于8.5歲青少年。根據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人在7~11歲時的認知水平處于具體運算階段,8.5歲的青少年其認知水平還屬于具體運算的較低層次,因此不能很好的運用記憶策略,記憶編碼過程也更多的依靠事物的外部特征。人在11~15歲時的認知水平處于形式運算階段,這時候認知發展水平較為完善,這一階段人們能夠很好的運用記憶策略,這有助于正確記憶水平的提高。因此,11.5歲青少年的記憶能力高于8.5歲青少年。因為11.5歲青少年能夠主動運用一些記憶策略,強化了記憶能力。但是實驗中15.5歲青少年的記憶能力顯著低于11.5歲青少年。依照過去的研究,記憶能力不應該15.5歲時就開始衰弱。經過分析,這可能跟學習詞顏色與測驗詞顏色不同有關。由于學習詞、測驗詞和年齡間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即測驗詞顏色的改變,使得青少年在記憶編碼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并且15.5歲青少年的偏差要強于11.5歲青少年,也就造成了15.5歲青少年正確記憶下降。針對此現象,合理的解釋是,記憶由自動加工系統和控制加工系統組成[11]。由于15.5歲青少年的認知水平較11.5歲青少年的認知水平高,在記憶的加工中有更為嚴謹的控制過程,即對于學習詞的加工過程更嚴格(例如對學習詞的外部特征,如大小、顏色等做了詳細的編碼),而當測驗時,由于一些學習詞顏色的改變,使得原有編碼(如學習詞匯為紅色)不能匹配測驗詞所具有的新特性(如測驗詞匯為藍色),最終導致了該年齡段青少年學習詞再認率的降低。
4.2年齡特征及認知發展水平對青少年錯誤記憶的影響
兒童很少發生錯誤記憶,而老年人的錯誤記憶則比兒童多[12]。但錯誤記憶的趨勢并不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多。總體上看,錯誤記憶與真實記憶有著類似的發展軌跡,都是倒U型。本文的實驗結果也符合這一規律。對于錯誤記憶的這一規律,可以用錯誤記憶的模糊痕跡理論(FTT)解釋[13]。根據該理論的觀點,記憶存在字面痕跡和要點痕跡兩種記憶痕跡。字面痕跡指的是學過項目的物理信息、表面信息,是刺激的物理特征;而要點痕跡指的是刺激的概括性信息、抽象的意義等。對于錯誤記憶,字面表征和要點表征的作用相反,字面提取一方面可以增加所學項目的特異性細節和關鍵誘餌進行區分,一方面可以用認知策略抑制認知的熟悉性,而降低錯誤記憶,而要點提取卻通過增加所學項目的熟悉性而增加錯誤記憶[9]。錯誤記憶的年齡差異在于字面加工與要點加工伴隨年齡的增長而發生動態變化:由于年齡的增長,認知能力的提高,人們會更多的依賴于語義編碼,從而更容易對那些導致錯誤再認的語義信息進行編碼和提取,而較少編碼或提取那些引起正確再認的區分性細節信息,因此在這一階段內錯誤記憶會逐漸上升。而達到一定年齡段后,由于認知能力的下降,減少了對于容易導致錯誤再認的語義信息的編碼和提取,使得錯誤再認降低。在實驗一中,8.5歲青少年處于具體運算階段,認知水平低于處于形式運算階段的11.5歲和15.5歲青少年,也就是說11.5歲和15.5歲的青少年更容易對要點痕跡進行編碼,進而對于那些意義與學習詞具有高關聯的關鍵誘餌產生誘發,導致了更多的錯誤記憶。而為什么實驗一中15.5歲青少年的錯誤記憶比11.5歲青少年低,這是值得研究的。理論上,11.5歲青少年的認知水平不會高于15.5歲青少年,故11.5歲青少年產生的錯誤記憶也不會高于15.5歲青少年。對于這樣的結果,合理的解釋是:15.5歲青少年在記憶的提取階段有更高的監控水平,不容易對于具有高關聯的關鍵誘餌進行提取,因此使得錯誤記憶降低。■
參考文獻
[1] 楊治良. 漫談人類記憶的研究[J]. 心理科學, 2011(1):249-250.
[2] 楊治良, 王思睿, 唐菁華. 錯誤記憶的來源:編碼階段/保持階段[J]. 應用心理學, 2006, 12(2):99-106.
[3] 李宏英, 隋光遠. 錯誤記憶研究綜述[J]. 心理科學, 2003, 26(3):512-514.
[4] Loftus G R, Loftus E F. The influence of one memory retrieval on a subsequent memory retrieval[J]. Memory & Cognition, 1974, 2(3):467-471.
[5] Roediger H L, Mcdermott K B. Creating false memories: Remembering words not presented in list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 1995, 21(4):803-814.
[6] Deese J. On the prediction of occurrence of particular verbal intrusions in immediate recall[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59, 58(1):17.
[7] Huff M J, Bodner G E. When Does Memory Monitoring Succeed Versus Fail? Comparing Item-Specific and Relational Encoding in the DRM Paradigm[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 2013, 39(4):1246-1256.
[8] Inhelder B, Piaget J, Parsons A, et al. The growth of logical think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M]// The growth of logical think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al operational structures. Basic Books, 1958:412-414.
[9] 郝興昌. DRM范式下的兒童錯誤記憶研究[D]. 華東師范大學, 2013.
[10] Brainerd C J, Reyna V F. Fuzzy-Trace Theory and False Memory[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1(5):164-169.
[11] 郭秀艷, 萬璐璐, 郭曉蓉,等. 錯誤記憶的無意識機制初探[J]. 心理科學, 2005, 28(2):362-367.
[12] 黃一帆, 王大華, 肖紅蕊,等. DRM范式中錯誤記憶的年齡差異及其機制[J]. 心理發展與教育, 2014, 30(1):24-30.
[13] Brainerd C J, Reyna V F, Ceci S J. Developmental reversals in false memory: A review of data and theor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3):343-82.
作者簡介:陳實,1991年出生,江蘇南京人。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