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家鄉的金秋
李 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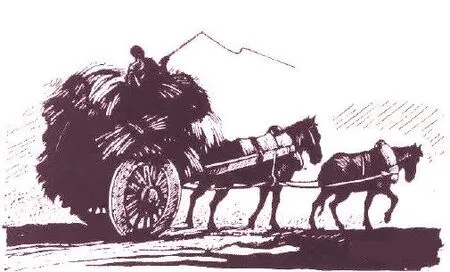
家鄉,我思念你的金秋。草原的秋末如同碩大無比的金氈鋪天蓋地,深深呼吸幾口沁人心脾的塞外清風,就像喝了香醇的美酒。由于從小就生長在呼倫貝爾大草原,對草原有說不出的愛戀。雖然身在草原,但每逢秋風瑟瑟草木搖曳之時,便難抑我對老家的思念之情。
老家坐落在豫中平原,是個古老的圩子,圩子的圍墻不知是哪朝哪代用黃土堆切起來的,墻上有垛口,墻下有塞門,墻外繞著一條時枯時豐的護城河,高大的洋槐樹又把圩子圍得密密實實。圩子外便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黃土地,這就是我祖輩世代生活的地方,我的老家,我的故鄉。
打我記事起,只回過三次老家,每次都感觸不同。記得第一次回老家是1971年,那是一個金秋時節,當火車駛入中原大地時,眼前是一片裸露的黃土地。火車途經商丘站時,站臺上一些搬運工仨倆一伙蹲在一起吃早飯,只見他們把黑乎乎的東西,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我感到好奇,父親說這是地瓜做的饃。說起地瓜,從小就有一種對地瓜的特殊情懷,從小在塞外草原,基本上見不到地瓜。地瓜甘甜可口,牽動著我肚子里的饞蟲,這次回老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吃地瓜,要盡情地吃,要敞開肚皮吃,要美美地吃個夠。此時看到用地瓜做的饃,不自主地咽起口水來,恨不得一步到家。
接站的是二伯父,他身著灰漬漬,看不出顏色的土布衣褲,腳下的布鞋張著“嘴”,從“嘴”里鉆出了幾個腳趾頭,頭上帶著一頂飛了邊的草帽。看到二伯父,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黑黑瘦瘦的臉盤與我的父親很相似,只是臉上布滿了皺紋,沒有一點光澤。當二伯父領著我們興致勃勃地穿過田間小路,走進了村子時,剛好是吃晚飯的時候。家鄉人吃飯都端著碗出來,蹲在路邊兒,幾個人圍在一起邊吃邊嘮,吃完了一碗回家盛上,返回來再繼續嘮。只見人們的碗里都是灰突突的片片,手里是在站臺上看到的那黑乎乎的饃。
父親從小就隨八路軍離開了家鄉,一走就是30多年。這次攜妻帶子探親,得到了生產隊里的特別照顧,借給了20斤麥種,眾親戚在一起吃了一頓撈面條,算是團聚飯。以后便是地瓜了,頭一次吃地瓜做的饃,甜絲絲的,吃幾頓后說什么也咽不下去了,接著還鬧開了胃腸炎。頓頓地瓜做的黑乎乎的饃和白水煮的地瓜干,以往對地瓜的美好憧憬一下子就破滅了。
生產隊長與父親是兒時的伙伴,在他與父親竊竊私語中,我隱約聽到,隊里好像多年沒分過一分錢了。鄉親們點燈用的油和吃的鹽,都是從雞屁股里摳出來的。雖然窮,但是在鄉親的言談話語中,感覺到他們仍然心中裝著一個踏踏實實的信念,那就是:跟著共產黨走,沒錯!
時隔八年,又是一個金色的秋天。帶著對家鄉苦澀的思念,我再次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車。
接站的還是二伯父。乍一看,我險些沒認出來。二伯父黑圓黑圓的臉上泛著紅光,再加上穿著半新的黃軍裝和腳下蹬著塑料涼鞋,顯得非常利落灑脫,還有幾分年輕。二伯父樂呵呵地讓我們上了騾車,他告訴我這騾子和車都是分的。上次回家時的鄉間小路,如今也是一條寬闊平坦的柏油路了。二伯甩起鞭子,騾子生風,蹄子“噠噠”,好似敲打著歡快的鼓點。遠看是與天際相連,一眼望不到邊的高粱和玉米地,近瞧是果實累累的棗樹,樹上的棗層層串串,每棵樹像撐開的紅色大傘。再看銀色的棉田,好似塞外的冬雪。田原上綠色、紅色、白色、黃色的各種植物波浪起伏,描繪出一幅色彩斑斕的豐收畫卷。
當落日的余暉把田野染成金光粼粼的時候,我們進了村。又是大碗,又是正逢鄉親們吃晚飯,我看到筷子挑起的竟是老面,手里拿的不是黑饃,而是白面烙饃,晚飯很豐盛。二伯告訴我們,土地承包到戶后,鄉親們再也不用吃地瓜度命了。如今莊稼人能過上好日子了!頓頓有糧食吃了!說到這時,二伯父的眼圈兒紅了,他說有些老人就是經常吃不到糧食,全身浮腫,過早地離世的。如今那令人心酸的歲月,再也不屬于這片古老的土地了。黨的富民政策向甘露一樣,滋潤著農民那久旱的心田。
斗轉星移,日月如梭,一晃又是八年。當草原的秋風撩起片片金色的樹葉在空中旋舞時,我又踏上了回鄉之路。這次來接我的是堂弟,他們每人騎著一臺用五彩塑料條打扮得花花綠綠的自行車。記得上次回家時,全村也沒有幾臺自行車。村子里的變化更是叫我眼里生輝。掩映在綠樹叢中的是棟棟精巧別致的二層小樓,幾個堂兄弟每人一棟,屋里的擺設也與城里不差毫幾。
在家鄉的日子里,我看到的是富足的生活,聽到的是農民發出來自心底的笑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方針政策使這里的人們煥發出巨大的活力。
時光荏苒,歲月飛逝,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40周年,這幾年我雖然沒有回過老家,但是通過和堂兄弟們的聯系,我得知家鄉那片古老的土地,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生機盎然。
今又秋風,大雁南飛,我寄于藍天中啾啾聲鳴的大雁,捎去我的相思,帶回對家鄉的更美好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