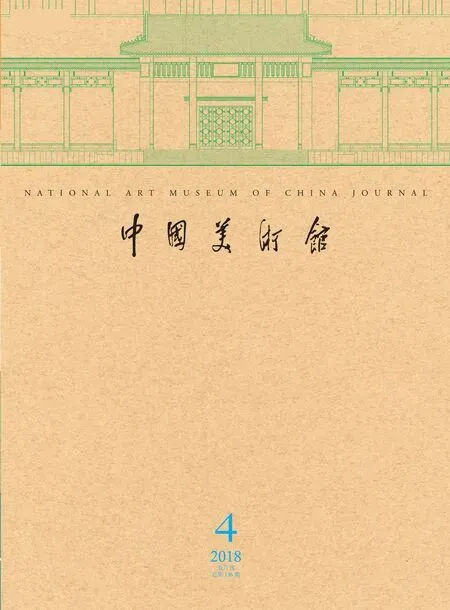淺析傳統印染類型與特征
—— 以中國美術館藏品為例
劉 瑩
傳統印染,是指運用靛青1等天然染料以手工方式在織物上染色形成單色或彩色花布的一種工藝。中國古代最早用染料在織物上施加花紋的方法是手繪,稱作“畫繢”,這種方法一直流傳在民間。漢代時出現了用木版捺印和手繪結合的方法,但這之后大量流行的是各種防染法。所謂防染法是指采用某種介質作為防染劑,使被防染劑覆蓋的部分不被染色,其他部分則染上色彩,從而形成花紋。唐代普遍流行的蠟纈、夾纈和絞纈三大染纈技藝便是具有代表性的防染印花方法,后來又在夾纈的基礎上出現了漏版刮漿的印
花工藝。近現代由于機器印花的發明和普及,傳統手工印染逐漸被取代,但是在我國的民間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卻被保留了下來。至今我們在貴州苗鄉、云南大理、湖南湘西、江蘇南通、浙江桐鄉、山東、陜西、新疆等地,還延續著蠟染、扎染、藍夾纈、藍印花布及彩印花布等傳統印染工藝及品類,它們分別從古代的三大染纈技藝發展而來并延續至今。中國美術館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大量征集民間美術作品,現有印染藏品七百余件,基本包含了上述品類,結合實物和文獻,可一覽傳統印染的各個類型及特點。
一、蠟染
蠟染,即古代所稱的“蠟纈”,是利用蠟的隔水性將其作為防染劑的一種印染工藝。史料所描述的“繪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與現代蠟染工藝幾無二致,即用蠟汁在布上繪出花紋,將布染色漂洗后,放入水中煮沸,蠟熔化后出現白色花紋。蠟染的起源一般認定在漢代甚至更早,唐朝時蠟纈已成為盛行的裝飾紡織品。唐開元年間蠟染曾用于軍服和宮廷貴族服飾以及室內裝飾屏風等,現存故宮博物院的三色蠟染實物以及藏于日本正倉院的蠟纈屏風都是唐代遺物。蠟染品還沿著“絲綢之路”遠銷到海外。宋代以后,隨著中原經濟和刺繡、織錦、緙絲等織繡工藝的快速發展,蠟染技藝在中原地區日趨衰落并相繼失傳。然而在我國的西南地區,卻隨著苗族的大遷徙以及與布依族的匯合,帶來了原居住地的蠟染工藝,因為處地偏遠閉塞、經濟發展遲緩,蠟染技藝通過當地人們的口口相傳世代流傳下來。直至今天,云貴地區的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民族,他們的服飾以及被蓋、背扇、包帕等日常用品都喜歡采用蠟染制品。這些地區由于民族多且支系復雜,生活習俗、民族傳說及文化認知均有所差異,因此蠟染的風格也迥然不同,其中以貴州分布最廣,幾乎遍及全省,類型也最為多樣,僅其一地的蠟染便可分為丹寨型、安順型、織金型、榕江型、黃平型、黔西型、納雍型等若干不同的類型。中國美術館所藏的印染作品中,也以貴州苗族蠟染最為全面,幾大類型均有涉及,風格典型。
(一)丹寨型
丹寨型蠟染是指分布于丹寨縣、三都縣一帶的苗族蠟染,是貴州最有代表性的蠟染之一,其紋樣題材多樣,主要為花、鳥、魚、石榴等動植物紋樣,經過提煉以流暢律動的線條加以表現,各種造型生動、夸張,具有很強的裝飾性,特別是鳥紋的變化最為豐富,寫實和抽象兼具,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圖1)。丹寨蠟染還有一種類型是結構嚴謹的幾何紋,這類紋樣基本依循傳統圖案,當地婦女徒手用蠟刀畫出的圓弧、直線竟好似尺寸制作,極為整齊規范。另外,在當地的“白領苗”女性盛裝上,有一種常見的渦紋,苗語稱為“窩妥”。千百年來,當地婦女一直虔誠地將這種渦紋描繪在衣服的領背和肩袖處,至今仍未改變。對于渦紋的來歷,一說為了紀念祖先長途遷徙歷經險灘惡浪留下的旋渦印記;一說是殺牛祭祖時記錄牛頭上的毛旋,因其是祖先的象征;又有說是祭祖時銅鼓上的旋紋(圖2、圖3)。

圖1 丹寨苗族花卉鳥獸紋蠟染褥面 82cm×156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2 丹寨苗族渦紋蠟染衣肩袖片 24cm×57cm×2 中國美術館藏

圖3 丹寨苗族渦紋蠟染女盛裝76cm×134cm中國美術館藏
(二)安順型
安順位于貴州省中西部,安順型民間蠟染主要指流行于安順地區的苗族彩色蠟染。安順苗族蠟染主要以自然紋樣及幾何紋樣為主,其特點是在藍、白為基調的蠟染上,用楊梅汁和黃梔子水加繪紅、黃兩種顏色,形成貴州少數民族蠟染中并不多見的色彩濃郁的蠟染類型,風格十分鮮明。在安順傳統蠟染中以背扇2最為精美,中國美術館收藏的一件安順彩色蠟染背扇心(圖4),底色大面積染成桔紅色,上面有馬蹄花紋,在中心圖案的外輪廓線上繪制的一排密集均勻的小點子,俗稱“點子花”,也是安順傳統蠟染的一個特點。

圖4 安順苗族馬蹄花紋彩色蠟染背扇心49cm×56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5 黃平革家蝶鳥太陽紋蠟染包片73cm×73cm 中國美術館藏
(三)黃平型
黃平型蠟染是指分布于黃平一帶革家人3的蠟染。據考,革家先祖屬古僚族的一個支系,至今仍保留著諸如“椎髻斑衣”的古僚族特征。革家人認為自己是羿的后人,信仰射日傳說,自古崇拜太陽,因此在革家人的蠟染圖案中主題紋樣多是太陽或太陽的變形,在構圖上講求對稱,常將太陽、蝴蝶、石榴、蝙蝠、鳥、蛙、銅鼓、花草、藤蔓等自然紋樣和螺旋紋、三角紋、云紋、回字紋等幾何紋樣相互穿插套疊,形成花連花、大花套小花、花中填花的精巧布局,豐富而有序(圖5)。繪制時常在圖形外沿繪一圈須毛狀的小線條,排列極為細密,其長短、粗細幾無二致,顯示出革家婦女們高超的畫蠟技巧,形成革家蠟染獨特的美感。
(四)榕江型
榕江地處黔東南南部,榕江型蠟染主要指分布于平永、興華、都江一帶的苗族蠟染,其蠟染制品主要用于祭鼓長幡、頭帕、服飾等,紋樣較為具象,主題多為鳥、龍、魚、蛙和銅鼓等紋樣,偶爾也以節日場景、苗族古歌或傳說典故為題材創作。榕江蠟染中最有特色的是“鼓藏”長幡。當地每隔十三年舉辦一次盛大的“鼓藏節4”,屆時人們用竹竿挑著高達五六米的蠟染招魂長幡,莊重而神圣地恭迎祖宗圣靈,渲染出一派莊嚴肅穆的神秘氣氛。鼓藏幡藍底白花,紋樣以苗龍為主,龍形似蛇,或舒展盤旋,或爬行蜿蜒,或游水嬉戲,與魚蝦、蛙、蝶、花鳥等組合成變化萬千的圖案,在紋樣邊緣常裝飾有一圈短弧線,似百足、似尖刺,整體效果震人心魄(圖6)。
(五)織金型

圖6 榕江苗族鳥龍紋蠟染祭鼓幡 (局部)82cm×320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7 織金苗族雀鳥紋蠟染背扇片 64cm×56cm 中國美術館藏
織金型蠟染主要分布于貴州西部的織金、納雍、普定等地,風格以細膩著稱,圖案小而工整,是貴州省目前所能見到的最精細的一種蠟染類型,細分之下這幾個地區的蠟染風格又有所不同。織金縣主要蠟染產地官寨鄉小妥倮村,當地的苗族因婦女梳歪髻,上插一柄彎月形花漆木梳而得名歪梳苗。歪梳苗的女性服飾中,衣、裙的多個部位大面積使用蠟染裝飾,紋飾以抽象的幾何紋、螺旋紋和卷草紋為主,極其精湛細密。織金蠟染有一種技法叫“點刺”,即在蠟染的醒目、關鍵部位施以刺繡,用彩色絲線繡出星狀小花點綴其間,多用紅黃色搭配,在大面積的藍、白紋飾之中綴以星點色彩,整幅作品既協調統一,又有局部的色彩對比變化,使蠟染別具情趣,生動活潑,成為其獨特亮點(圖7)。納雍的苗族蠟染多用于衣擺、衣袖、裙、背扇等,既有單一的藍白蠟染,也有色彩豐富的彩色蠟染,其圖案飽滿對稱,善于運用曲線,線條流暢密集,各種紋樣之間巧妙穿插融合,看似難分彼此,細看卻絲毫不亂,風格頗為獨特(圖8)。
(七)黔西型

圖8 納雍苗族蝶紋彩色蠟染背扇片 59cm×60cm 中國美術館藏
黔西型蠟染主要指位于畢節地區的黔西縣及其附近的林泉、沙窩等地苗族蠟染,因地域上與織金、納雍相鄰,蠟染風格相互有所影響,都屬于精細一派。黔西蠟染一般要染兩次,第一次點蠟浸染后形成淺藍色花紋,晾干后用蠟封住一部分花紋再次浸染,形成深藍色,因此畫面呈現白、淺藍、深藍等多種色調,還有多次封染產生的冰裂紋,非常富有層次感。中國美術館收藏了三十余件黔西蠟染背扇和袖片,紋飾以花草植物紋居多,圖案規整有序,所有花紋層層分明一絲不茍,十分精細(圖9)。除藍白系蠟染外,黔西還有以紅、黃、紫等顏色作輔助的彩色系蠟染,淡淡的色彩有規律地填充于花紋局部,呈現出更加豐富的畫面效果(圖10)。

圖9 黔西苗族水草紋蠟染背扇片 54cm×52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10 黔西苗族杏葉構成紋蠟染袖口片 23cm×34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11 惠水布依族花鳥壽字紋楓香染背扇(局部)69cm×66cm 中國美術館
(八)楓香染
除去以上幾種主要蠟染類型,在貴州地區還有一種與蠟染異曲同工的印染方法——楓香染,其印染原理和制作過程與蠟染相似,均用藍靛浸染,只是用作防染劑的不是蜂蠟或石蠟,而是以當地特有的楓香樹分泌的油脂按一定比例混合牛油調配而成。蠟染雖流布于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而楓香染卻集中在較小的范圍,鮮為人知,現在主要在惠水地區的布依族和麻江縣的繞家(瑤族的一個分支)當中流傳。這兩個產地的區別在于,繞家人通常使用竹制小刀蘸著油脂繪制圖案,而布依族則習慣直接使用毛筆蘸楓香油進行繪畫。楓香染一直以藍、白為主,沒有其他色彩變化,通過兩次封染,還可以得出深淺兩種藍色。傳統楓香染圖案古樸、構圖明朗,以花草、魚鳥等自然紋樣為主,在結構布局上常以連續紋樣和適合紋樣組成。中國美術館藏有幾件馬正榮先生捐贈的20世紀60年代的楓香染背扇,紋飾中有漢族常用的壽字紋和回紋,花鳥形象也較為具象,與中原地區紋樣較為接近,顯示出民族間文化的融合(圖11)。惠水布依族的楓香染由于使用毛筆作為繪制工具,這使得線條非常流暢舒展,并且有筆觸上的變化,具有較強的繪畫感。
二、扎染
扎染,古稱“絞纈”,俗稱“雜花布”,是一種古老的結扎染色工藝。其原理是利用麻、絲、棉繩線在平整的布料上進行有規律的結扎絞纏,使布料皺攏,將其浸入染缸,扎結處不易浸色,而未捆扎處則很容易著色,拆去線結使之呈現出白色花紋,并形成自然的色暈效果。扎染在我國的起源很早,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早在東晉,此種工藝已在民間流傳,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鹿胎紫纈”和“魚子纈”圖案。隋唐時期,絞纈更是風靡一時,史料記載的絞纈名稱就有“大撮暈纈”“瑪瑙纈”“方勝纈”“團窠纈”等。到了宋代,絞纈工藝進一步往精細方向發展,頗為費時費工,北宋政府遂下令禁止和限制染纈品在民間的流通和使用。元代以后,隨著戰亂的頻繁,明清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及歐洲化學染料的輸入,扎染在沿海、中原一帶日趨衰落,一些技藝也逐漸失傳,但卻在云南、四川、貴州、湖南等一些偏遠地區保存沿用下來,并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明清時期,洱海白族地區的染織技藝已到達很高的水平,出現了染布行會,明朝洱海衛紅布、清代喜洲布和大理布均是名噪一時的暢銷產品,時至今日大理白族地區仍是全國著名的“扎染之鄉”(圖12)。四川作為著名的織染產地,曾出產過歷史上有名的貢品“蜀纈”,自貢為主要產地,自20世紀70年代起,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自貢扎染取得了新的突破,將傳統技藝發揚光大。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美術館的扎染收藏非常之少,僅有數件創作型扎染,缺少傳統扎染作品,故難以例證。

圖12 云南大理周城現代白族扎染
三、夾纈
夾纈是一種極為古老的印染技術,其利用雕版將織物夾在中間進行染色形成紋樣效果。史書記載,隋煬帝曾令工匠們印染五彩夾纈花羅裙,賞賜給宮女和百官妻女。唐朝時期夾纈藝術已非常盛行,多印在絲、絹、錦上,色彩斑斕,專用于宮廷,民間禁止使用。到了宋代,朝廷指定彩色夾纈為皇室專用,不準流通,民間只能使用單色夾纈,并且多印在土布上。進入元明后,由于制作工藝復雜,夾纈逐漸被紙版漏花等其他印染方式所替代,夾纈的使用漸趨稀少,到明清時已罕見,至近代已基本絕跡。直至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在浙江南部溫州地區的蒼南、樂清、瑞安等地又發現了流傳于民間的單色夾纈(藍夾纈),并逐漸恢復了此工藝。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溫州,夾纈布被用來縫制成被面,作為閨女出嫁時娘家人的必備之物,與生活密不可分。夾纈被在當地又有“方夾被”“雙紗被”“敲花被”“大花被”等稱謂,或憑圖案稱之為“百子被”“龍鳳被”“狀元被”等。夾纈的制作工藝分作雕版和印染兩大步驟。雕花版上的紋樣必須具有一定的深度,染色時染料才能夠滲入其中,并且線條要求均勻規整。一床花被所用的一套雕花版通常為17塊,印染時需將17塊花版依次分別固定在分段折疊好的坯布上,再浸入染缸染色,最后印出16個紋樣不同但左右對稱的圖案,整個過程極為費時費工(圖13)。

圖13 完整的一套夾纈花板

圖14 夾纈狀元被 214cm×205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15 夾纈工農兵圖案被面(局部)中國美術館藏
夾纈被面的傳統圖案多為百子圖、狀元圖及戲曲劇目中的才子佳人等形象,作為新婚女子的陪嫁品,寓意夫妻好合、祈福求子(圖14)。此外,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浙南的夾纈工匠順應“破舊立新”的思潮,雕刻出以“工農兵”為主角的一系列作品,內容多是工農兵學習、生活和勞作的場景,如大煉鋼鐵、栽花植樹、插秧拾穗等,極富時代特色(圖15)。
四、藍印花布
藍印花布是宋代“藥斑布”的繼承和發展。藥斑布又名“澆花布”,是一種堿劑防染法,將草木灰或石灰等堿性較強的物質抹于坯布上,染青后去灰,則青白相間。以后這種防染技術不斷發展,改用石灰和豆粉調制成防染漿,采用“漏版刮漿”的工藝,將這種防染漿通過漏版刮在布上,然后浸入染缸反復染色,晾干后刮去坯布上的灰漿形成藍地白花的花布。漏花用的紙版為多層桑皮紙黏合而成,刻出鏤空花紋后,在花版兩面涂刷桐油以增加牢度并防止透水。因其工藝相對簡單,逐漸替代了夾纈制品,江蘇是其主要產地,明清時期印染業達到鼎盛,藍印花布由江南遍及全國城鄉,有些地區甚至形成了“織機遍地,染坊連街”的盛景。現在的藍印花布產地主要以江蘇南通、浙江桐鄉為中心,輻射至周邊區域,湖南湘西鳳凰古城、山東沂蒙地區也有部分流傳。
藍印花布主要流傳于漢族群眾當中,用于制作床單、被面、門簾、頭帕、包袱、圍兜等生活日用品,其圖案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專門制作匹料的,為比較嚴格的四方連續,紙版的花紋四邊可接;另一類是適用專項用途的,為整體圖案。藍印花布的紋樣內容非常豐富,且具有民間傳統的吉祥寓意,是漢族文化的體現。中國美術館收藏有江浙地區的上海金山、蘇州、啟東、南通以及山東臨沂等幾大主要產地的藍印花布,相較而言,江南一帶的藍印花布圖案較為飽滿(圖16);魯西南沂蒙山區的藍印花布圖案造型更加稚拙簡練,整體風格更加質樸,富有鄉土氣息(圖17)。
五、彩印花布
彩印花布是在藍色之外還加有其他色彩圖案的印花布,若按照傳統手工印染工藝來區分,彩印花布又有“漏版刷花”和“木版捺印”兩種類型,兩者流布地域和藝術效果有著較大區別。

圖16 江蘇啟東麒麟送子紋藍印花布被面217cm×131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17 山東臨沂富貴平安紋藍印花布門簾188cm×93cm 中國美術館藏
(一)漏版刷花
此種彩印花布工藝曾在山東、陜西、山西等黃河流域地區十分普遍,主要用作大小包袱皮,俗稱“花袱子”。其制作方法類同于藍印花布,同樣采用漏版方式,但無需染缸浸染,而是用大紅、桃紅、姜黃、翠綠、紫色等染料在鏤空的花版上直接刷色,一色一版,不同顏色需要鏤刻不同的花版,通過多個版的套色印刷,形成色彩豐富的花樣。在刻版時,往往分刻中心版、角隅版和邊飾版,以根據需要靈活組合運用。在山東等地的風俗中,結婚陪嫁物必須用彩印大小包袱包裹或包蓋,送到婆家后,這種彩印包袱皮就成為結婚的信物和紀念品,被新婚夫婦長期珍藏。中國美術館共收藏了近50件彩印花布,大多出自山東,均為1984年由山東美術館代為征集,其中以嘉祥、鄆城、臨沂、博興四地的作品較為精彩,各地風格不盡相同。其中一件鄆城縣彩印包袱皮(圖18),邊花和主紋樣分開印制,紫色花邊為框,中心以單一“麒麟送子”紋樣縱橫排列刷印九次填滿其間,看似繁縟錯節,細觀人物眉眼精細,八寶器物穿插于四周,構成完整的單獨圖案。總體來看,山東彩印花布的特點是紋樣固定,重復排列組合,構圖飽滿充盈,色調明快,飽和度高。因色塊較多,刷印時每版中都有統一的標志,一般在每版相距的一定位置上鑿三四個圓眼,以便能夠快速準確對版。

圖18 山東鄆城麒麟送子紋彩印花布包袱皮158cm×162cm 中國美術館藏
(二)模戳彩印花布
在傳統手工印染工藝中,還有一種木模印花的方式,即利用梨木或核桃木上雕刻出凹凸分明的圖案,然后以此模直接著色在坯布上印出紋樣,其形式如同蓋“印戳”,故稱作“模戳印花布”。此工藝曾盛行于歐洲,在我國主要為新疆維吾爾族所使用并形成傳統,流布于喀什、和田和阿克蘇等地。木模的大小規格各異,印制時可單獨使用,形成獨立花紋,也可組合使用,形成整體圖案,各種木模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可產生豐富多彩的紋樣效果。另有一種滾筒狀印花木棒,用來滾印花紋,其紋樣變化也極為豐富,可印制四方連續紋樣。維吾爾族印花布用途廣泛,通常可做衣里、墻圍、壁掛、窗簾、桌單、餐巾、褥墊等,用以裝飾美化生活,與當地的建筑風格、居室環境等風格一致,相得益彰。其紋樣和風格與漢族有明顯的不同,與當地的宗教文化、建筑裝飾及其他手工藝品有著很大的聯系,可分為幾何紋、植物紋、文字紋、建筑紋、器皿紋等幾大類,受伊斯蘭教不得表現有靈魂物體的教規約束,維族印花布中不采用人物和動物形象。

圖19 新疆喀什維吾爾族八達暈紋彩印花布90cm×262cm 中國美術館藏
維吾爾族的印花布按色彩的不同可分為雙色印花和多色印花兩種,無論哪種,通常都運用黑色的裝飾線條勾勒圖案,再加以明快的色彩,形成強烈的對比,從而呈現出既色彩絢麗又不失深沉典雅,并略帶神秘的藝術特征。因為黑色在維吾爾族的色彩審美文化中是吉祥色,具有多重的意義,象征著美麗和高雅。中國美術館收藏有5件新疆模戳印花布,雖然數量不多,但作品紋樣細密精致,印染水平較高。其中一件模戳彩印花布(圖19),采用典型的黑、紅雙色印染,紅色代表著生命與力量,也是維吾爾族人民的崇拜色,作品四周為多層帶狀花紋,中心是八達暈紋,也稱八達韻、八苔暈,是一種中心呈八面形,向八面延伸連接成網狀的四方連續,富于變化,風格繁復華美,因由八面組成,故稱“斗八”,表示八面相通之義。墻圍是維吾爾族模戳印花布中用途最廣的一種,可用于居室裝飾和隔離墻面使用。墻圍的構圖主要以帶有宗教色彩的龕形結構為主,紋飾內容多為巴旦木紋、水壺紋等維吾爾族特有的紋樣(圖20)。
以上所列種種僅限于中國美術館所藏,受篇幅所限也僅是述其大概。在我國的傳統印染工藝中,還有一些產地和品類因館藏作品不足未有過多涉及,如山東的“撮花布”5“豆花布”6等,以及苗族以外其他少數民族的染纈品類。民間傳統染纈工藝歷史源遠流長,作為農耕文化的產物曾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遺留下來古代印染品其技藝之精湛,令后人嘆為觀止并引以為傲,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手工印染工藝曾一度衰落乃至消亡。幸而,近十幾年隨著國家非遺保護政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傳統技藝被重新發掘和重視。貴州蠟染、云南白族扎染、四川自貢扎染、南通藍印花布、山東彩印花布、新疆模戳印花布等均已被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技藝得到保護和傳承。從中國美術館現有的印染藏品來看,以貴州苗族蠟染和江蘇、山東兩地的印花布數量最多也最全面,其他類型雖有涉及但數量較少或不夠典型,今后在收藏方向上或可重點關注。

圖20 新疆喀什維吾爾族龕形花卉紋彩印花布墻圍 90cm×262cm 中國美術館藏
注釋
1.也叫“靛藍”,利用馬藍、蓼藍等藍草植物葉子發酵制成的一種有機深藍色染料。
2.背扇俗稱背兒帶,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婦女養育孩子不可缺少的重要生活用品。中間方形部位用來包裹住嬰兒,稱為“背扇心”;兩邊長長的條帶系于胸前,稱為“背扇手”。
3.革家自稱“哥摩”,是我國目前尚未認定的一支具有悠久歷史的少數民族族群,主要分布于貴州的黃平、凱里、麻江、關嶺等地。
4.又叫“吃牯臟”“祭鼓節”等,是苗族人民古老而盛大的祭祖節慶,其重要內容是殺牲祭祖。
5.山東臨清一帶流行的扎染花布,因紋樣形似雙翅展開的飛蛾,又叫“蛾子花布”。
6.又叫“包豆子花布”,是山東民間扎染花布中包扎豆類果實再行投染的一種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