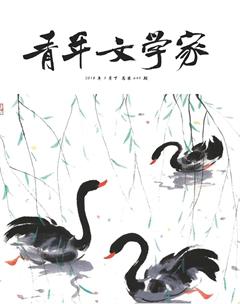個體偶在命運長存
摘 要:《永別了,武器》自1929年出版以來便受到一致好評,時至今日,國內外的研究成果蔚然大觀,囊括作品的人物、思想、藝術特色等各個方面。本文無意于重蹈前人之功,筆者擬用印象式的體驗之刃開鑿未露的冰山,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發現個體偶在(勝利、愛情)與長存的命運(死亡、孤獨)的張力,以及在這一過程中亨利從履行職責到遠離戰爭,從佳人相伴到雨中獨行,最終完成了對人生虛無的體認。
關鍵詞:海明威;永別了,武器;虛無;孤獨;命運
作者簡介:吳若瑤(1995-),女,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英美文學方向)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9-0-02
不同于一般的反戰小說,在《永別了,武器》這本書中,除了強烈的反戰傾向之外,更是通過主人公戰爭觀和愛情觀的嬗變實現了對人生意義的頓悟,一切皆是虛無。偶在的是贏得勝利的戰爭,美好的愛情,長存的卻是死亡,孤獨。相較于命運之力,自然界,個體的存在自是偶在,而這種偶在又孕于必然之中,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不難發現亨利最終掉入虛無的深淵實是命運之舉。
一.勝敗偶然死亡必在
小說開篇似乎就籠罩著陰沉幻滅的氛圍“部隊打從房子邊上走上大路,激起塵土……我們看著部隊在路上開著走,塵土飛揚,樹葉給微風吹得往下紛紛掉墜,士兵們開過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蕩蕩,只剩下一片落葉。”敘述者將讀者置于眺望和俯瞰的角度,一開始就暗示了一切終將歸于塵土,部隊似乎是死亡之軍,紛紛掉墜的樹葉何嘗不是滅亡的前音,樹猶如此!雨作為小說中間歇性的伴奏從這里也開始了,雨后總是清新,而小說中的雨似乎無法將塵埃滌蕩干凈。
小說中從未正面描寫激烈的交戰場面,代之以簡要的戰況說明,偶爾在大規模進攻的空當,兵士們開著無關痛癢的玩笑,似乎與前線隔了一層保護膜,而炮彈的聲響又不斷地將他們拉回殘酷的戰場。在亨利受傷療養期間,報紙上又刊載了許多打勝仗的消息,但是,與零星的勝利相比,更多的是不期而至的失利和撤退,從軍事角度來看,勝敗乃是常事,而不管勝利與否,死亡都是一個無法規避的話題。小說在第一章末尾便不無諷刺地談到“冬季一開始,雨便下個不停,而霍亂也跟著來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結果部隊里只死了七千人”,[1] “區區”七千人與戰爭帶來的傷亡人數自然是不值一提,戰爭可怖,微觀中的人物在這場戰爭中命運不自知,當然很多人走向了毀滅。凱瑟琳的舊情人在索姆戰役中犧牲,帕西尼在吃干酪的時候意外被迫擊炮擊中呼吸漸無,而亨利也在這次襲擊中受到重傷。
戰爭包含著諸多的危險和不確定性,戰火與硝煙無疑是生命無常的最好注腳,而小說的諷刺點在于有些人并非因單純的戰爭因素而死。雷納蒂是一位年輕的意大利外科醫生卻在妓營中染上梅毒而死。再如意軍大規模撤退時,亨利一行人與部隊失散,走小路想要穿過田野的當,同行的艾莫頸部中槍,經過亨利的分析,開槍的是意大利人而不太可能是德國人,艾莫沒有死于敵軍之手卻遭到了所屬軍的槍擊,這不啻為一種嘲諷。亨利僥幸躲過了敵軍的注視,卻又被憲兵逮捕,被當作披著意軍的德國間諜,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亨利沒有掙脫,被槍斃是無疑的了。而小說至此,對戰爭荒誕性的描寫也到達了最強音。正如亨利所感受到的“所謂光榮的事,并沒有什么光榮……抽象的名詞,像光榮、榮譽、勇敢或神圣,倘若跟具體的名稱——例如村莊的名稱、路的號數、河名、部隊的番號和重大日期等等——放在一起,就簡直令人厭惡”。[2]其實我們從軍事角度來看,亨利實際上就是一個逃兵而已,這樣一個懦弱者的角色何以值得大書特書呢?顯然小說首先否定的是戰爭本身的合理性,既然戰爭并沒有所謂的神圣性,背離戰爭這一行為便是無可厚非的。
生命自是無常,不管是死于戰爭的流彈還是死于意外的梅毒,難產這些非戰爭因素,個體的存在都是一種偶然,而戰爭似乎是一種催化劑,加速了亨利生存觀的改變。人生本身何不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人從降生起始就身不由己地拋入這樣的命運之中,“你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你連學習的時間都沒有。他們把你扔進棒球場去,告訴你一些規則,人家乘你一不在壘上就抓住你,即刻殺死你。或者無緣無故地殺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樣,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納蒂那樣。但是到末了總歸會殺死你的。這一點是絕對靠得住的。你等著吧,他們遲早也會殺死你的。”[3]面對早已注定的結局,亨利試圖用愛情來拯救他無望的人生,然而凱瑟琳的死亡讓亨利最后的幻想也破滅了。
二.愛人不再孤獨恒常
亨利一開始對待這份感情的時候是以一種游戲的心態,兩人的相遇結識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像其他將士一樣,談論女人和酒成為他們日常的消遣,亨利大多時候是將凱瑟琳作為填補內心寂寞空虛的存在,去醫院看望凱瑟琳是無聊的戰爭中難得的樂趣。一直到亨利受傷之后,在米蘭的一家醫院與凱瑟琳再次相遇,亨利似乎“真正”愛上了凱瑟琳,而吊詭的正是亨利苦心離開的戰爭反而促成了他與凱瑟琳的愛情。因而在筆者看來,這種愛基于受過戰爭洗禮后急于尋求安慰才生發,帶有過強的目的性而顯得不那么純粹。
愛情本身便是一種偶在,于千萬人之中,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兩人陷入愛河。其中的偶然性不明自顯,雖然亨利與凱瑟琳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戰爭的因素,但也正是這種動蕩給這份愛情增添了稀貴的籌碼,筆者認為亨利與凱瑟琳的愛情雖然沒有足夠動人的真摯,但兩人的互持畢竟帶給人一種溫情,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孤島,面對慘淡的戰況,可悲的現實,共同面對當然要比獨自承擔幸福得多,兩人試圖牢牢綁在一起而免于被世界征服,在兩人看來,二人搭建的堡壘固然單薄了些,但只要二人合為一體,沒有隔膜,便沒有什么可以把他們摧毀。讀者甚至都要相信在紛雜的戰亂中,始終還有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愛人的懷抱,而小說在這里急轉直下,凱瑟利竟死于難產。這樣的結局不免讓人失望,而仔細翻閱文本,凱瑟琳的死又是必然的。
小說中提到亨利總是有種不祥的預感,到了臨產期間,生產的不順利再次讓亨利產生可怕的念頭“倘若她死去呢”,不料竟一語成讖,小說結尾再次用海明威式的克制筆法描寫奔涌在冰山下的苦痛與無奈,最大的痛苦是自己又要不得不一人面對接下來的人生,凱瑟琳的死看似偶然卻是命運的必然,而凱瑟琳的死亡對于亨利來說與其說是一種巨大的痛苦,不如說是一種解脫,這種解脫是來自災難終于降臨而因為臆測帶來的惶惑終于得以釋放。
我們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就算是遠離了戰爭,與凱瑟琳在瑞士過著表面祥和的生活,亨利卻仍然填補不了心靈上的空洞,亨利一直盼著找點事情做做,哪怕只是留一下胡子,嘴上說著“我喜歡這種生活”而夜里又會突然醒來,東想西想。兩人的愛情固然甜蜜,甜蜜到讓亨利忘記戰爭的荒誕無趣,卻無法抵擋住虛無,比起在硝煙的戰場上死里逃生,無所事事只剩愛情的生命之“輕”似乎更讓亨利難以承受。人像書中描寫的木柴上的螞蟻一般,起先是向著中間著火的地方爬后來向兩邊爬,直到身體燒得又焦又扁,不知道最后爬到什么地方去。
小結:
戰爭的洗禮加上愛人的離去最終促使了亨利完成了對人生虛無的體認,如尼采所言,在亨利身上實現了“最高價值的自行廢除”,亨利與凱瑟琳出場就是宗教信仰缺失,而亨利在戰爭中一步步發現哪有什么神圣,榮譽,所謂的終極目的,終極意義都被戰爭攪得蕩然無存,唯有酒色是生命的趣味,所有個體偶在的呢喃都抵不過命運微小的一擊。“一旦有了這一‘發現,虛無主義就降臨了。因為失去了與終極的真實、目的和整體關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真實、意義與價值都會蕩然無存。”[4]亨利在偶在與必在之間不斷認識自身,打量他所處的世界。而筆者發現,個體的偶在,不論是勝敗之別,還是愛情的降臨又都是一種必然,似有命運之手操控著一切,命運不斷地創生著偶在,任何偶在事物又都是命運必在的例證。
在小說中戰爭本身是荒誕的鬧劇,愛情也絲毫沒有填補虛無的空位,萬事最終歸于一人承受,孤獨必然,命運長存。像亨利一樣我們始終要關注和思考的是如何為個體的偶在立法,為精神世界建立穩固的大地,這或許是小說給我們的最大警示。
注釋:
[1]海明威:永別了,武器[M].林疑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4頁。
[2]海明威:永別了,武器[M].林疑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192頁。
[3]海明威:永別了,武器[M].林疑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337頁。
[4]余虹:虛無主義——我們的深淵與命運[J].學術月刊,2006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