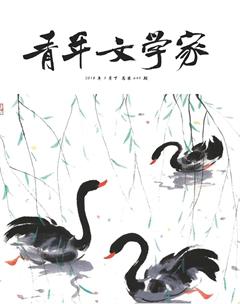小說敘事中的博弈關系
摘 要:格非的《小說敘事研究》是一本小說敘事的研究著作,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小說敘事的基本理論,從小說與現實、作者與讀者、故事、結構、語言以及小說的未來等六個方面加以論述,第二部分則以一批文學大家的作品為例,對小說的敘事方式做了具體的分析。如何處理小說,小說如何敘事,本就是作者與作者,與讀者,與世界的一個關系的制衡,本文將在格非對小說敘事手法和策略的分析之上,具體分析作者、讀者、世界在敘事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關系。
關鍵詞:作者;讀者;世界;博弈
作者簡介:王婷(1992-),女,漢族,四川達州人武漢大學文學院碩士,專業: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9-0-02
一、作者與讀者的博弈
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諸種關系一直受到批評家、文體家、小說修辭家的關注,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該如何看待與讀者的關系,如何處理與讀者的關系,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是小說家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格非在《小說敘事研究》專門用了一章“作者與讀者”來論述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與此同時其他各章節也有涉及。
近年來,隨著西方后現代主義以及不斷在中國擴大影響的接受美學觀念的發展,作者與讀者的關系問題被再次提起,并引起了學術界的更大關注。格非在書中提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處于“期待與滿足”的心理,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會將自己躋身于故事的創造之中,會在閱讀過程中通過自己的揣摩、疑問、推理等方法介入,這樣就導致了“讀者與作者之間張力空隙的產生”[1]。一般說來,作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由書寫自己的小說,但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也并非完全處于被支配的地位,他可以隨時選擇結束閱讀,讀者與作者的博弈關系就此產生。
格非在書中將作者與讀者的關系定義為“共謀”關系,“共謀”并非說明兩者利益一致,在我看來,這恰恰是雙方在進行權力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讀者永遠是貪婪的,作者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方法永久滿足讀者,作者也不必一味地縱容讀者。“高明的作家懂得節制,同樣亦不會過分依賴懸念、戲劇性的故事轉折和種種敘事的技巧。”[2]在處理與讀者關系時,高明的作家一般會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利用各種手段盡可能地推延故事高潮的來臨,另一種是故意違拗讀者的期待,這種大膽的做法有時會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結果。
高明的作家愉悅讀者,優秀的作家創造讀者。格非在書中提到,喜歡閱讀通俗淺顯故事的讀者雖然依舊大量存在,但是讀者層中的分類也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潮流,因此,作家應當了解讀者“期待”的各個層次。不管作家是否認同,讀者的某些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小說的后續發展。作家寫作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與讀者進行交流,但是,作家在進行創作這個過程中并不會與真正的讀者面對面交流,格非在此提到了“虛設的讀者”這一概念。不同類型的作者虛設的作者對象也會不同,暢銷書的作者虛設讀者必定是普通讀者中的某一位,而現代主義作家則將大眾讀者排斥在外,只為少數“精英”寫作。
在這場作者與讀者的博弈中,我們當然不能說雙方力量旗鼓相當,因為雙方交流過程中,作家一直在進行或明顯或隱藏的介入和誘導。早期小說家主要以直接介入敘事的方法在作品中引導作者,引入自己的價值取向,比如笛福的作品,比如中國的《三國演義》等。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將自己“復興漢室”的立場和觀念介入其中,對筆下人物傾注了強烈的愛憎,這種將作者的價值取向精準傳遞給讀者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讀者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使閱讀成為一個被動地接受過程,這種直接的介入是格非強烈反對的,認為對敘事構成了損害。 格非在書中多次提到了《紅樓夢》,可以看出格非對其敘事方法的贊賞,贊賞曹雪芹的“假語傳事”,敘述觀點極為隱晦和相對,作者將自己在敘事中隱藏,與讀者進行共同評價。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不可能完全從小說中消失,而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引導為前提,看似不經意,但最終效果卻比“直接的引導和介入”更為有效。
作者與讀者,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兩者一直在進行博弈,是一種心智、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博弈。
二、作者與作者的博弈
在前文已經提到,任何一種敘事模式的確立,都會降低閱讀的難度和樂趣,不僅不會使讀者得到滿足,作者自己也會逐漸厭倦,因此會不斷變換自己的敘述規則與敘事技巧,這個階段,也是作者與作者自己的博弈。在一般認知中,故事敘述的重復會被視為一種低級的錯誤,但通過精心布局的某些合乎情理的重復卻能增強小說的敘事效果,例如馬爾克斯的《一件事先張揚的人命案》。
作家在寫作之初總是會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但是在寫作過程中卻會發現, 故事的走向往往會和自己的設想和構思發生分歧,因為故事有其內在的邏輯所在。但這并不是說作者處于一個放任的狀態,因為控制力依然非常重要。許多作家在進行構思時,并未形成一個完全的小說或故事,而只是模糊出現的一個意象或者某個場景,一種朦朧不能明說的感受,就是寫作者初始的創作動機。 此時當這個原始意象或畫面出現時,作者也就開始了與自己的博弈,格非在書中提到“作者只是朦朦朧朧地被這種意象所指引,陷入了創作的巨大沖動”[3],并提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正是以作者的一段真實經歷為基礎,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對這個意象進行了重新創造和書寫。
“重復”在某種程度上是作者最不愿容忍的事,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但是,我們將一個作家較長時間的創作做一個系統的分析,就會發現某種中心意象或主題一直存在,盡管形式會有所區別。每個作家的寫作都代表著自己對世界的思考,對人生的思考,例如格非在書中提到的海明威,童年的經歷一直烙印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共同的主題,闡釋他對世界圖景的看法和立場。“寫作既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限制。”[4]一個優秀的作家始終力圖不斷超越自己,這就要求作者需要不斷思考,對“重復”主題進行超越。
前面提到過“虛設的讀者”,其中就包含作者自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這個自我,讀者可以感知,但并不能與作者劃上等號,而此時的寫作過程也就是作者與“第二自我”的交流,思想與思想的碰撞,如何寫出自己能夠信服的作品,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疑惑然后解答,這就需要作者學會剖析自己的內心,深入挖掘自己的思想。
作家的思考與認識決定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僅靠作者的“感覺”是不夠的,敘事的流暢需要有一定的技巧,需要作者運用某些方式調整好故事的強度和速度。這就要求作者學會判斷,根據不同的藝術追求采用不一樣的敘事策略,因為這些會最終影響整個敘事的成敗。除此之外,格非還在《語言》這一章節中提到,作者在使用前人的語言成果時,必須仔細選擇和甄別,同時去創造和發現新的語言的方式,不一樣的比喻方式可以成為作家的風格。特別是隨著近年來大眾媒體的普及,報刊雜志對文學語言的大量借用,文學語言的濫用迫使作家不斷更新自己的表達。但是格非同時也提到,“矯揉造作”的語言并不可取,而是需要作家從自己的生命體驗中去尋找和發現。
三、作者與世界的博弈
在如今,作家在與世界的交往過程中本就會不斷變化,世界和個人會發生一些激烈的碰撞。因此,當代作家在寫作之初,就已經決定作家不再是一個旁觀者,不能完全客觀描述這個世界,揭示出他與這個世界的聯系,這就是作者與世界的博弈。
格非在談到作家與世界現實的關系時,引入了俄國著名哲學家巴赫金關于作家兩種視野的理論,作家的第一視野照例會觸及到重大的社會現實的本質因素,第二視野則是關注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義等。因此作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對世界做出反應和表現,在作品中關聯世界,體現一些問題,同時也要在作品中給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給出解答。與此同時我們知道,作家的第二視野涉及的是個人自身,包括對個人成長的反思,因此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也并非必要。格非在書中提到了崛起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新寫實主義小說”,認為小說終于走出了實驗小說的陰影之中,與政治保持距離,不再玩弄語言,不再只是精神的幻想游歷,而是回歸了日常的塵世。雖然部分新寫實小說太過沉醉于瑣碎的日常,但是新小說的作家們已經開始從單純臨摹外部世界中走出,而是通過自己的觀察,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構現實世界,準確揭示了現實世界的真實屬性。優秀的作品絕不僅僅只是作者感受到的世界,而是對作者把握“真實”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以作家的個人體驗為基礎,以作家的敏銳和智慧為前提,去探索世界的真實本質。
隨著商業化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學在社會上已很難再產生以前的那種轟動效應,文學在社會、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更是每況愈下,我們不禁會思考,文學的未來在何處,作者該如何處理小說與世界的關系? 格非在本書中,通過《小說的未來》這一章節,回答了這個問題。格非認為,隨著近年來電影電視技術的挑戰,小說確實面臨著捉襟見肘的局面,“小說的死亡”雖未必是現實,但也不是杞人憂天。但是,作者在通過分析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小說《南方》時,認為后現代主義小說盡管林林總總,表達方式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在思想深度上,還是從敘事方法上,都隱藏著對現實主義敘述規則的超越,力圖找到通向人類精神的統一之路,以達到人類精神統一的彼岸。
在探討文學危機成為一種時尚時,格非卻認為是作家們的左右搖擺和無所適從的心理所造成的,因為文學從來就是一項寂寞的事業。對于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說,世界的不斷變化縱然會帶來很多問題和挑戰,但是發現和創造始終是作家們最為基本的神圣使命,真正的文學永遠不會死亡。
四、小結
格非的《小說敘事研究》雖然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小說的敘事技巧,但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這并不是格非的真正用途。在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格非對現代主義小說和后現代主義小說的思考,通過其具體論述也能發現,格非通過剖析小說的語言、結構、形式等表達了他對經典小說的認識,同時表示,一篇優秀的小說具有多種特質,需要作者從各個方面進行精心的思考和處理。
本文從作者與作者,與讀者,與世界的三個關系的博弈具體分析了在小說敘事中各方力量的一個制衡,一方面,三個關系的不斷博弈是小說敘事策略不斷發展的一個內在推動力;另一方面,在推動小說敘事手法或者策略不斷發展的同時,小說的內涵,其承載的內在思想也在不斷豐富,小說敘事的變化也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要求。
注釋:
[1]格非 著《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頁。
[2]格非 著《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22頁。
[3]格非 著《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51頁。
[4]格非 著《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