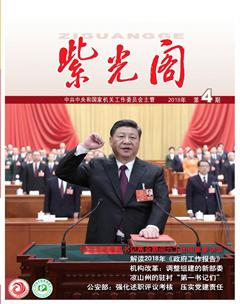組建應急管理部的現實意義
鐘開斌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組建應急管理部是此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我國應急管理體制的重大調整,是我國應急管理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意義重大。
我國應急管理體制的歷史沿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我國是災害多發頻發的國家,黨和國家長期高度重視應急管理工作。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同發展階段,我國逐步形成了各有特點的應急管理體制。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建立的是以部門管理為主、非常設機構為輔的應急管理體制。為了有效應對水旱、洪澇、地震等自然災害,工礦企業生產安全事故,血吸蟲病等傳染病疫情,各級政府組建了民政、水利、地震、勞動保護、衛生等專職部門。與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這種部門化的應急管理體制以單災種分類管理為基本特征。在橫向上,相關職責分屬多個職能部門, 各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在縱向上,各職能部門上下高度一致, 單個部門的專業化程度較高,獨立執行任務的能力較強。同時,為了加強跨部門、跨區域協調,我國當時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中央救災委員會、中央防汛總指揮部等長期性協調機構以及針對唐山大地震等重特大災害的臨時性應急領導小組。
改革開放后至2003年,我國建立的是由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牽頭協調的應急管理體制。改革開放后,我國面臨的公共安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突發事件的影響日趨廣泛。由于平時各自為政,缺乏綜合協調職能部門進行統籌,我國傳統的以部門為主、分類管理的應急管理體制,逐漸暴露出協同性較差、綜合應對能力不足等問題。為此,我國開始在常設的分類管理機構之外設立了許多非常設機構(如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國家森林防火總指揮部、國家減災委員會),承擔重特大突發事件跨部門組織協調和臨時性應急處置任務。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與應急管理相關的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共有16個(其中指揮部7個、領導小組5個、委員會4個),聯席會議制度有9個。
2003年至2018年應急管理部成立前,我國建立的是由政府應急管理機構和部際聯席會議牽頭協調的應急管理體制。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國應急管理組織指揮不統一、信息渠道不暢通等問題。此后,我國全面推進以“一案三制”(應急預案,應急管理體制、機制和法制)為核心內容的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在此期間,由主辦部門牽頭進行協商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迅速發展,政府應急管理機構的綜合協調職能得以明確,以政府應急管理辦事機構為運轉樞紐、協調若干議事協調機構和聯席會議、覆蓋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體制逐漸形成。截至2011年5月,全國有22個省(區、市)成立了應急委,其余9個省(區)明確了應急管理領導機構,各省(區、市)都成立了政府應急辦。全國地級市建立應急管理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的比例分別為97.8%、96.1%,縣級政府相應比例為89.6%、80.8%。
2018年應急管理部的組建, 標志著我國開始建立由強有力的一個核心部門進行總牽頭、各方協調配合的應急管理體制。根據方案,將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的職責,國務院辦公廳的應急管理職責,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職責,民政部的救災職責,國土資源部的地質災害防治、水利部的水旱災害防治、農業部的草原防火、國家林業局的森林防火相關職責,中國地震局的震災應急救援職責以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國家減災委員會、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的職責整合,組建應急管理部,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公安消防部隊、武警森林部隊轉制后,與安全生產等應急救援隊伍一并作為綜合性常備應急骨干力量,由應急管理部管理。
組建應急管理部的現實取向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組建應急管理部,是落實黨中央重要決策部署的具體體現, 集中反映了當前我國應急管理體制改革的三大取向。
一是綜合化。在當今開放社會,突發事件的并發性、連鎖性、復合性影響日益增加;強化跨部門、跨區域、跨行業綜合協調,實現信息共享和資源統籌,成為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務。《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河北唐山調研考察時指出,要“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2016年12月19 日)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也規定:“國家建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組建應急管理部,整合優化分散在各部門的應急力量和資源,明確其對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這兩大類突發事件的統籌管理職責以及對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其他突發事件的協同配合職責,充分體現了《決定》提出的“加強、優化、統籌國家應急能力建設,構建統一領導、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國家應急能力體系”的目標,有利于盡快“推動形成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平戰結合的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
二是屬地化。《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指出,“科學設置中央和地方事權,理順中央和地方職責關系,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國作為災害多發的大國,做好應急管理工作,需要同時充分發揮好中央的指導作用和地方的主體作用。過去,一些地方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存在等待、依賴、觀望的思想。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提出并實行“地方作為主體”的應急管理工作新思路,強化地方的主體意識、主體責任、主體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探索出一條中央統籌指導、地方作為主體、災區群眾廣泛參與的恢復重建新路子”。蘆山地震災區恢復重建,中央首次明確“地方作為主體”的新機制,實現了由中央直接安排部署向地方具體負責的轉變,形成了一套有別于過去舉國體制的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新機制。《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特別提出:“需要說明的是,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一般性災害由地方各級政府負責,應急管理部代表中央統一響應支援;發生特別重大災害時,應急管理部作為指揮部,協 助中央指定的負責同志組織應急處置工作,保證政令暢通、指揮有效。”
三是社會化。面對形形色色的突發事件,政府不能也不必“大包大攬”“單打獨斗”。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眾等既是突發事件的直接受眾,也是應急管理的重要主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維護公共安全,編織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形成公共安全人人維護的良好氛圍。《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要“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廣泛參與”“更加注重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建立完善災害保險制度,加強政府與社會力量、市場機制的協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統籌志愿者隊伍、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巨災保險等市場力量,是應急管理部組建后需要統籌的重要職責。
確保機構改革平穩有序過渡
組建應急管理部、推進應急管理體制改革,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但改革往往存在一定的變更風險。應急管理機構改革政策性強,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可以預料,在全國各級應急管理部門組建、應急力量和資源整合優化的過程中,人的去留進退,機構的撤并重組,職能的劃轉移交,特別是消防隊員、森林武警隊員的深深軍人情結等,都會產生出許多活思想。突發事件的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突發事件也不會等新部門完全組建好了再發生。
隨著當前各地陸續將進入主汛期,地質災害、地震災害不確定因素多,其他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也處在易發階段,更要做好新部門組建期的變更風險管理工作,確保改革平穩有序過渡。建議盡早出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計劃,明確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最大限度地減少機構調整磨合期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加強輿論引導和情緒疏導,做到“思想不亂、工作不斷、隊伍不散、干勁不減”,為人民值好班、為國家站好崗,確保有力、有序、有效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重特大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