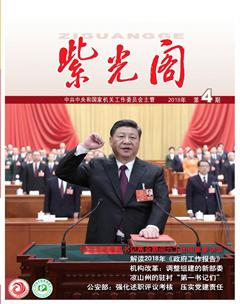日美貿易摩擦的歷史回顧與經驗教訓
劉軍紅
二戰后的日美經濟關系堪稱一部“日美貿易摩擦史”。作為軍事同盟國,日美在貿易上長期持續對立,實為罕見,也是令人費解的現象。
日美貿易摩擦早在日本經濟剛剛走出“戰后”的50年代便已開始了。圍繞棉織品對美出口,美日發生了激烈對立。之后,鋼鐵、電視機、機床、汽車、半導體等制成品的對美出口成雙邊摩擦的主要對象。但80年代中期開始,日美貿易摩擦的重心轉到了日本市場開放、擴大進口等領域,持續近十年。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日美貿易摩擦在一段時間里“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貨幣及其權力博弈的對立。日美微觀層面的貿易摩擦轉變為宏觀層面的體制碰撞,以及金融貨幣權力的較量。特別是冷戰結束后,日美經濟矛盾堪具“意識形態”對立的屬性。
貿易摩擦與自主限制
二戰結束后的50年里,日本出口品結構與產業結構同時發生重大變化,但日本出口對象國卻沒有明顯改變,幾乎一以貫之地保持著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地的構圖。即使如今,日本對華出口占比上升,對美出口占比下降,中國一度上升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對象國,但2013 年以后,隨著中美經濟同步轉型,美國再成日本最大的出口地。美國市場對日本貿易的重要性依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盡管最初,日本的出口品也被指責為廉價而劣質,但隨著日企品質意識不斷改善,日本制品不斷被美國市場所接受,在不同時期形成暴風驟雨般的出口劇增局面。如1950年到1952年的2年時間里,日本棉織品對美國出口暴增40倍。日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要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反傾銷措施、臨時進口限制措施,以及自主出口規制措施。在方式上,美國多用雙邊談判方式,即一對一與日本談判,集中提出限制措施。其結果是,雖減少了日本對美出口量,但無法堵住其他替代出口者。如,關于棉織品,1971年美日簽署了“日美纖維協定”,解決了日美摩擦,但香港和臺灣等地棉織品乘勢打入美國市場,紡織品的貿易摩擦反而國際化了。直到1974年,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達成了一攬子國際協定,紡織品貿易納入國際管理體系,紡織品貿易摩擦才得以消停。
世界經濟體制巨變,日美貿易摩擦升級
整個上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貨幣體制危機,匯率制度從固定匯率轉變為浮動匯率制,國際政治也從美蘇兩極對立轉為“中美蘇大三角格局”。此間,日本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期注重“量的增長”轉變到“質的沉淀”,日本企業也完成了根本轉型。這又奠定了80年代到9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集中到來的前提。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完成了增長方式的轉變,形成了“日本經濟模式”;日本企業實現了經營方式的升級,形成了“日本經營方式”。在電子技術飛躍發展下,日本制造業實現了“機電一體化”升級,一時間“豐田方式”“日本禮贊”享譽世界。日本的汽車、半導體、機床,以及一系列升級版家電流行于全球,成為世界級名牌產品。“日本造”又一次如暴風驟雨般“空襲”美國,日美貿易摩擦如火如荼。這一次日美貿易摩擦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持續到90年代中期,歷經10年,跨越兩個時代。美日之間所動用的“摩擦武器”堪稱史無前例。美攻日守,互有攻防。在摩擦方式上,自主限制、數量限制、鋼鐵協定、半導體協定……可謂“十八般武藝全面上陣”,“刀槍劍戟一應俱全”。最具代表性的解決方案就是日美結構協議、日美框架協議。
這一時期,日美貿易摩擦的一大特點是圍繞“市場開放,擴大進口”展開制度博弈。特別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的全球經濟戰略轉變,在經濟上不再容忍“日本第一”。克林頓政府甚至提出“日本經濟是資本主義異類”,美日經濟“模式之爭”躍然紙上,微觀層次上的貿易摩擦升級為宏觀層面的體制碰撞,堪稱意識形態的對立。誠然,日美經濟矛盾的最終解決還是落腳于國際化的多邊貿易體系,即WTO為美日解決貿易摩擦提供了協調機制。WTO不僅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有管理的自由貿易體系,也是迄今唯一自帶強制性“爭端解決機制”的多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作為進攻方的美國的訴求得到了公平的解決,日本的反擊也得到了法制化的保障。
貿易摩擦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1984年,美國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赤字雙雙超過1000億美元,至今升勢不減。而1991年日本貿易順差首超1000億美元,翌年經常收支順差再超1000億美元。日美貿易、經常收支的反向變動,成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美貿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綜合征”的基本動因。
所謂“日元升值綜合征”,是指 1971年以后日美政府的貿易、匯率和金融政策所引發的不規則的日元升值趨勢,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日元國際化政策的前因。可以說,日元國際化政策的目標之一,就是使日本經濟增強日元升值抵抗力,并使升值有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制瓦
解后,日美貿易動向成為日元美元匯率變化的重要因素。而此前20 年,日本制造業的生產率上升率和生產規模的擴張率均已超過美國,這被認為是美國遏制日本的發端。
但實際上,對美國而言,單純的日本經濟增長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并不能構成威脅。關鍵在于這種增長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合流,沖擊了“美國治下的和平體制”。如,1971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首次轉為赤字,紐約股市大調整,而此前,歐洲、中東搶購黃金,大搞“脫美元化”,引發世界性“黃金荒”。同時,蘇聯突然闖入世界糧食市場,又引起世界性糧食供應緊張。在此背景下,日本優先發展“重大厚長”型工業,引發世界資源價格驟漲,環境惡化。
而在更深層次問題上,還存在著日美對外資產關系的逆轉。即在日美貿易收支逆轉下,1983年美國對外資產余額銳減40%,1985年陡然出現1119億美元的純債務,戰后首次轉變為純債務國,1986年成為世界最大純債務國。與此同時,日本于1984年實現對外純債權倍增,1985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1986年成為世界第一純債權國。日美對外純資產關系的逆轉,反映了日美經濟結構的相對變化,更被美國看成日本資本市場相對閉鎖的結果。
在美國看來,戰后,日本對外資實行嚴格管制,資本輸出增加的同時,資本輸入難以擴大。1983年后,隨著日本企業資金剩余,日本民間對外證券投資,大量經過“歐洲日元市場”涌入美國證券市場, 成為日美對外資產關系逆轉的要因之一。同時,美國資本的主要輸出地——拉丁美洲出現債務危機,致使美國對外資本輸出銳減,而其國內投資形態又發生了變化,證券投資流入增加,銀行對外融資減少,資本對外影響力下降。
日美資本輸出結構的變化,正是美國利用貿易、匯率政策敲打日本,席卷其金融市場的根本動因。
從當時美國的全球戰略看,美國將對日貿易、匯兌制裁納入了全面捍衛美國主導體制的軌道,堪 稱“帝國反擊戰”的一部分。“反擊戰”的內容包括:對前蘇聯禁運、控制中東、封鎖伊朗,與搞黃金美元脫鉤相結合,以“石油、美元、戰爭三位一體”戰略,迫使日本等分擔國際貨幣體制成本。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高,但在資本輸出上并未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特別是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大部分回流到美國國債市場, 成為后者長短期利率逆轉的主要條件。同時,中國產品的低廉價格反過來又維護了美國整體的物價平緩,使其金融當局得以專心使用利率手段,抑制不動產泡沫,而不必過度擔心緊縮金融導致經濟下滑。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爆發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并不符合美國的現實利益。
對中國而言,利用貿易順差條件,主動調整貿易結構、深化匯兌制度改革,增強匯率彈性,強化國民經濟對匯率波動的抵抗力,使貨幣升值轉化為經濟穩定增長的有利因素,更有利于維護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