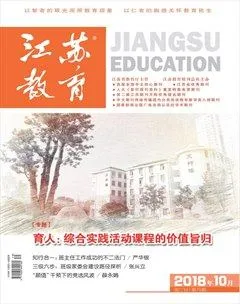讓兒童在游戲中創造童年價值
【摘 要】游戲始終伴隨著兒童的成長,兒童在游戲中發現自我,也借助游戲一次次完成自我實現的體驗。兒童熱衷于參與游戲或者創生新的游戲,因為他們能夠“賞析”游戲中微妙的、象征性的內涵,從而實現心理補償、身份確認、知能發展。教育者只有真正理解游戲在童年階段的豐富價值,才能夠給予兒童適切的陪伴、引領和幫助。
【關鍵詞】游戲;兒童成長;同伴文化;心理補償;自我實現
【中圖分類號】G6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8)79-0061-04
【作者簡介】李竹平,北京亦莊實驗小學(北京,100176)教師,高級教師,安徽省語文特級教師。
筆者曾在《童年與同伴文化》一文中指出,游戲與“小團體”是兒童創造同伴文化的方式和產物,游戲當中存在分享文化、層級區分、身份確認等內涵。那么,游戲對于童年和兒童成長的價值和意義有哪些?是如何體現出來的?教育者又應該怎樣看待兒童游戲?
約翰·赫伊津哈在《游戲的人》中指出:游戲就是游戲,沒有除了其本身之外的目的。他認為正是游戲的這種特性促使其在生命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文化以游戲形式產生,即一開始就是在玩游戲。即便那些旨在直接滿足生存需要的活動,比如狩獵,在古代社會也往往呈現出游戲形態。社會生活的形式超越生物學意義,具備游戲性質,其價值得以提升,正是通過游戲,社會表達出對生活的詮釋和對世界的認識。”[1]這段話提醒我們,游戲在兒童成長中的價值和意義應當是多么的豐富。
一、游戲與心理補償
十歲的烜,沉迷于搓捏小紙人,每天在教室里用廢紙捏出一個又一個小紙人,然后藏在桌肚里、書包柜里。下課時,他會一手拿一個小紙人,玩起小紙人打仗的游戲,有時上課也會趁老師不注意偷偷地玩。偶爾,他會邀請旁邊的小伙伴一起玩。他們一邊操縱小紙人,一邊敘述自己想象的各種故事情節。這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因為類似的游戲一般常見于學前兒童或小學低年級兒童,五年級的男孩大多覺得這種游戲很幼稚,即使是玩想象中的打仗游戲,也多扮演電子游戲或科幻電影中的角色。另外一個值得探究的情形是,平時玩小紙人游戲時,烜一個人只需要操縱兩到三個角色,但他會不停地搓捏出新的小紙人,以至于不到一個星期時間,他就積累了整整一塑料袋小紙人。通過觀察和聊天,筆者逐漸理解了這個同齡人看來十分幼稚的游戲對這個男孩的價值,尤其是心理補償的價值。
幼兒一開始參與同伴游戲,大多是基于分享和身份確認的需要,隨著年齡的增長,到了小學階段,這種需要會更加明顯和明確。一個兒童發起的游戲有沒有得到同伴的響應,或者自己有沒有被熱情地邀請參與游戲,都會伴隨著兒童對自己在同伴中地位的判斷和體驗,進而逐漸形成比較固定的自我認知和評價。有的兒童在游戲中找到了自信,有的兒童在游戲中發現自己總是被邊緣化或者只能充當無足輕重的配角,從而導致自信心受損。兒童與大人一樣,沒有支配權和控制權就會缺乏安全感。玩小紙人游戲的烜,因為在家中倍受溺愛,與同學相處時自我中心表現突出,缺乏對規則的理解和尊重,同時由于閱讀能力的缺失,思考力的相對不足,在很多話題上與同學不在一個理解層次上。隨著年齡和心智的發展,烜逐漸意識到在家庭中輕而易舉獲得的支配權和控制權根本無法在教室生活中擁有,沮喪感和挫敗感促使他努力尋求心理補償,直到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了小紙人游戲。而那個被他順利邀請參與游戲的另一個男孩,心智年齡被診斷為滯后同齡人近兩年。在他們的共同游戲中,規則的制訂、故事的編創等,創造游戲的烜總是居于支配地位。面對同學的白眼甚至嘲笑,烜從一開始的生氣到后來的置之不理,說明他對自己的游戲行為有比較清晰的價值判斷。對于一個有強烈的認可需要的兒童來說,通過自己創造的游戲獲得心理補償顯然比面子更加現實。
烜在玩小紙人游戲時,與學前兒童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他不斷增加小紙人的數量,而不是反復用三五個小紙人來組織游戲。他這么做,基于兩個想法,一是不斷創造新的小紙人是游戲的一個組成部分,二是被裝進方便袋中的小紙人都是在游戲中被打敗的“人”,被打敗的“人”越多,他的成就感就越大。
了解和理解了烜在小紙人游戲中扮演的角色和他的心理體驗,我們就不會輕易地用“幼稚”來評價他的游戲行為。游戲正好反映了他在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困惑和需求,這也提醒教師和家長,烜在這一階段的成長中需要怎樣的陪伴、引領和幫助。
“兒童的幻想游戲是他們的情感寄托,幫助他們對抗各種憂慮和恐懼……”[2]不僅一個人的幻想游戲具有心理補償的價值,幾個人的幻想游戲也可以幫助兒童對抗壓力。除了在《童年與同伴文化》一文中提到的“三劍客”外,筆者班級還有幾個男孩,一到下課時間就聚在教室后面的世界地圖前,他們一邊指指點點,一邊編創幻想的劇情,玩“戰爭”游戲。這幾個男孩恰恰是在班級生活中和學業上遭到的批評更多,也被家長“關照”得更多。
二、游戲與身份探索
“我是誰”這樣的哲學命題總是伴隨著生命的成長和體驗,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人們總是在用行動來尋求一個讓自己認可的、能提供安全感的答案。兒童往往通過參與游戲來積極主動地探索“我是誰”。兒童同伴文化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堅持不懈地試圖掌控自己的生活”[3]——玩耍和游戲是兒童進行這種身份探索的普遍形式和場域。
成人往往有一種錯覺,認為兒童因為年齡和身體的緣故,天然地對成人有依賴性,甚至依賴成人的權威,所以把兒童的游戲都看成幼稚的、無意義的玩耍。例如,當兒童樂此不疲地玩爬高游戲,站在高處向成人炫耀自己的“高大”時,成人僅僅報以溫柔的微笑了事,沒有意識到兒童是在用這種方式來挑戰成人的權威。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幾個同齡的孩子一起玩耍,一個孩子站上椅子告訴同伴自己最高時,很快就有孩子站上更高的物品以證明自己還要高,或者指出第一個孩子只是因為站在了椅子上才顯得高而已。兒童對“高大”的迷戀,源自他們認為成人之所以相對于他們處于支配地位,就是因為成人長得“高大”——“高大”就是一種身份的象征。
還有一種情況也證明了這一判斷。在角色扮演游戲中,小學低年級的兒童都希望自己能扮演有控制權的成人角色,而年齡稍大一點的兒童會熱衷于扮演大家公認的“主角”——班級戲劇選角時就會遇到這種情況。兒童這么在意角色的“分量”,既是源自對角色地位本身的理解,也是在同伴中進行自我身份的探索,探察自己是否得到大家的認可和重視。教育者讀懂了這一點,往往就能根據兒童的心理,在具體情境中以理解和對話的姿態,引導兒童從不同的視角來達成身份認同。
身份探索總是在關系的建立和理解中不斷得到回應,并不斷努力創造個體的身份價值。兒童大多喜歡與確定的同伴一起共享某個游戲,在游戲中標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系——認為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們的相互信賴是團隊強大的基礎。五年級的曼、婕、萱三個人總在一起玩追跑游戲,并分享對班級同學的看法。她們視彼此為“閨蜜”,在對班級同學和事情的評價上尋求一致,如果其中一人有不同看法并試圖說服另外兩個人,那這個人就會受到質疑:我們還是好朋友嗎?她們不喜歡其他人加入追跑游戲,除非事先獲得了他們的一致同意。她們這么做,一是為了捍衛友誼,二是防止屬于她們的心理空間被“外人”入侵。如果要拓展團隊,一定要是三個人都欣然同意的。這樣的“團隊”中,更有主見或主意的人,往往意見更加受到重視。
男孩子更加執著于幻想游戲,除了前面提到的心理補償的需要,同時也在幾個人共同經歷的幻想游戲中探索自己的身份。他們經常會在故事發展到某個階段,在由誰來主導情節的發展方面而爭執不下,就是有力的證明。
可以這樣說,游戲創生了具體的同伴文化,實現了兒童身份的一次次確認。
三、游戲與知能發展
兒童參與的游戲一般分為兒童自己的游戲和成人設計的游戲(電子游戲除外),這兩種游戲目的性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從實際上促進了兒童對知識的學習和應用,以及各種能力的發展。
體育游戲促進兒童體育知識的豐富和身體素質的發展,這早就成為共識,其他類的游戲對于兒童知能的發展,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當兒童在游戲過程中停下來,就游戲的內容和規則重新進行探討時,實際上他們就是在進行積極的反思,將經驗(知識)的理解應用于當下的游戲,或者在游戲中學習并應用新的知識,以便使游戲更具有共同參與的價值。例如,下課時幾個兒童圍坐在一起,一邊用手打節奏,一邊輪流提問并逐個回答這樣的問題:“廚房里有什么?”這個游戲不在于輸贏,而在于反應的速度和生活知識的積累,回答不僅要與問題對應,還要跟上節奏。要能夠順利地參與游戲并從中獲得成就感,兒童還要善于賞析游戲中的“妙處”,如果對游戲規則和效果的追求了解不夠,就會造成游戲中斷,不得不停下來重新理解游戲規則。
《美國學生游戲與素質訓練手冊》一書中指出:“游戲是培養孩子良好性格和社會技能的有效方法,最關鍵的一點是游戲還很有趣,能讓孩子在玩耍中快樂成長。”這本書選編了103個游戲,這些游戲分別著力于培養兒童的團隊協作能力、自信心、溝通力、發現力、情緒管理能力和應對力。這些游戲就是成人設計的游戲,兒童參與這類游戲,通過強化體驗和積極反思逐步實現一定的成長目標。在文化課學習上提倡游戲化,也是基于游戲是兒童所喜聞樂見的形式,兒童能在游戲中通過變通和創新來獲得知識。
四、童年與電子游戲
有一個教師論壇討論的話題是“學生可不可以擁有手機”,反對學生擁有手機的理由都集中在學生會用手機玩游戲并且會沉迷于游戲上。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理由,因為在這個理由里,游戲,或者說電子游戲,成了洪水猛獸。世界上好玩的事情那么多,為什么人們特別擔心兒童沉迷于電子游戲呢?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探討,就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質:電子游戲憑什么容易讓兒童著迷?文章開頭講過,煊每天玩小紙人游戲,也到了沉迷的境界;有的“小團體”連續幾個學年每天都會在下課時間聚在一起玩同一個游戲……在這些游戲中,有的滿足了兒童的心理補償,有的滿足了兒童對友情的渴望,有的促進了兒童的身份探索,只是很多時候成人因為高高在上,誤讀了兒童的游戲,才自以為是地認為兒童的游戲不值一提。同樣,兒童喜歡電子游戲,是因為電子游戲和生活中其他游戲一樣,可以幫助他們實現分享的需要、自我確認的需要、情緒紓解的需要……教師和家長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性看待兒童與電子游戲的關系,不至于使兒童“沉迷”電子游戲,否則,兒童即使不沉迷電子游戲,也會沉迷于天馬行空的想象游戲當中。
在電子游戲還沒有出現的年代里,童年也是與各種游戲密不可分的。馮驥才在《歪兒》中就寫到,一群兒童玩踢罐電報游戲,也到了“沉迷”的地步;筆者小時候與伙伴玩游戲,經常天黑了還需要大人一再“威脅”才磨蹭著回家。電子游戲缺少了現實世界中的互動性,但一定實現了兒童心中渴望的“互動”,這種“互動”隱秘地在游戲世界中展開,補償了兒童在現實世界中可望而不可即的需要。如果成人能夠積極地與他們分享,跟他們一起玩,一起探索,情況就會大大出乎成人的意料。到那時,兒童可能不再沉迷于電子游戲,而是“沉迷”于與成人分享游戲。
一款成功的電子游戲的開發,一定有洞悉了人們心理的機制滲透其中。童年的發展,兒童的成長,身體和心理都在路上,而心理的成長更加玄妙。教育者關注不到兒童心理成長的玄妙,無法從游戲中解讀兒童的需要,任何游戲都可能會被看成是浪費時間。
兒童參與已有的游戲,同時也會創造游戲。在參與和創造之間,包含了對規則的理解和自我實現的追求。海倫·施瓦茨曼認為,兒童不僅在游戲中嘗試成人世界的精選內容,同時也把游戲當作“評論和批評的舞臺”。沒有游戲,就沒有童年,就沒有兒童的自我實現,游戲之于童年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參考文獻】
[1]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文化的游戲要素研究[M].付存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4.
[2]威廉·A.科薩羅.童年社會學:第四版[M].張藍予,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143.
[3]威廉·A.科薩羅.童年社會學:第四版[M].張藍予,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