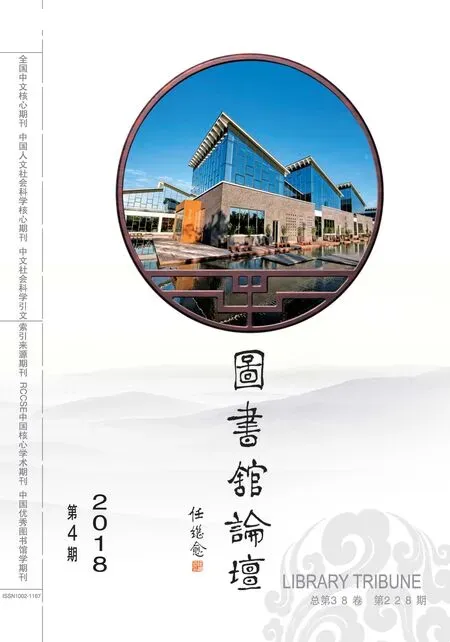知識啟迪與權威尊崇:基于重復發表的引文動機研究
劉 宇,張永娟,齊林峰,回勝男
0 引言
自績效管理思想引入學術界后,學術評價便成為熱點話題,歷時數十年不衰。績效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強調投入產出比,理想的績效測量包括軟硬兩方面[1],硬指標主要測量產能(Productivity),衡量行為主體產出數量;軟指標主要測量效能(Effectiveness),衡量行為主體產出的質量和效果。依據績效管理思路,學術評價從產能和效能兩個角度展開。由于非應用型科研成果的知識價值(即效能)需要經過歷史檢驗才能最終顯現,難以即時準確測量,所以學術界通行的做法是將效能簡化為被引用次數。因此,當前學術評價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對科研主體進行量化考核,即將科研主體在一定級別出版平臺上的發表數量作為職位晉升和資源分配的依據。具體來說,就是計算科研人員在一定級別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篇數,或計算在一定級別出版社出版專著的本數。這一量化評價方式興起于1970年代的美國學術界[2],1990年代在我國開始盛行。
量化學術評價的操作前提是為出版平臺評定等級。由于期刊在當代學術傳播中的突出地位,“為期刊定級和排序遂成為學術評價的要務”,成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3]。傳統上期刊的學術水平和學術地位停留在心知肚明的認知層面[4],學術共同體有一種潛在的集體共識。自SCI創立之后,這種潛在共識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顯化。論文的被引用次數逐漸被默認為等同于論文的質量和價值,影響因子成為衡量期刊等級的最主要指標和期刊評價最主要的工具[5]。因此,學術評價在很大程度上被引文評價左右。引文評價的合法性基礎是:引用關系建立在文獻之間的知識啟迪和借鑒之基礎上,能夠有效地體現出知識傳承和累積[6]。然而這一預設卻難以與科研人員的主體感知相符。“難有同行的科學”告訴我們,最能夠準確把握研究成果質量的小同行就是作者本人[7]。不過,很多發表經驗豐富的學者發現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往往不是被引次數最多的作品。“洛瑞悖論”從學科角度對引文評價的合法性提出挑戰[8]。這些事實意味著引文評價的邏輯預設有待檢驗,如果采用引文數據進行學術評價,必須對學者的引用行為和引文動機進行深入研究。
1 文獻回顧
對研究人員在科研寫作過程中為什么會引用文獻以及為什么引用某一特定文獻的心理動機,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解釋:認可論和說服論。認可論認為引文動機源自知識啟迪,它植根于規范主義的科學社會學;說服論認為使用引文是作者為了說服讀者相信自己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價值,它植根于建構主義的科學知識社會學。
1.1 科學社會學與知識啟迪
以默頓為代表的規范主義科學社會學認為,現代科學興盛的原因在于科學制度存在著自身特有的精神特質,“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性以及有組織的懷疑態度,構成了現代科學的精神特質”[9]。這四大精神特質規范著科學共同體的價值觀,約束著科學家的行為。普遍主義精神特質要求科學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承認,不依賴于生產該知識的科學家的個人特征或社會屬性,只能依據它的知識貢獻度,即研究結論與客觀事實的吻合程度以及研究結果是否是揭示自然規律的“真知”。在普遍主義精神特質的約束下,引文是對以往研究成果優異性和知識貢獻的一種工具性承認,是科學界處理科學發現優先權和知識產權的一種社會機制(SocialDevice)[10]。
當一篇文獻被另外一篇文獻引用時,表明施引作者受到被引文獻的啟發,用引文這一符號形式向被引文獻的作者表達學術認可。引文作為科學話語體系的一部分,是施引者“給予同行的工資”[11]。一篇文獻的知識貢獻度越大,對后續研究就越具有啟發性,被其他文獻引用的次數就會越多[12]。因此,引用關系體現了文獻之間的知識傳承和知識生產的累積性,引文網絡體現了“人類知識空間的擴散過程”[13]。在這一意義上,引文成為學術知識圖譜中自然凝結的足跡[14],科學文獻之間的引用關系反映出科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是一個與砌墻(Bricklaying)類似的累積過程[15]。
在實證思路上,支持認可論的學者主要通過展示已經被歷史證明的優秀成果、學人、機構或期刊所獲得的被引次數的確高于同時期的其他競爭對手,以此證明學者寫作的引用行為符合規范主義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在此基礎上,使用引文數據來預測研究成果能否經受住歷史的檢驗是一種有效的方法,以引文評價的結果進行學術資源的分配是合理的。
Myers的研究發現,美國心理學家發表期刊論文的總被引次數與其獲取各種科研獎項及殊榮顯著相關[16],包括被選為美國心理學協會(APA)主席、被列入美國科學家名錄(Am erican Men of Science)等。Sim onton對1879-1976年間69位美國杰出心理學家的歷史研究發現,他們的職業成就、逝世后的聲望(Posthum ous Reputation)與其被引次數顯著相關[17]。Lawani等以870篇癌癥研究的期刊論文為樣本,根據其是否被The Year Book of Cancer摘錄分為高中低三檔(被摘錄的期刊論文需要經過嚴格的同行評審),發現被同行高度評價的論文在發表后的頭5年被引次數明顯高于普通論文[18]。Saha等通過對113名內科醫生和151名臨床醫學研究人員的調查發現,專家對9種普通醫學期刊的感知質量和影響因子評價的結果高度相關[19]。Rinia等以56項荷蘭物理學基金項目為對象,收集項目產出的5000余篇論文及其被引數據,發現評審專家對項目的評價與項目論文的被引指標高度相關[20]。Garfield等對諾貝爾獎得主進行了系統的引文分析,研究發現同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和普通科學家在科研產出和影響力上均具有顯著差異,這一結果使其深信“基于引文數據的簡單、量化、客觀的評價算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支持甚至預測基于人類判斷的復雜、質化、主觀的選擇過程”[21]。
1.2 科學知識社會學與說服性修辭
以拉圖爾為代表的科學知識社會學認為,科學事實的發現和科學知識的生產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科學為了應付日常實踐中的各種需求同樣到處滲透著利益因素[22]。科學論文是集事實呈現與價值判斷、邏輯論證與說服修辭于一體的文本形式[23]。引文是科學文本中一種組織化的修辭方式,“所有這些引證都被指向特定的目標、被為著一個目的組織起來:為斷言提供支持”[24]。
Gilbert對科研成果轉化為科學知識的社會過程進行了分析:科學研究的發現要變成科學知識,必須經過同行承認的社會化過程,即科學共同體對研究發現的真實性和價值要形成一定的共識[25]。通常情況下,新研究成果的真實性和知識價值并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它不僅依賴于研究的質量和水平,也依賴于作者說服同行的能力。作者發表文獻的目的就是要說服讀者相信自己研究發現的真實性和重要性,而引文恰恰是展示研究成果有效性和重要性的修辭工具[26]。通過引文,新發表的文獻和已有知識之間建立起聯系,作者使用已經被認可的各種文獻為自己研究的合法性提供背書和支持。例如,作者寫作時會選擇引用那些“重要的”“正確的”文獻來證明自己研究的科學價值及其和已有科學知識的自然聯系,使自己的研究發現融入到現有的知識體系之中;選擇那些“有爭議的”文獻作為挑戰的對象;避免引用那些瑣碎的、不重要的文獻。整個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充滿了社會化的建構和操作。
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同樣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研究顯示,作者的引文動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化心理過程,受到學術權威等社會因素的影響。普賴斯的研究發現[27],工程技術領域論文的參考文獻數量顯著少于各個純科學研究領域,因為這些論文可以直接通過實物展示研究的真實性和價值,不需要文獻之間的背書和支持。這恰恰說明了引文是科研寫作中的一種修辭工具[28]。
此外,實證研究顯示,科學文獻之間的引用呈現出顯著的馬太效應。Tol對100位高產經濟學家的引文分析發現,馬太效應在作者和論文兩個層面均產生明顯作用,由知名作者發表的知名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呈現出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29]。Medoff研究發現,在將期刊作為控制變量的基礎上,那些由精英院校作者撰寫的論文的被引頻次顯著高于非精英院校作者的論文[30]。Peng等以2000-2009年間有關互聯網研究的SSCI期刊論文為樣本研究發現,論文被引用的決定性因素是發表該論文刊物的特征,論文的內容特征和形式特征對被引的影響受到刊物特征的調節[31]。Lariviere等對SCI、SSCI、A&HCI期刊論文進行大樣本跨學科研究,得出的結論與Peng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證實了馬太效應的普遍性[32]。
馬太效應其實違背了科學的普遍主義觀,因為累積優勢效應已偏離了業績本位(Achievement)的原則。[33]文獻引用中的馬太效應可以證實引文動機受到社會性因素影響,引用行為是一種社會化行為,無法用普遍主義的科學規范精神進行解釋。正如說服論的理論解釋,為了達到說服的目的,作者傾向于引用那些被認為具有權威性的文獻,而這一動機又使權威作者、權威機構或權威出版物更容易成為高被引對象。科爾兄弟的研究發現,科學系統內部根據榮譽獎勵、職業位置和知名度形成一定的等級結構,它會反作用于個體成果的被接受程度,形成科學界的社會分層[34]。
1.3 總結和研究問題
通過文獻回顧不難發現,科學社會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實證數據的支持。但是,規范主義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是一種簡化的理想模型,就如同經濟學中理性人假設一樣。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決策和行為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礎上的[35]。盡管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同行評議和引文評價的結果具有相關性,但是也有不少實證研究表明,同行評議和引文評價的結果并不一致,或在不同學科間相關性差異較大[36-37]。建構主義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引入了社會學的視角,對引用行為的復雜性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豐富了科學界對引文動機的認知。
盡管兩種引文動機理論都獲得大量經驗證據的支持,但是實證路線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在研究設計上無法有效地將被引對象的社會特征與其內在的知識品質相分離,即無法真正分清論文的高被引是因為被引論文的內在品質高(即高質量),還是源自于它的社會特征(如發表期刊、作者、作者所在機構的學術地位高)。在支持認可論的實證研究中,論文的高被引完全可能是由于發表期刊或作者的學術地位較高等原因所致;同理,在支持說服論的實證研究中,也無法排除權威作者、權威期刊或權威機構所產出的研究成果在內在品質上的確高于其競爭對手,高被引完全是由于論文的高質量所致。在這一意義上,現有的實證研究都未能對兩種理論提供充足有效的支持。本文試圖在實證路線上彌補這一缺陷。
2 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重復發表論文作為研究樣本,通過考察重復發表論文的被引次數差異,檢驗作者的引文動機是否符合科學社會學的普遍主義精神特質。重復發表論文作為研究樣本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有效控制論文質量這個核心變量。重復發表論文在內在品質上完全相同,那么依據普遍主義的科學規范,無論它發表在什么樣的期刊上,都應該受到相同的承認和學術認可,獲得的被引次數不會有顯著差異。
使用重復發表論文作為樣本研究引文動機的成果在國外并不多見,國內尚未有相似研究成果發表。2006年Knothe以化學期刊上的重復發表論文為案例,進行小樣本的引文分析,發現期刊的影響因子是決定論文被引次數的決定性因素[38]。2009年Lariviere等以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的4532篇重復發表論文為樣本進行引文分析,得出的結論與Knothe完全一致[39]。這兩篇文獻對本研究極具啟發性。然而這兩篇文獻采用的核心解釋變量都是期刊的影響因子,而影響因子是以期刊論文的平均被引次數為基礎,在邏輯上這一實證路線屬于自我迭代。說服論解釋引文動機的核心要素是權威或學術地位。這個要素不僅涉及被認知對象的客觀屬性,也涉及到認知主體的主觀判斷。影響因子僅能覆蓋到期刊的客觀屬性層面,無法有效體現出權威這一抽象的認知性概念。因此,現有基于重復發表研究引文動機的實證設計在變量測量方面有改進空間。
本研究通過改進解釋變量的測量方法,增加新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來考察作者的引文動機和行為特征,以檢驗規范主義或建構主義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本研究以論文的下載次數、被引次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理論上論文需要先被其他學者下載閱讀,才有機會成為被引文獻,因此,使用下載次數和被引次數共同測量論文的被認可程度。本文以刊物等級代替影響因子作為解釋變量,測量方法以是否入選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進行二元分類。雖然核心期刊的遴選指標體系包含影響因子,但還包含大量非引證指標(如被文摘轉載、獲獎、基金論文比等),而且在評選的最后一個環節會根據專家意見進行調整[40]。因此,這一評選比影響因子更能有效反映同行的主觀感知,更適宜用來研究引文動機的社會性。此外,本研究增設了重發路徑、發表性質、學科跨度三個解釋變量,檢驗它們對引文動機的影響。在數據分析上,主要使用的統計方法是非參數檢驗。非參數檢驗是在總體分布特征未知、方差未知的情況下,利用樣本數據對總體分布形態等進行推斷的統計方法。由于論文的被引次數和下載次數并不是正太分布而是冪分布,所以適宜采用非參數檢驗的統計方法。
3 數據收集與描述
本研究以圖書情報學期刊論文為樣本,通過圖書情報學界重復發表論文的被引次數差異檢驗認可論和說服論在中國學術環境下的適用性。以CNKI數據庫為數據源,選擇學科領域為“圖書情報與數字圖書館”,時間范圍限制在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按子學科分別下載題錄數據,總計198,518條;然后使用Sati軟件將下載題錄轉換成Excel工作表,再使用查重函數選出題名相同且作者相同的文獻記錄作為重復發表的研究樣本,剔除會議報道、同時作為會議論文和期刊論文的重復發表等,最終得到337篇論文,累計重復發表697次。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收集方法無法揭示出蓄意重復發表行為(Covert Duplicate Publication),即作者有意改變論文題目產生的重復發表。但是,這一缺陷對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會產生顯著影響。
如圖1所示,從10年間的發展趨勢來看,除了2006年出現異常之外,重復發表現象呈現出線性下降趨勢(y=-2.4333x+49.611,R2=0.3078),說明我國圖書情報學界的學術規范水平在不斷改善。統計數據顯示,絕大多數重復發表論文僅發表過2次(94.1%)。

圖1 圖書情報學2001-2010年重復發表論文首發時間分布趨勢
4 數據分析與討論
4.1 刊物等級與學術認可
依據科學規范的普遍主義精神特質,兩篇質量水平相同的期刊論文應該受到同等水平的學術認可。在本研究中,重復發表的論文在知識品質、作者的學術地位和作者所在機構的學術地位等維度上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別就體現在論文發表在不同的期刊上。按照規范主義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重復發表論文應該獲得相似的下載次數和被引次數。表1為M ann-W hitney U檢驗的數據分析結果,數據顯示一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的下載次數和被引次數的平均秩要顯著高于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孿生論文(p<0.001)。這一研究結果與Lariviere[41]、Peng[42]等人的研究結論完全一致,即論文發表在什么級別的期刊上決定了論文的被認可程度(Where you publish m attersm ost)。正因為如此,在量化評價主導的學術體制下,核心期刊編輯具有極為強勢的學術話語權,這正是學術界不斷暴露出有學者變相賄賂大牌期刊編輯之類學界丑聞的制度根源,如蘇州大學王堯事件[43]。由于嚴格意義上的同行評議制度在我國學術期刊界尚未普及,編輯工作對于廣大作者來說缺乏足夠的透明度,處于一種“暗箱操作”狀態,因此少數學者認為一稿多投在國內學術體制下具有正當性[44]。

表1 刊物等級與學術認可的差異檢驗
4.2 重發路徑與學術認可
如前所述,刊物等級對研究成果的被認可程度有顯著的影響。為了進一步分析發表平臺對研究成果被認可程度的影響,本研究依據首發、重發期刊是否為核心期刊,將重復發表的路徑分為四種基本類型:首發和重發都是普通期刊,首發和重發都是核心期刊,首發普通期刊重發核心期刊,首發核心期刊重發普通期刊。表2為Kruskal-Wallis檢驗的數據分析結果,數據顯示重發路徑不同會顯著導致論文的被認可度不同(p<0.001)。圖2顯示了重發路徑對論文總下載次數和總被引次數的事后成對比較,黃色線條表示節點之間的差異達到了p<0.05的顯著性水平。由圖2可知,不管是首發還是重發,只要一篇論文能夠發表在核心期刊上,它獲得的學術認可程度就會顯著高于都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論文。這一認同機制可能會促使很多首發在普通期刊的作者將自己的論文再次投給核心期刊發表,以爭取更多的學術認同。

表2 重發路徑與學術認可的差異檢驗

圖2 重發路徑與學術認可的事后成對比較
4.3 發表性質與學術認可
理性人假設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想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回報。重復發表現象的產生源于少數學者的理性逐利動機。科學文獻的指數增長客觀上增加了優秀研究成果被湮沒的可能性,“睡美人”文獻的存在就是力證。對作者來說,重復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和顯示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學術同行發現、閱讀、認可,從而提高自己的學術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以影響因子、計量指標、排名為導向的量化學術評價制度,既刺激了也默認了學術不端行為[45]。當然,重復發表有道德風險,但是這種道德風險的成本會受到制度環境壓力的調節[46]。在我國現有學術環境下,尤其在對一稿多投、重復發表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制度環境的約束力弱,導致學術不端行為頻繁出現。因此,本研究將重復發表論文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后分為兩類:首發論文和重發論文。表3為Mann-Whitney U檢驗的數據分析結果,數據顯示一篇首發論文的下載次數和被引次數的平均秩要顯著低于重發的孿生論文(p<0.001)。這說明重復發表的確有利于提高作者的顯示度和學術影響力,重復發表的收益要大于道德風險;這也反映
出我國學術界對重復發表等學術不端行為的懲戒力度不足。
4.4 學科跨度與學術認可
理論上一篇重復發表論文如果能夠同時發表在圖書情報學期刊和非圖書情報學期刊上,那么該論文的潛在讀者范圍最為廣泛,這意味著它可能被更多的學者閱讀和引用。根據發表期刊的學科屬性,本文將重復發表論文的學科跨度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圖情內(都發表在圖書情報學期刊上),跨學科(既發表在圖書情報學期刊上也發表在非圖書情報學期刊上),外學科間(都發表在非圖書情報學期刊上)。

表3 發表性質與學術認可的差異檢驗
表4展示了Kruskal-Wallis檢驗的數據分析結果,數據顯示學科跨度不同會顯著導致論文的被認可度不同(p<0.001)。圖3顯示了學科跨度對論文總下載次數和總被引次數的事后成對比較,黃色線條表示節點之間的差異達到了p<0.05的顯著性水平。由圖3可知,都在圖書情報學期刊上的重復發表論文,獲得的總下載次數和總被引次數的平均秩顯著高于其他兩類重復發表論文。這一數據分析結果和讀者范圍越大學術認可度越高的常規邏輯不符,是因為下載、閱讀、引用圖書情報學論文的人集中在學科之內,其他學科的學者對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成果并不關注。因此,在圖書情報學內的重復發表可以顯著地提高研究成果在學科內部的可見度,強化研究成果的學術認同。如果一篇論文同時發表在圖書情報學期刊和非圖書情報學期刊,那么在其他學科期刊上的重復發表并不能強化同一成果的可見度,所以跨學科重復發表的學術認可度反而低于學科內的重復發表。對那些全部發表在非圖書情報學期刊上的重復發表論文,由于受到大量非相關信息的干擾,很難受到圖書情報學界關注,可見度較低,因此被認可程度也顯著低于圖情內的重復發表。這一特征也表明圖書情報學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學科,不大關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同時其他學科也很少引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成果。

表4 學科跨度與學術認同的差異檢驗

圖3 學科跨度與學術認同的事后成對比較
5 結語
學術認可的分配機制是否遵循普遍主義的科學規范精神,是認可論與說服論對引文動機產生不同理論解釋的爭論焦點。本研究采用圖書情報學的重復發表論文作為研究對象,在嚴格控制論文質量的前提下,檢驗論文發表期刊的權威性對論文被認可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論文質量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學者在寫作時會更多地引用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較少引用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孿生論文。這種引用行為特征驗證了說服論對引文動機的理論解釋更符合客觀事實。在圖書情報學界,論文能否發表在核心期刊上決定了研究成果的被認可程度。很多學者認為,期刊的權威性取決于期刊編輯和審稿人嚴格執行的評審標準,帶有很強的同行評議性,是學術同行對期刊聲望認定的結果,因此,論文被聲望高的期刊錄用,文稿的質量也就越高,可以使用權威性作為期刊質量的參考。本文認為這一論斷并不適合于我國的學術生態,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我國的期刊審稿制度是匿名評審與三審制相結合的評審制度,與西方學術期刊實行的同行評議制度有較大區別。比如,西方學術期刊會同時請多位審稿人對文稿進行評審,從而避免專家的個人偏見,這一審稿形式在我國尚未普遍使用。其次,我國行政權力對學術有著強力的支配作用,學術主體的權威性并不是在學術市場上通過自由競爭自發形成的,而是由行政權力賦予的[47]。期刊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基本決定了刊物的權威等級。因此,在我國學術生態下使用權威性作為期刊質量的參考是不合理的。總之,論文質量的判斷非常復雜,真正的質量和知識貢獻度要經過時間的長期檢驗才能顯現。因此,有理由推定在論文質量不確定的情況下,大部分作者更容易傾向于引用權威期刊上的論文,以期刊權威性代替自己對論文質量的判斷,通過引用權威文獻增加自己研究成果的說服力和可靠性。
[1]仲理峰,時勘.績效管理的幾個基本問題[J].南開管理評論,2002,5(3):15-19.
[2]WADE N.Citation analysis:a new tool for science administrators[J].Science,1975,188(4187):429-432.
[3]朱劍.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從“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排行榜談起[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5-15.
[4]錢榮貴.核心期刊與期刊評價[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228.
[5]GARFIELD E.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J].Science,1972,178 (4060):471-479.
[6]劉宇,李武.引文評價合法性研究——基于引文功能和引文動機研究的綜合考察[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50(6):137-148.
[7]楚賓.難有同行的科學[M].譚文華,曾國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11.
[8]李沖,張麗.“洛瑞悖論”與引文分析評價學術的可靠性[J].科學學研究,2014,32(2):184-188.
[9]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M].魯旭東,林聚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65.
[10]KAPLAN N.The norms of citation behavior:prolegomena to the footnote[J].American Documentation,1965,16(3):179-184.
[11]葉繼元.引文法既是定量又是定性的評價法[J].圖書館,2005 (1):43-45.
[12]COLE S,COLE JR.Scientific output and recognition:astudyin the operation ofthe reward system in scienc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7,32(3):377-390.
[13]劉玉仙,武夷山.關于引文本質的思考[J].科學學研究,2015,33(12):1779-1786.
[14]CRONIN B.Theneed for atheoryofciting[J].Journalof Documentation,1981,37(1):16-24.
[15]DE SOLLA PRICE D J.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M].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64-65.
[16]MYERSC R.Journalcitationsand scientificeminence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0,25(11):1041-1048.
[17]SIMONTON D K.Leaders of American psychology,1879-1967:careerdevelopment,creativeoutput,and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J].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Psychology,1991,62(1):5-17.
[18]LAWANISM,BAYER AE.Validityofcitation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scientific publications:new evidence with peer assessment[J].Journalofthe American 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1983,34(1):59-66.
[19]SAHA S,SAINT S,CHRISTAKIS D A.Impact factor:avalidmeasureofjournalquality[J].Journalofthe MedicalLibraryAssociation,2003,91(1):42-46.
[20]RINIAE J,LEEUWEN T N V,VUREN H G V,et al.Comparative analysisofaset ofbibliometric indicators andcentralpeerreview criteria:evaluationof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in the Netherlands[J].Research Policy,1998,27(1):95-107.
[21]GARFIELD E,WELLJAMS-DOROF A.Of nobel class:acitation perspective on high impact research authors[J].TheoreticalMedicine,1992,13(2):117-135.
[22]布魯諾·拉圖爾,史蒂夫·伍爾加.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M].刁小英,張伯霖,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298-305.
[23]王彥雨,程志波.科學論文的意義:從傳統科學社會學解釋到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1,28(5):31-35.
[24]布魯諾·拉圖爾.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M].劉文旋,鄭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62.
[25]GILBERT G N.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into scientific knowledge[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76,6(3/4):281-306.
[26]GILBERT G N.Referencing as persuasion[J].Social StudiesofScience,1977,7 (1):113-122.
[27]DE SOLLA,PRICE D J.Istechnology historically independentofscience?Astudyinstatisticalhistoriography[J].TechnologyandCulture,1965,6 (4):553-568.
[28]COZZENS,S E.What do citations count? The rhetoric-firstmodel[J].Scientometrics,1989,15(5-6):437-447.
[29]TOLR SJ.TheMatthew effect defined and tested for the 100 most prolific economist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2009,60(2):420-426.
[30]MEDOFF M H.Evidence of a Harvard and Chicago Matthew Effect[J].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2006,13(4):485-506.
[31][42]PENG T Q,ZHU JJH.Where you publish matters most:amultilevelanalysisoffactorsaffecting citationsof internet studi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2012,63 (9):1789-1803.
[32][39][41]LARIVIEREV,GINGRASY.The impact factor'sMatthew Effect:anaturalexperimentin bibliometric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2010,61(2):424-427.
[33]閻光才.學術認可與學術系統內部的運行規則[J].高等教育研究,2007(4):21-28.
[34]喬納森·科爾,斯蒂芬·科爾.科學界的社會分層[M].趙佳苓,顧昕,黃紹林,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208.
[35]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61.
[36]FRANK M.Impact factors:arbiter of excellence?[J].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03,91(1):4-6.
[37]SELLERSSL,MATHIESEN SG,PERRY R,et al.Evaluation ofsocial work journal quality:citation versus reputation approaches[J].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10,40 (1):143-160.
[38]KNOTHE G.Comparative citation analysisof duplicate or highly related publicat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2006,57(13):1830-1839.
[40]朱強,戴龍基,蔡蓉華.研究報告[M]//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12.
[43]南方都市報.教授維權事件中的隱形腐敗更值得關注[EB/OL].[2016-09-20].http://news.sina.com.cn/pl/ch/2015-10-18/doc-ifxiwazu5569888.shtml.
[44]馬建平.一稿多投正當性的法理分析及其權利規制[J].現代出版,2012(3):18-21.
[45]BIAGIOLI M.Watch out for cheats in citation game[J].Nature,2016,535(7611):201.
[46]NECKER S.Why do scientists cheat?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2016,74(1):98-108.
[47]閻光才,岳英.高校學術評價過程中的認可機制及其合理性:以經濟學領域為個案的實證研究[J].教育研究,2012(10):7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