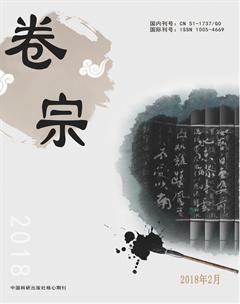《孟子字義疏證》中關于自然和必然的思想
趙陽
摘 要:戴震關于自然和必然的思想是在其“有物有則”的思想方法上建立起來的。“有物有則”強調了事物皆有其“則”,“則”就在事物之中,但此“則”并不僅僅是事物自然之分理,而是秩序的“條理”。“自然”指的是事物自然之分理,“必然”對應于“則”。根據“有物有則”的思想方法,他認為“自然”與“必然”是統一的,“自然”是“必然”的基礎。同時,“必然”是“自然”得以保存與完善的保障,戴震從“血氣心知”的得養與否和必然與同然的關系兩方面具體說明了此思想。
關鍵詞:有物有則;必然;自然;同然;
,戴震是清代考據學、哲學的代表人物。本文以《孟子字義疏證》為材料,試從其“有物有則”的方法,闡明其關于自然、必然、同然概念的思想。
一、“有物有則”的思想方法
戴震關于必然、自然的思想與其“有物有則”的思想方法緊密相關。“有物有則”出于《詩經·大雅·文王》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解釋到:“以秉持為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理,以實之于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賢圣所謂理也。”“則”解釋為可以“經常”實行,“理”解釋為“各如其區分”,需要注意并不是各物的“區分”就被稱為“理”,而是要“各如其區分”,即符合其區分。聯系戴震對于“理”的解釋:“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艤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可知,各物的“區分”只是各物的“分理”,萬物“各如其區分”應該指“條理”,要求“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這可與戴震在另一處對“有物有則”解釋互證:“ 天地、人物、事為,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在這里,“物”指的是“實體實事”,即一切現實存在物;“則”指的是“純粹中正”,這就指明了“則”不是單純的事實上的事物的“分理”,而是有標準與價值取向的,所以說“則”對應的是“條理”。
在這里,一方面,“有物有則”表明了一種“物”與“則”的必然聯系,“則”就在“物”中,“物”中必有“則”;另一方面,對于“物”的解釋,戴震也有其獨特的觀點。對于“物”,戴震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具體來說:(1)“物”,指的是實體實事,即一切存在物;(2)“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專門指人類社會的各種事件以及事物。就前者而言,需要與戴震關于“才”的思想相聯系,他認為不同的物類有不同的“才”,同時在每個“物類”之中,各個個體之間的“材質”并不是均等的。就后者而言,“物”專指人類社會中的不同事件與器物,在此層面的“則”,在戴震哲學中有其特殊的標準,戴震稱之為“同然”,下文將詳述。
最后,戴震還發揮了“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思想,這實際上是在為“性”為何要向善、合于“理義”找到根據。戴震對于“性”的內容,解釋為“血氣心知”,“血氣”指耳目鼻口的內容,“心知”對應于“心”的內容。他在解釋為什么孟子以“心之同然”證明人性之善時,一方面,以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必求其“尤美”者為依據,得出“心知”于“理義”也必求其“至是者”,這里他以“至是者”解釋“善”;另一方面,指出孟子專門以“理義”解釋“性善”,是因為理義具有“好歸之心”,由此證明“理義”不是外在于人的。這里,他的依據就在“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斷定。
二、自然、必然與同然
戴震在其“有物有則”的思想方法指導下,發揮了他對于“必然”和“自然”的思想。但是,要指出戴震關于自然、必然的思想是與其關于“理欲”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而且必然與自然也不是割裂的,也是結合在一起講的。這體現出他貫徹了他關于“一本”的思想。
“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無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
此段引文可視為戴震論“自然”與“必然”的關系的總綱。“自然”是戴震思想中最為普遍的概念。他講:“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所謂“自然之分理”,按照“有物有則”的思想,指的是每個事物本身具備的“分理”。同時,“自然”還用來指稱事物本有的功能、傾向,比如“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就“必然”而言,戴震認為:“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極于不可易之為必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人倫日用”指的是事物具有的自然之分理,將其自然之分理“推而極于不可易”,也就是“各如其分”,這就叫做“必然”。“必然”是事物分理之極致,“自然”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區分”、“分理”。但是,“自然”與“必然”是統一的,“自然”是“必然”基礎,“必然”是“自然”的完善。
問題在于為什么“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
三、自然與必然關系的證成
戴震并沒有直接回答此問題。但是,筆者根據《孟子字義疏證》的論述,嘗試從以下兩方面總結戴震對此問題的基本解釋。
一方面,戴震從其“氣化即道”的思想出發,認為人性來自于陰陽五行:“性者,分于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這是人性的基本內容。進一步,“才”是每個個體由于“性”不同得出的不同材質基礎。人性與物性不同,在人性內部,各個個體的“才”也不同。就“性”上言,“耳目鼻口”對應于“欲”,人逞其欲而不得其分就被稱為“私”;“心知”對應于“理義”,人有智愚之分,皆有其蔽。在此基礎上,戴震認為,就像對應于“耳目鼻口”的各種“聲色臭味”,如果能夠合于其性,就能養其“性”一樣;“心知”之于“理義”也是一樣的。如果不能用合于理義的事情來養“心知”,要么“蔽”越來越多,要么就被對于不平之事造成的消極情緒影響。所以,就人性而言,為了保全其“自然”、完善其“自然”,就必須以“必然”為保障。
另一方面,戴震具有批判性的指出,如果個人不能完善其“自然”之性,必然會對社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同時,戴震在此處的論證,提出了在人類社會領域,由自然達到必然,從而獲得真正的“理義”的標準,也即“同然”。在具體的事件中,如何處理個人欲求與他人的關系,戴震提出“以情絜情”的方法,也就是“反躬”自身,并最終以“天理”為標準,達到“得其平”。那么得起“平”的標準何在?戴震反對僅以一己出發來考慮,認為這樣得出的結論一定是“意見”而不是“天理”,他指出:“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同然”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天下萬世”皆認可才可稱為“同然”。所以“同然”即具有經驗論色彩,以眾人之經驗為基礎;同時,又有其本體依據,乃是以“自然之分理”為基礎的。
如果“心知”有“蔽”,就會“存乎意見”,就不能正確的認識事物之分理。在這里,戴震指出,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有可能因其“蔽”而執于一偏,而且會因為其道德高尚而自認為“得理”,從而更加不能認識到自己之“蔽”。這就是說,“理義”不只是關乎道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于心知之“蔽”的程度,所以他認為去蔽的方法在于“學”,由此來去蔽提高對“理義”的認識能力。
參考文獻
[1][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錢穆.《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