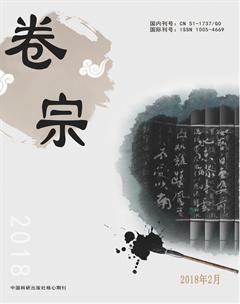我所理解的歷史人類學
摘 要:歷史人類學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有人認為它是人類學學科體系下的分支,更甚者將它視之為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合。林林總總的觀點很多,我更傾向于它是一門關于歷史的人類學研究,歷史人類學的背后是將“歷史”本身當做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本文從歷史人類學的學術史出發,將中西歷史人類學的代表性觀點梳理一番,給出“人類學本身就是歷史人類學”的論題,并在最后作出個人思考。
關鍵詞:歷史人類學 人類學 歷史學
20世紀70年代,勒高夫在《新史學》中認為:“或許是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這三門最接近的社會科學合并成一個新學科。關于這一學科,保羅·韋納稱其為‘社會學史學,而我則更傾向于用‘歷史人類學這一名稱”。21世紀初,清華大學的張小軍教授認為似乎是勒高夫“搶注”了“歷史人類學”這個名詞,并且提出了提出“歷史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他更傾向于在歷史學的框架下探討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相生相融,似乎缺少了以一種人類學的視角去看待歷史的情懷。
1 歷史人類學的發展
在梳理歷史人類學發展的關鍵時期之前,我想談談如何看待歷史人類學的定位問題。前面談到有人將歷史人類學看成是人類學的分支或者是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結合,我想這無疑是以偏概全,或者更進一步說,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至少從整體的人類學角度來看,也很難得出歷史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這一觀點。張佩國教授認為“歷史人類學并不否認對人類學學科傳統的知識傳承,但在開放的跨學科甚或“去學科化”合作中,這樣的歷史人類學應該建立起整體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模式”。這種整體性的社會科學(人類學)的觀點是值得我們去關注并推崇的,因為對人類學自身進行分科這一做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我們所熟知的經濟人類學、政治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等等,這樣的分科無疑有點“偏工具化”的嫌疑,更嚴重的甚至會對人類學和社會科學造成危害。
談及早期較有影響力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不得不提到馬歇爾·薩林斯。我們所熟知的薩林斯是一位結構人類學大師,但他早年是新進化論的倡導者,認為應該將懷特的普遍進化論和斯圖爾德的多線進化論結合到一起。并且提出“一般進化”與“特殊進化”的觀點,他與塞維斯(Elman Rogers Service)指出“文化進化一方面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由階段到階段的一般發展,另一方面是各種類型的文化的特殊進化”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歷史的隱喻與神話的現實》一書出版后,薩林斯被認為是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先行者。黃應貴認為“就人類學的發展脈絡來看,歷史人類學的形成與發展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從薩林斯建立文化如何界定歷史的研究課題開始”。《歷史的隱喻與神話的現實》一書其實從頭到尾敘述了庫克船長是怎么被夏威夷土著人所殺害的,在整本書中,薩林斯將結構與歷史結合起來看,認為應該強調結構和實踐兩者的重要性。歷史是如何發展和變化?這種變化本身又存在怎樣的結構?因為盡管歷史千變萬化,但終究可以從中看到不變的“規律”存在,庫克船長的例子表明歷史的發展既來自結構同時又影響著結構。當然,另外一位結構人類學大師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研究中也是十分關注歷史的。有一些對他的批評認為他只是一位“搖椅上的人類學家”,只注重關于結構的分析,卻忽視了歷史的重要性。但列維—斯特勞斯在其著作《結構人類學》第一卷的開篇就談論到人類學(民族學)與歷史學的關聯,并且給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很有力的回擊了那些不了解他的批評者:“民族學的目標是超越人們就自身的變異過程所制造的那些有意識的和每次都不一樣的影像,列出一張羅列所有無意識的可能性的清單;這張清單以及每一種可能性跟所有其他可能性之間或相容或不相容的關系能夠為歷史發展提供一個邏輯架構;歷史發展也許難以預見,但從來都不是任意發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名言‘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卻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歷史。”
不可否認,薩林斯的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在學術史上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但如果再往前追溯,20世紀四十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已經開始關注歷史,并且把歷史當做人類學關注的對象。在其《論社會人類學》中,有這樣一段話值得我們思考:“我認為社會人類學屬于人文科學而不屬于自然科學……在我看來社會人類學更像是歷史學研究的某一個分支——社會歷史,以及史學與敘事史、政治史相對應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并且史學和社會人類學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他生活的大背景是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導下的英國,功能主義或者是結構功能主義已經為學者奠定了一個范式,他們力圖尋找人類生活的共通點。但是普理查德認為人類學不在于“發現”,而在于如何“理解”。前面提到以一種整體科學看待人類學,這邊就不得不提到法國的年鑒派史學,他們對待歷史一直倡導以一種“整體史觀”,這種方法對人類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無論是薩林斯、列維·斯特勞斯還是普理查德等人,他們的研究都表明,在人類學的研究中將歷史作為關注對象是必不可少的。在回顧了國外歷史人類學發展的幾個代表性觀點后,那么,在中國本土的歷史人類學又有怎么樣的發展呢?中國本土對于歷史人類學的重視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我們所熟知的華南學派為代表。美國耶魯大學的蕭鳳霞、香港科技大學的科大衛、中山大學歷史系的陳春聲等一批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通力合作,對中國的珠三角、廣東等地區進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通常這也被成為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開始。但是在此過程中,也有一些歷史學者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出現一些偏頗。他們平常的歷史研究主要在于翻史料、讀文獻、整理等書齋工作,而在人類學的田野技術被他們接受后,仿佛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可以利用人類學的田野技術到田野中去,找一些現實存在的史料(如碑文、家譜等實際性材料),然后回到書房整理書寫,他們認為這樣就是歷史人類學的研究,這其實是對歷史人類學的一個誤解。而蕭鳳霞的總體方向是正確的:歷史人類學應該關注“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利用田野資料來彌補歷史文字記錄的不足,通過了解當地人的社會生活去看待這個地方的歷史是如何被建構的,甚至是如何影響到國家層面上的發展的。拿王銘銘的《逝去的繁榮》為例,其副標題為“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足以窺見其歷史人類學的足跡。書中通過對泉州城的描寫,引發讀者的思考:繁榮從何而來,又是如何逝去的?泉州城的“逝去”是否能夠反映地區的發展,甚至是國家的歷史變遷問題?
二、人類學本身也可以稱為歷史人類學?
對于歷史人類學來說,如果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可以把眼光放長遠一點,而并不僅僅局限于前文提到的中外發展史。我們始終推崇“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研究”這樣的說法,但現實中人類學似乎總逃離不了關于現代社會科學的影子。這種人類學存在著兩個大的發展階段,一個是以古典進化論、傳播論為代表的古典人類學階段,另外一個是存在不同理論流派的現代人類學時期。那么如果說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研究,那么可能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早就存在人類學。也就是說在現代意義上的人類學語境之前,存在著古人類學階段,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他者的研究是不是意味著從人類出現開始就有?如果從文字記載來看(以中國為例),無論是較早的《山海經》、《穆天子傳》還是歷朝歷代史書的編纂者,都存在著對他者的認知與理解,從這一點上來看,他們也可以稱作早期的“人類學家”。現在我們把歷史學和人類學相區分開,是否應該回顧歷史的起點,看到兩者本就是相生相融的一體?歷史可能并不是純粹的自身描述,還應該看到對于他者的認知與理解,穆天子巡游尋找西王母,史書中對非我族群的敘述等等都體現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痕跡。從這些重視描述歷史與現實生活,同時又對外族群體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的歷史中,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形式?再看這種經驗主義時期之后,西方教皇統治時期,宗教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個時期的“他者”是圍繞神論展開的,他們以宗教為界,宗教體系之外的就被認為是不同于自身的他者,并且形成一種文明中心論的時代。在這之后就是為我們熟知的文藝復興的出現,追求一種自由的狀態,要求擺脫教皇的封建統治,并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樣的人類學歷程中的“他者觀”都帶有歷史分析的傾向,或者說傳播論、進化論也是存在歷史的取向。從以上的觀點來看,人類學本身就是一種歷史人類學。
三、個人思考
歷史人類學并不是簡單的在人類學研究中加入史學的視角,也不是在史學的學習中融入人類學的知識,而是要把歷史本身當做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用人類學的視角去研究歷史,這樣的方法是區別于歷史學的。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學可能更多的是在重構一種歷史,而重構的歷史還不全面,就是所謂的歷史表象,王朝更迭式的敘述。而人類學的研究恰恰是想還原更加豐富的歷史內涵,這是一種不一樣的視角。就拿王朝更迭的例子來說,我們所熟知的“黃袍加身,陳橋兵變”,公元960年,趙匡胤在河南陳橋發動兵變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就這一事件,歷史可能關注的是時間、地點、人物、發生了什么事情。而人類學關注的,可能就要問為什么是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發生這樣的事件,為什么會有趙匡胤這樣的人物的出現等問題。這也許就是歷史人類學所追求的,歷史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歷史變化發展的背后又是怎么樣的。王銘銘認為“與其他學問一樣,歷史人類學須尋找趨近現實的路徑。而同時考察被研究者生活方式、觀念形態及其遭到的挑戰(既可能來自內部,也可能來自外部)是趨近現實的好路徑。其實歷史人類學家要做的,不是處理學術爭論,而是為歷史的理解提供獨到的洞見”這樣的觀點也同樣強調了應該將“歷史”作為人類學研究對象,這才是我們所說的歷史人類學。
參考文獻
[1]勒高夫,諾拉等編.新史學[M].姚蒙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2]張小軍,歷史的人類學化和和人類學的歷史化——兼論被史學搶注的歷史人類學[J].歷史人類學學刊,2004,1(1).
[3]張佩國,作為整體社會科學的歷史人類學[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
[4]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5] 馬歇爾·薩林斯.歷史的隱喻與神話的現實[M]. 藍達居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黃應貴.歷史與文化——對于歷史人類學之我見[J].歷史人類學學,2004,2(2).
[7]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一卷[M].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8]埃文斯·普理查德.論社會人類學[M]. 冷鳳彩譯,梁永佳校.世界圖書出版社,2011.
[9]王銘銘.逝去的繁榮——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0]王銘銘.我所了解的歷史人類學[J].西北民族研究,2007,2.
[11]張佩國.作為整體社會科學的歷史人類學[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劉張磊(1992—),男,漢族,江蘇南通市人,研究生,法學碩士,單位: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 研究方向: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