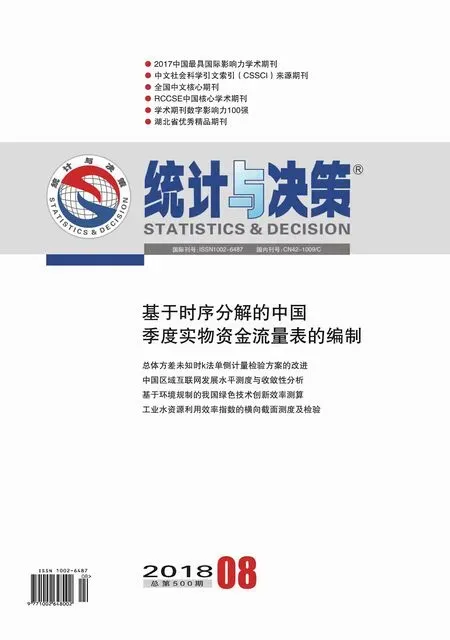基于環境規制的我國綠色技術創新效率測算
岳鴻飛
(北京師范大學 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0 引言
綠色技術作為兼顧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的主要抓手,成為國家經濟綠色發展與轉型的重要驅動,自然資源的公共品屬性與生態環境的負外部性決定了綠色技術創新無法通過單一的市場機制得以實現,需要政府給予科學有效的環境規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嚴格的環境規制在提高全社會總福利的同時,必將以廠商生產成本的提升為代價,進而降低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另有研究表明:企業在環境規制的影響下會更容易將研發經費投入到非綠色技術領域的研發,從而造成資源和環境的更大浪費與破壞。20世紀90年代著名的“波特假說”被正式提出。“波特假說”從動態的角度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具有創新補償效應,即適當的環境規制強度可以補償規制成本,進而促進科技創新。
為探究當前我國環境規制是否促進了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哪種規制方式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更加顯著,本文基于松弛變量的方向性距離函數(SBM-DDF)測算我國2005—2014年省級層面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并以此避免傳統方向距離函數的徑向性和導向性問題;同時,圍繞行政型環境規制、市場型環境規制,結合各地區國際化開放程度、地區企業所有制結構、地區教育資源稟賦與科技整體水平等因素實證分析了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1 研究方法與模型設定
1.1 綠色技術創新效率的測算
本文通過SBM-DDF方法,以我國30個省(區、市)為研究對象。令x為各省(區、市)科技創新活動的N種投入變量;y表示所研究問題的M種期望產出,,;b表示所研究問題的K種非期望產出因此有表示第i個地區t時期的投入產出向量。再令(gx,gy,gb)為方向向量為投入產出的松弛向量。因此,可基于松弛測度構造非徑向性、非導向性的方向距離函數(SBM-DDF),其中第i個省(區、市),第t時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公式及限定條件如下:

本文以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各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作為投入變量;以技術專利數、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期望產出變量;以單位GDP能耗和國內重點監測的主要污染物:廢氣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為非期望產出,以此科技創新的綠色屬性。
由于公式(1)是從無效率角度進行衡量的效率指標,即該值越大,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就越低。因此,當方向向量時,令綠色技術創新效率(GTIEP)為:


1.2 指標選取
1.2.1 環境規制類變量
環境規制變量表示一個地區對當地環境的治理強度。根據環境規制方式的不同,環境規制可分為行政型規制、市場型規制等。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的環境規制多為行政型方式;20世紀70至80年代,伴隨著市場化進程的開展,市場型環境規制開始成為行政型規制的重要補充,并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研究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以行政型環境規制與市場型環境規制作為分類依據。
在行政型規制方面,選取各地區“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總額”(TSIE)為代理變量,即環保設施同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的投資額度,可用以表示在項目事前、事中和事后對環境進行規制和干預的強度。在市場型規制方面,選取各地區“重點監控企業排污費征收額”為代理變量(ESC)。市場型環境規制主要通過稅費與排污許可證等工具實現規制。我國排污費征收制度在國內實施時間較長,1979年的《環境保護法(試行)》就規定了在我國實行征收超標準排污費制度,且多年來政策相對穩定。考慮數據的可得性與可靠性,本文將以“重點監控企業排污費征收額”為相關代理變量。
1.2.2 其他影響因素
除行政型規制與市場型規制外,本文從國際化開放程度、企業所有制結構、地區教育資源豐裕度和科技整體發展水平四個方面考慮綠色技術創新的其他影響因素。
國際化開放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源于國外資本與技術的大量涌入。對于綠色技術創新來說,一方面外商投資可以短時間內彌補國內科技創新環境的資金缺口,另一方面其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會更大范圍地影響當地社會和內資企業的技術進步。此外,國際貿易在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更會通過貿易壁壘倒逼中國企業的綠色技術改造。然而,根據“污染天堂”假說,外商企業也容易將污染密集型的產業集中到我國環境標準較低的地區,進而阻礙當地的綠色發展和綠色技術創新。本文選擇各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作為該項指標的代理變量。
企業所有制結構。企業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其所有制屬性的不同將影響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中的表現。國有制企業通常擁有更多的優勢資源與市場份額,有研究表明,大型國有企業規模生產對創新投入的補償優勢與技術溢出效應將是其他市場主體不可替代的。然而,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企業,雖資本實力與市場規模不及國有企業,但其靈活的體制與運營模式極大地推動了企業的自主創新。本文以各地區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額與私營工業企業資產總額比值(SPTA)作為代理變量,以表征地區企業的所有制屬性。
地區教育資源豐裕度。科技創新活動的另一重要主體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與科研院所作為人才與知識的主要匯集地,是知識存量水平的集中體現,任何科技創新活動都需要在一定的知識存量上得以實現。本文以各地區“每十萬人口平均高等學校在校生數”(HLPT)為指標,表示當地的教育資源豐裕水平。
地區科技整體發展水平。地區科技整體發展水平體現了該地科技創新活動的大環境。綠色技術創新作為整個科技創新活動的子集,其從研發、到中試,再到最后投產,每個環節都需要科創環境的支持。本文使用技術市場成交額指標(TMT)反映地區的科技整體發展水平。
1.3 面板數據模型的構建
本文對我國30個省區(不包括西藏自治區),2005—2014年間的數據展開研究,通過上述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構造如下面板模型,并通過取對方式消除量綱:

其中,GTIEP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lnTSIE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行政型環境規制強度;lnESC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市場型環境規制強度;lnFDI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國際化開放程度;lnSPTA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企業所有制結構;lnHLPTit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地區教育資源豐裕度;lnTMTit表示第i省(區、市)第t期的地區科技整體發展水平;αit代表省份決策單元的固定效應;β'=(β1i,β2i,β3i,β4i,β5i)表現各影響因素對i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程度。
模型(3)在滿足時間一致性的基礎上,其截距項與各影響因素的斜率系數將隨著地區的不同而各有不同。除此形式外,伴隨以下兩種假設另有模型(4)和模型(5):
假設1:斜率相同,但截距不同,模型形式為:

此時,各地區及各影響因素的初始水平差異將體現在截距項 ai中,其中 β'=(β1,β2,β3,β4,β5)的取值不再因地區不同而不同,即此時各影響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具有地區一致性。
假設2:截距和斜率均相同,即模型形式為:

此時,各地區及各影響因素初始值對模型的形式與系數不具有差異性,可將樣本視為多時期截面數據樣本。其中,a僅作為固定效應體現,不再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
具體選用何種模型將使用Hausman檢驗,通過構造兩個假設檢驗的F統計量,并利用協方差分析最終確定模型形式。
1.4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各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技術專利數、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均源于2006—2015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地區生產總值源于2006—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廢氣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源自2006—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單位GDP能耗由2006—2015年各地區統計年鑒計算而來。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總額,重點監控企業排污費征收額來自2006—2015《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報》;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額與私營工業企業資產總額比值由2006—2015《中國統計年鑒》計算而得。地區教育資源豐裕度指標選自2006—2015《中國教育統計年鑒》。技術市場成交額指標源自2006—2015《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其中地區GDP以2005年為基期,并按生產總值指數平減,部分數據使用了wind數據庫作以補充和查驗。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2.1 綠色技術創新效率測量結果與分析
本文基于SBM-DDF方法,通過matlab軟件測算了2005—2014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并按東部11省、中部8省、西部11省進行了分組對比。測算結果參見表1。
從全國總體水平來看,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平均效率在十年間呈現穩步上升趨勢,指標從2005年的0.8364逐年提升到2014年的0.8737,這體現了我國在近十年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不斷進步。“十一五”“十二五”時期國家明確了國內生產方式向集約與環境友好型轉變的戰略發展方向,并提出要注重科技創新在綠色轉型當中的核心作用。該測算結果驗證了我國在該時期綠色技術創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從區域間比較結果看,東、中、西部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均呈現上升態勢,且東部地區的效率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地區略優于西部地區。全國十年平均效率值在0.9以上的7座城市均在東部地區,其中海南、天津、北京位列前三名,效率值依次為0.9988、0.9745和0.9691。從變化的過程看,東部地區的十年平均效率值提升幅度最大,由2005年的0.8462增長到2014年的0.9150;中部地區其次,由2005年的0.8162提升為2014年的0.8515;西部地區則無太大變化,增長幅度僅為0.0067個效率值。科學技術的創新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東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各類服務于綠色技術創新的要素在該區域匯集,這使得其綠色技術創新效率領跑于全國其他地區。

表1 2005—2014年中國各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效率
從區域內比較來看,東部地區的不同省份(區、市)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差異較大。其中海南的十年效率均值0.9988比山東的十年效率均值0.6980多出0.3008個效率值。海南、天津、北京、福建、上海、浙江、廣東、江蘇等省份均在部分年份出現效率值為1的情況,而遼寧、河北、山東的效率最低年份則分別為0.7195、0.7053和0.6773,效率值嚴重落后。近年來,北京、天津等主要城市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力度,將諸多傳統制造業產業外遷。相比較而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內部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差異并不明顯,其十年均值效率跨度僅為0.1934和0.1452個效率值。
此外,從測算結果中不難發現,排在各地區前列的省份如東部地區的海南(0.9988),中部地區的江西(0.8999),西部地區的青海(0.8942),均為生態資源大省,而在各地區排名靠后的省份例如山東(0.6980)、河南(0.7455)、山西(0.7065)、陜西(0.7804)、四川(0.7769)、內蒙古(0.7490)等均為以煤炭為主的礦產資源主產省。這一結果表明以礦產資源為支柱產業的省份,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其傳統資源消耗式的增長方式,并在綠色技術創新方面表現出較明顯的滯后性。這也印證了學界常提到的“資源詛咒”或“荷蘭病”效應。
2.2 面板數據選擇與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東、中、西部地區均應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通過計算F統計量并進行協方差分析,三組地區采用模型(4)即變截距模型,見表2。

表2 協方差檢驗結果
在確定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的基礎上,本文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三大地區的面板模型均具有較好的擬合優度,且絕大多數指標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實證結果見表3。

表3 環境規制等影響因素對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2.2.1 行政型環境規制的影響
實證結果表明,行政型環境規制對不同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明顯不同。在東部地區,行政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0.001581***)。在中部地區,該項因素的影響效果為負向(-0.020601****),即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綠色技術創新。對于西部地區,行政型環境規制對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并不顯著。
東部地區較中西部地區而言,工業化進程發展較快,且人口活動密集,經濟生產活躍。相對集中的工業化生產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了東部地區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行政型環境規制在東部地區最為嚴格,且實施效力最大。因此,效力較大的行政規定使東部地區的環境規制達到了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程度。就綠色技術本身而言,東部地區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的要素最為充沛,其創新成本相對低于中西部地區,這也使得行政型環境規制更容易在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發揮促進作用。
對于中部地區,由于其長時間處于經濟追趕狀態,當地經濟發展仍以開發建設為主,這使得當地行政型環境規制本身并沒達到可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程度。如此前文獻綜述所言,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必將提高生產者的生產成本,進而減少企業用于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阻礙企業的自主研發與科技進步。此外,東部地區嚴格的環境規制,使得傳統污染型企業“內遷”或“西遷”,以四川為例,全省中輕度污染型企業由2000年的20.96%增長到了2006年的25.95%。較東部、中部而言,西部地區本身的經濟發展與科技水平相對滯后,其工業化發展程度不高,當地綠色技術創新的訴求也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因此當地環境規制力度較弱,且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
2.2.2 市場型環境規制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型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均表現出了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對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0.31613****)大于對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0.016185***)。與此同時,市場型環境規制對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也產生了較為顯著的影響,但該影響效果則表現為負向阻礙作用(-0.042088***)。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市場型環境規制比行政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果更加顯著。市場型環境規制通過排污稅費等方式將規制與產品產量或排污量掛鉤,其規制成本相對更加直接地體現在生產過程中。東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高于中部地區,因此市場型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其對中部地區的作用。而其對西部地區的負向作用,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和分析:第一,市場型環境規制同行政型環境規制的作用機理一樣,通過排污費或排污權交易等方式提高生產成本,進而實現環境規制。規制成本的追加削減了企業科技創新的投入經費,因此抑制了綠色技術創新。第二,根據國內部分學者得出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U”型關系理論,我國的市場型環境規制力度還沒有達到可以促進綠色技術的強度,仍處于“U”型底部的左端,進而呈現負向影響。第三,綠色技術創新需通過能耗、污染物減排等指標得以體現,這使得綠色技術創新與一般的技術創新相比需要更長的作用時間和影響周期,因此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果也相對滯后出現。
2.2.3 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并沒有給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帶來顯著影響。這一方面因為東部地區本身的創新資源相對豐富,另一方面也說明發達國家并沒給我國帶來直接的綠色技術外溢與輸出。然而,外商直接投資卻給中部地區帶來顯著的促進作用(0.006622*)。這說明外資的引進補充了中部地區相對不足的資金缺口,進而有助于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結果還顯示,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受到了外商投資的負面影響,這表明外商在西部地區仍以項目開發建設為主,并不太注重綠色技術的創新和現有技術的改造。
企業所有制結構并未給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帶來顯著影響,但該因素卻對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0.002947*)。對中西部地區而言,企業所有制結構和體制問題并沒有成為影響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相對匱乏的創新資源才是影響當地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對于創新要素充分的東部地區,創新主體的活躍性則成為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相比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具有更加靈活的體制且在創新活動中表現出更為活躍的自主行為。地區私有企業比重越高,當地創新活動就越活躍。因此國有資產與私有資產比重對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負向影響。
地區教育資源豐裕度指標對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均表現出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說明高校資源與知識存量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東中部地區擁有巨大的綠色發展與技術改進的需求。而該指標在西部地區則表現為負向作用,這也符合西部地區教育資源相對貧瘠,綠色技術創新任務并不緊迫的實際情況。地區科技整體發展水平指標在東中西部均表現出了較明顯的正向作用,即地區科技整體實力越強,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越活躍。這也從邏輯上印證綠色技術創新作為技術創新的一個子集,離不開科技整體環境的支持與帶動。
3 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從2005—2014年,各省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在穩步提升;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且在十年間增幅最大,海南、天津、北京、福建、上海、浙江、廣東、江蘇等省份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均在部分年份出現前沿面上,但在東部地區的內部,綠色技術創新效率也存在嚴重不平衡性。中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效率的十年平均值略低于西部地區,其區域內部跨度較大。西部地區十年來增幅較小且區域內部差異不大。同時,以礦產資源型省份的綠色科技創新表現出較明顯的滯后性;以生態資源為主的省份則在綠色科技創新領域領跑全國。
從影響因素看,第一,行政型環境規制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創新要素充裕的東部地區才會對綠色技術創新起促進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區的影響并不顯著甚至產生抑制作用。第二,市場型環境規制比行政型規制所產生的影響更加顯著,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均表現了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且因東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高于中部地區,市場機制性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西部地區的環境規制尚未對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起促進作用,甚至因規制成本的原因給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帶來阻礙。第三,創新要素是抑制中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關鍵,通過引進外資等方式可以促進當地的綠色技術創新。第四,企業所有制結構影響著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更為活躍的表現。第五,高等院校等教育資源是東部和中部地區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第六,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的科技整體水平緊密相關,地區科技整體水平的提升將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第七,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與工業綠色轉型的訴求尚未十分迫切。
參考文獻:
[1]Acemoglu D.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2,69(4).
[2]Fukuyama H,Weber W.A Directional Slacks:Based Measure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J].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2009,43(4).
[3]Jaegul L,Francisco M,Veloso D.Forcing Technological Change:A Case of Automobile Emissions Contro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US[J].Technovation,2010,(4).
[4]Wong S.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Knowledge Sharing and Green Innov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China[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3,22(5).
[5]景維民,張璐.環境管制、對外開放與中國工業的綠色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14,(9).
[6]余慧敏.環境規制對綠色創新績效的影響[J].財經研究,2015,(2).
[7]李婉紅,畢克新,曹霞.環境規制工具對制造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以造紙及紙制品企業為例[J].系統工程,2013,31(10).
[8]尤濟紅,王鵬.環境規制能否促進R&D偏向于綠色技術研發?[J].經濟評論,2016,(3).
[9]張成,陸旸,郭路.環境規制強度和生產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11,(9).
[10]李斌,彭星,歐陽銘珂.環境規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與中國工業發展方式轉變[J].中國工業經濟,2013,4(4).
[11]童偉偉,張建民.環境規制能促進技術創新嗎——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再檢驗[J].財經科學,2012,(11).
[12]張杰.中國制造業企業創新活動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江蘇制造業企業問卷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7,(6).
[13]張江雪,蔡寧,楊陳.環境規制對中國工業綠色增長指數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