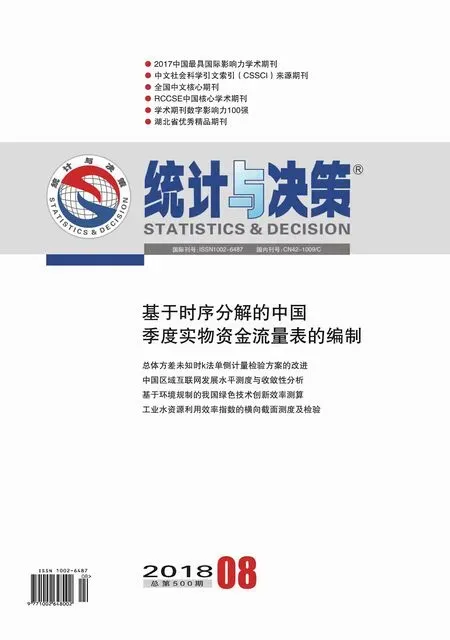開放經濟下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研究
李冠杰
(咸陽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咸陽 712000)
0 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在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日益加重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受關注。尤其是長期以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給我國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由于生態環境屬于公共資源,單靠市場機制顯然是無法解決環境問題的,因此必須通過政府的“有形之手”加強監管。環境規制是政府為了應對環境污染行為而做出的調節手段。通過環境規制,可以抑制污染環境的行為,也可以刺激和引導綠色生產,從而優化環境質量。而在開放型經濟下,地區之間的聯動越來越強,一個地方的環境規制可能對周邊環境產生作用,這就是環境規制對環境的外部性影響。本文正是以此為切入點,研究我國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
1 計量模型、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1.1 變量指標選取及數據樣本說明
為了盡量擴大樣本容量,以提高分析精度,本文采用大樣本的面板數據。由于指標獲取渠道來源并不多,因此本文通過搜集、整理,最終決定選取2010—2016年我國大陸地區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其中西藏自治區因為數據缺失較多,故予以略去。本文涉及的有關變量指標及數據樣本說明如下:
第一,主要研究變量:環境污染。衡量環境污染的介質主要有大氣、水體和固體污染物三種。為了綜合分析出環境規制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在測算環境污染指標時,采用大氣污染指數、水環境質量指數和污染源監測指數三者的平均數表示。其中,大氣污染指數采用國家公布的API指數來代替;水環境質量指數采用地下水水質超Ⅳ類比例、主要地表水體劣Ⅴ類斷面比例兩者的均值來綜合表示;污染源監測指數采用國家公布的PMI指數來代替。為了體現各省級單位的相關指標,采用各省級單位的省級城市對應的指標來代替,相關數據通過國家環保局網站以及其他網站搜集得到。
第二,主要解釋變量:環境規制強度。對于環境規制強度指標,國內外已有大量的學者進行設計和測算,這在前面的相關研究回顧中已經提到。即使如此,仍鮮有學者能充分考慮到環境規制中的潛在性問題,包括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強度等方面。
第三,控制變量。如果單從環境規制強度這一個變量去解釋環境污染是顯然不夠的,因為還有許多外在因素與環境污染存在較大的聯系,尤其是涉及到經濟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納入了以下幾個控制變量: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反映當地的綜合經濟發展規模,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②產業結構特征,主要反映當地的工業企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采用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③對外貿易水平,主要反映在外向型經濟背景下通過對外貿易的擴大,是否也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采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④創新發展水平,主要反映一個地區通過科技創新發展,是否會降低當地的環境污染程度,從而提高環境質量,創新發展水平采用當地的R&D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所有指標均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的相關數據得到。
1.2 計量模型構建
本文借鑒薛福根(2016)的研究方法,擬采用空間動態模型進行分析。
空間動態模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空間滯后模型(SAR),另一類是空間誤差模型(SEM)。兩類模型的數學形式如下:
(1)SAR模型

其中,y為因變量,ρ為空間滯后系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X為自變量集合,β為自變量對應的系數向量,ε為隨機誤差項。這里需要對空間權重矩陣W進行細化說明。對于這個矩陣,有學者采用0-1法,也有學者采用歐氏距離法,為了簡便起見,本文采用前一種方法。設wij是W中的一個元素,如果地區i和j之間存在公共邊界,那么有wij=1;如果不存在公共邊界,那么有wij=0。特別地,約定地區wii=1,且假設海南省與廣東省有公共邊界。引入前面提到的研究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得到相應的空間動態模型擴展:

(2)SEM模型

其中,η為帶有空間關聯性的誤差項,λ為空間誤差系數,其余變量同上。引入前面提到的研究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得到相應的空間動態模型擴展:

其中,EPO表示環境污染綜合水平;REGU表示環境規制強度;PGDP、STRU、OPEN和TECH分別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特征、對外貿易水平和創新發展水平;α0~ α6,β0~ β6均為待估計系數;i和t分別表示地區和時期。
2 環境規制強度的指標設計及測算
環境規制強度的測算方法有很多,如可采用污染減排支出與企業特征來估算行業的環境規制強度,也可采用產業增加值、成本與從業人數去除污染減排支出來估算相對的環境規制強度。但考慮地區產業結構的不同,需要建立一個調整的指標來測算環境規制強度(REGU):

其中,REGUst表示s地區t年份環境規制強度;Sst表示s地區t年份單位產值的污染減排成本;Sst表示經過產業結構調整的單位產值的污染減排成本;Pst表示污染減排支出;Yst表示生產總值;(Pit/Yit)表示第i個行業單位產值的污染減排成本,(Ysit/Yit)表示i行業占s地區產值的比重,也就是相應的權重;s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i代表行業。
污染減排投入主要包括企業的投入和政府的環境支出。為了消除不可比的影響,借鑒式(5)單位污染物所需治理投入的思想,構建一個修正的環境規制強度(REGU’):

其中,SIst表示工業污染減排投入的無量綱化結果;Ist表示環保投資、工業污染治理投資與三廢治理費用的總和;Iˉt表示全國各地區工業污染減排投入的均值;TEst表示多種污染排放加總的綜合污染排放水平;SEsjt表示第j種工業污染物排放的無量綱化結果,采用s地區t年份第j種工業污染物排放量與全國各地t年份第j種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均值的比重來衡量;其他字母含義同上。
根據歷年《中國環境年鑒》,整理我國30個大陸地區(西藏除外)和行業污染減排支出相關數據,采用上述污染減排投入測算方法,測算我國各省份修正的環境規制強度的排名及變動情況,具體數據見表1。

表1 2010—2016年我國各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的排名及變動情況
由表1可以看出,我國30個地區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修正的環境規制強度排名變化情況。同一個地區不同年份的環境規制強度排名差距相對較大的省份有黑龍江、廣西、福建、海南等地區;同一個地區不同年份的環境規制強度排名差距相對較小的省份有山西、貴州、陜西等地區。
3 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分析
3.1 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檢驗
首先,通過MATLAB 7.1軟件附帶的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程序,分別根據式(2)和式(4)進行回歸,并將結果進行整理,得到表2。
根據表2,對比SEM模型和SAR模型的回歸情況,無論是從校正后的擬合度還是極大似然值,都是SAR模型較高,而且空間計量模型特有的指標LM值和R-LM值也使SAR模型更加顯著。由此,本文認為SAR模型得到的回歸結果更加優越。
(1)環境規制強度對當地環境污染的影響。環境規制強度變量REGUit的系數值為-0.69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由此可見,地方環境規制強度與當地的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有利于減少當地環境污染。這也表明,一個地區實行環境規制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地的環境污染,從而有助于優化生態環境。這一回歸結果與環境規制的初衷是相一致的,環境規制作為政府的一項社會性規制手段,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對企業和社會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降低環境污染,從而弱化其外部不經濟性。
(2)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環境規制強度的空間作用變量W×REGUit的系數為-0.20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就表明,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存在較為顯著的外部性,即一個地區實施環境規制政策,可以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周邊地區環境污染帶來一定的減弱作用,從而對周邊地區環境質量的提升帶來正向外部性。

表2 兩類空間動態模型回歸結果
3.2 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外部性影響的“U型”檢驗
就像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的影響可能存在“U型”特征一樣,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可能也存在“U型”特征。為了從經驗上佐證這一點,本文基于式(3)、式(4),引入二次項變量,拓展為以下模型:
(1)SAR模型

仍舊采用MATLAB 7.1軟件附帶的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程序,分別根據式(7)和式(8)進行回歸,整理結果得到表3。

表3 關于“U型”檢驗的兩類空間動態模型回歸結果
從表3的SEM模型和SAR模型的回歸效果比較來看,SAR模型的回歸效果仍略優于SEM模型,因此仍舊認為SAR模型在解釋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外部性影響的“U型”關系上更加有力。
(1)環境規制強度對當地環境污染的影響再檢驗。從表3的環境規制強度變量的系數變化可以看出,一次項REGUit的系數為-0.277,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同時二次項(REGUit)2的系數僅為-0.006,且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環境規制強度對當地環境污染的影響不存在“U型”特征,且似乎更加符合線性特征。從回歸結果來看,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能顯著地帶動當地環境污染減少。由此可見,對于一個地區而言,無論環境規制強度達到什么程度,只要該地區能夠實施環境規制,就能促進該地區的環境污染有所降低,從而帶動環境質量優化。即使環境規制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對當地環境污染的削弱作用存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從回歸經驗也可以看出,這種削弱作用也并不會被打破。
(2)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再檢驗。引入二次項后,環境規制強度的空間作用變量系數由表2的負值變為正值,同時二次項變量W×(REGUit)2的系數為-0.04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由此表明,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確實存在“U型”特征,且“U型”開口向下。
對于這種“倒U型”曲線影響效應,本文給出以下解釋:
(1)當一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較小時,該地區的環境規制可能并不會引起周邊地區對環境規制的重視程度提高,但是由上文的分析又可以知道,該地區只要實施環境規制,就有利于本地環境污染減少。這其中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企業被責令整改、關停或被迫遷出。于是,對于這些企業而言,一個較為穩妥的方法便是技改,而另一個就是遷移到周邊地區,特別是業務分散布局在多個地區的這類企業,更有傾向將業務遷移到周邊的“大本營”。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導致遷入地的環境污染得到加重。這個角度就解釋了對于低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具有一定的“負外部性”。
(2)當這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持續提高時,周邊地區的政府也會越來越感覺到該地區實施環境規制的有效性,于是也會逐步模仿實施這種策略,由此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所在地區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發展,積極走綠色發展之路,于是環境污染也會有所減少。所以,當一個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達到一定的臨界值并繼續提升時,將發揮出輻射帶動效應,有效刺激周邊地區增強環境規制,從而減少環境污染。可見,從這個角度便能解釋對于高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的論斷。
4 結論
本文考慮了開放型經濟下區域間經濟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的趨勢,以2010—2016年我國大陸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為樣本,通過控件面板數據計量模型的方法,實證檢驗了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研究結論如下:第一,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內部性影響。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能顯著地帶動當地環境污染減少,而且即使環境規制對當地環境污染的削弱作用存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這種削弱作用也并不會被打破。第二,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與內部性影響不同,環境規制強度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影響卻存在“倒U型”規律,低環境規制強度在短期內反而會加劇周邊地區環境污染,而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對周邊地區環境污染的影響便會逐步轉向削弱。
參考文獻:
[1]Becker R A.Air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Under the Clean Air Act:Evidence From the PACE Survey[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5,50(1).
[2]Cole M R,Fredriksson E P.Endogenous Pollution Havens:Does FDI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08(1).
[3]Cole M A R.Elliott J R.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ost Jobs?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the UK[J].The B.E.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7,7(1).
[4]程都,李鋼.環境規制強度測算的現狀及趨勢[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38(8).
[5]申偉寧,福元健志,張韓模.京津冀區域收入差距與環境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7,31(11).
[6]郭慶賓,劉琪,張冰倩.環境規制是否抑制了國際R&D溢出效應——以長江經濟帶為例[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6,25(12).
[7]薛福根.產業結構調整的污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空間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湖北社會科學,2016,(5).
[8]韓先鋒,惠寧,宋文飛.環境規制對研發技術進步的影響效應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4,(12).
[9]李冠杰.“協同共生”:區域生態環境治理新范式[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