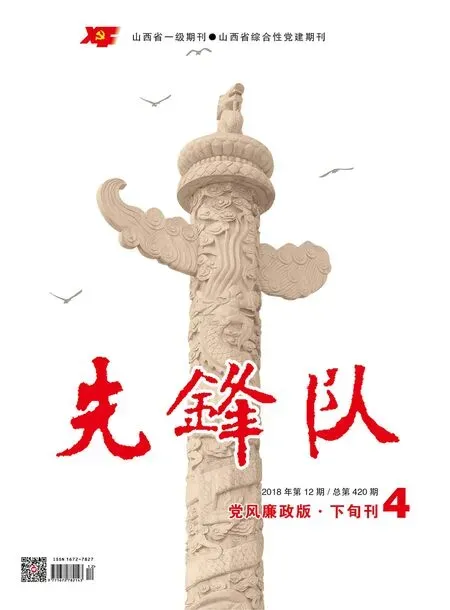一部厚重自信的史冊
——評《中國古代監察法制史》
■ 馮秋穎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系統性、完整性、持續性都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的。它所確認的監察制度建構、多元的監察機關體系、廣泛的監察法律規范,都鮮明地表達了中華民族在運用法律約束權力、規范權力運行上的理性思維與智慧。
一
讀何兆武《上學記》,里面都是西南聯大的老教授們講課的故事,其中有一章提到史學大家雷海宗,說道:“雷先生講課真有意思,好像說故事一樣。”
其實,真正的大家講歷史,往往不是沉浸在故紙堆里引經據典、照本宣科,而是信手拈來幾個故事,娓娓道來、啟發聽者。
比如張晉藩老先生,他是中國法制史學界的元老,今年已經88歲了,最近接受記者采訪,記者請他介紹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緣起。張老笑了笑,隨口講了一個故事:
戰國時期,齊國官員淳于髡與齊威王一起飲酒,貌似酒量還不錯,齊威王好奇地問道:“先生能喝多少才醉?”他回答:“一斗也醉,十斗也醉。”齊威王更加好奇,他解釋說:“大王賜酒,御史在旁邊,我哪敢多喝,一斗就醉了。”
這個故事記載于《史記》,張老為何要在回答監察制度緣起的時候,專門講這個故事呢?
讓我們把視線移到戰國。
戰國兩百余年,列國并起,七雄割據,混戰不休,國君求賢改制,以期富國強兵,名士縱橫捭闔,學者百家爭鳴。中國的官僚體系也隨之發生了最重大的一次變革,那就是封建官僚制度正式取代貴族世卿制度,以前貴族的封邑遍布天下,官吏亦主要由公子、公孫擔任。到了戰國,封邑大都變成了郡縣,即使是保留下來的少數封邑,貴族也只是“食祿而不治民”。那誰來“治民”呢?由封建官吏來承擔。
官員不再是世襲,而是由國家任命,無論是中央文官的最高職位“相邦”,還是地方政府的主官“守令”,都由國家授予官璽,并在任期結束后予以考核,即“上計”。官吏不稱職或有過失者,收其璽免其官。《荀子》記載:“相邦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可見,即使是“百官之長”的相邦,也不能游離于監督之外。
成書于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稱:“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視“吏治”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御史也就作為“治官之官”,出現在歷史舞臺上,這個古老的官職,從戰國一直沿用到清朝,成為最廣為人知的一個古代監察官職。
也正是在戰國,中國法制初見雛形,魏有《法經》,趙有《國律》,燕有《奉法》,秦有《秦律》,徹底改變了過去“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也為中國監察法制成文法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所以說,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中國監察法制與制度便已濫觴,監察體系初步建立,正如那則小故事里講的,即使是一言而得“精兵十萬、革車千乘”,嚇退強楚、居功至偉的淳于髡,在級別遠遠低于自己的御史的監督下,卻也不敢放肆飲酒、君前失儀。
二
擺在案頭的這部《中國古代監察法制史》(修訂版),便是張晉藩先生主編的,去年重新修訂,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則故事也被收入其中的“結語”部分。
此書由張晉藩先生帶領屈超立、汪慶紅、李青、焦利等四位教授,耗時兩年完成,共八章,張老親自撰寫了其中三章,列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成果。透過厚重的紙張,一幅古代監察法制演變的歷史長卷展現在讀者面前。中國古代監察法制,從先秦的萌芽狀態,到秦漢的形成階段、魏晉的南北互進、隋唐的成熟樣態、兩宋的深向發展、元代的承上啟下,一直到明代的調整強化、清代的細密完備。
通覽全書,感覺有三個鮮明特點力透紙背:史家功底、法學視野、文化自信。
一是史家功底。此書史料詳實,征引書目遍涉從先秦到清末的數百部古籍原典,以明朝一章為例,除了《明史》《明會要》《大明會典》《國朝典匯》《明通鑒》等常見明朝歷史、典章原典之外,還引用了《皇明世法錄》《明大政纂要》《皇明大訓記》等少見、稀見典籍,并從大量明人筆記、奏疏中提煉出史料佐證,予以審慎考證。
可以說是“典史互證”,即不僅僅羅列監察制度,而是用具體史料來回應、印證,比如針對明朝監察任職回避制度,“父兄伯叔任兩京堂上官”,即直系親屬擔任中央機關主官的,“不得任科道官”,不能擔任監察官員。著者從汗牛充棟的史書里,為這個制度尋找史料支撐,以正德元年監察官員許誥為例,許誥時任刑科右給事中,負責監察刑部,由于其父許進突然在古稀之年被重新啟用為兵部尚書,根據回避制度,許誥的職務調整為翰林院檢討,不再擔任監察官員。這樣子,關于制度的表述便不會生硬枯燥,而是鮮活呈現在讀者面前。
二是法學視野。按照現代的學科分類,法制史是研究法律及相關制度的發生、發展、演變及其規律的科學。狹義的法律史僅著重于法律本身的演進,而廣義的法制史所包含的范圍較廣,除法律本身、法律相關制度以及法律實行的情況外,還包括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此書似乎介于法制史概念的廣義與狹義之間,每章均包括5個層次:梳理這一時期的政權結構、監察體制、監察思想、監察立法以及監察法的實施。也就是說,不僅僅局限于監察制度、監察成文法的演變過程,而是將之置于政治和法律的宏觀背景之中,抓住監察法律的核心要素,予以提煉分析。
三是文化自信。正如此書“前言”所言:“中國古代監察法的系統性、完整性、持續性都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的。它所確認的監察制度建構、多元的監察機關體系、廣泛的監察法律規范,都鮮明地表達了中華民族在運用法律約束權力、規范權力運行上的理性思維與智慧。”其實,西方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研究也很重視,德國前總統、法學博士羅曼·赫爾佐克在其《古代的國家——起源和統治形式》一書中,提到了中國古代監察,并稱“中國歷代國家比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都更多地對自己的省級官員進行了監督考察,這樣一種監察在所有的國家都是必要的”。書中還收錄了歷史上敢于擔當盡責的監察官員的部分事跡,彰顯文化自信。
三
通讀此書,縱觀中國古代監察法制史的發展長河,可以感受到一些內在規律。
監察機構的改革從未止步,圍繞機構獨立行使監察權、完善機構設置等主題,發生了三次大變革。第一次是秦漢時期,組建和完善以御史大夫(中丞)為長官、以諸侍御史為專職官員的中央監察機關,以及司隸校尉、丞相司直等其他監察機關,另外,還囊括了監御史、刺史、郡守、督郵等地方專兼職監察官員,共同構成了覆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司法和軍事機關的監察機構。然而,由于監察機關分屬不同系統,職權往往有交叉,權責不統一現象比較多。于是第二次變革出現在了隋唐時期,整合中央監察機關,組建了“一臺三院”的監察體制,臺是御史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為長官,機構分為臺院、殿院、察院,號稱“三院”,臺院監察京官,殿院糾彈朝儀,察院監察地方官吏,職能分工更為明確。第三次變革則出現在明清時期,都察院取代御史臺,作為中央監察機關,但還存在“科道”監察系統,即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等中央機關,十三道監察御史監察巡視地方,“道”只是名義上隸屬都察院,實際獨立運作,“科”在形式和實際上均是獨立設置,依舊存在監察權力交叉,后來進一步實現“科道合一”,所有職權均收歸都察院,從此都察院作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進一步提高了監察效率。三次變革的總趨勢是,提高監察機關的機構規格,增強監察機關的職能權限,擴大監察范圍,整合監察系統,確保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監察法規逐步完善,西漢初年即出現了《監御史九條》《刺史六條》兩部監察法規,曹魏《察吏六條》,西晉《察長吏能否十條》《察長吏八條》等亦同此類。唐代的《唐律疏議》和《唐六典》,則從法理上為監察機構的設置與運作提供了法律根據。元代《風憲宏綱》,則收錄了自元世祖到仁宗時的監察法令匯編,內容豐富,法條細密。明代《憲綱總例》《糾劾官邪規定》《通政使司典章》《出巡事宜》《巡撫六察》《責任條例》等監察法規,更是體現了古代監察法規的可操作性,而且問責意識更為強烈。比如《憲綱總例》規定:“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拿杖一百,發煙障地面安置。有贓從重論。”監察官員巡視地方,如果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理,就會被流放,收受財物則從重處理。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欽定臺規》,則成為中國古代第一部監察法典,標志古代監察法的完備程度達到頂峰。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這本書修訂再版,或許更有一定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