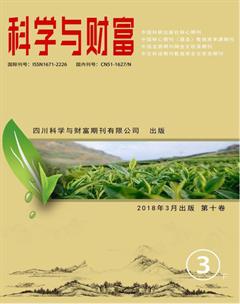網約車司機在集體勞動法的身份定位
羅科麟 陳鳴 朱星霖
摘 要: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網絡技術也在不斷優化和發展,而其中的網絡約車成為現代快節奏的一種表現形式,現在的網絡約車成為人們普遍打車的一種方式,網絡約車平臺對于處在一個共享經濟的時代來說是代表著共享經濟的運作模式。根據我國《勞動法》的相關規定,網約車司機和平臺公司并不是勞動關系,網約車司機既不是個別勞動法上的勞動者,也不是集體勞動法上的勞動者。而就目前網約車的發展狀況來看,把網約車司機劃分入集體勞動法的保障范疇是必然的。本文對網約車司機在集體勞動法的身份地位進行探究和分析。
關鍵詞:網約車;勞動者;個別勞動法;集體勞動法
前言:
現在是一個共享經濟的時代,它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網絡約車是共享經濟的表現。網絡約車的平臺吸引了大量的人員來從事這個工作,因為平臺不僅縮短了人們等車的時間,還給司機提供方便,極大程度上減少了尋找客戶的時間,而且還會給司機帶來更多的利益。在《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兩個文件中明確規定了網約車的合法地位,但是網約車司機在集體勞動法中的身份定位受到爭議,對于網約車司機和平臺公司是否屬于勞動關系一直尚未明確規定。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網絡平臺的發展,網絡約車的現象普遍存在,它正在慢慢改變著人們的出行方式,而且共享經濟的出現和發展讓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服務的提供者,讓每個人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空閑資源為社會創造價值。網絡約車是共享經濟運作模式的代表,它不僅縮短了司機和乘客的搜尋時間,也創造了一個由供需決定的有效市場,從而降低了服務的不確定性。但是,現在的網絡約車司機缺少一個法律上的身份認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網絡約車司機和平臺公司是否屬于勞動關系的爭議越來越多。
二、網約車司機之勞動關系的現狀
根據《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和社會保障部所確立的勞動關系的情形,可以將勞動者在個別勞動法中的內涵總結為“年滿十六周歲,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并接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還要符合用人單位規定的各項規章制度,不管與用人單位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其都是勞動者且其勞動也具有法律效益。”勞動關系的產生是勞動者在用人單位提供勞動服務,用人單位支付其勞動的費用。勞動關系一旦產生勞動者就必須接受并聽從用人單位的指揮和監督,由此可以看出,勞動者的一個重要特性便是從屬性。
理論上的從屬性包括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以及組織從屬性。其中的人格從屬性是指勞動關系確立后,用人單位分配工作給勞動者,并確定勞工勞務支付地、支付時間及勞動強度、勞動過程等工作內容,在工作期間用人單位可根據勞動者的勞動表現予以懲罰和獎勵,保證企業正常運行和維護企業資方在經營管理上的權威。經濟從屬性是指依賴勞動所得的工資為生活提供保障且如果失去這份工作那么就會難以生存下去,這份工作是在生命的基礎上維持生活所必須依賴的物質條件。組織從屬性是指在工作單位與其他同僚、伙伴進行分工合作,并接受雇主的生產組織體系的安排。而我國個別勞動法中關于勞動者的定義中就有這三類從屬性的特征。我國個別勞動法中對人格從屬性的要求表現在"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且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管理",對經濟從屬性的要求表現在"從事用人單位所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對組織從屬性的要求表現在"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首先,網約車司機并沒有被列入平臺公司的人事系統內,所以并不屬于平臺公司從事人員,也就不適用平臺公司的規章制度。網約車司機不受企業控制,對于客戶的訂單具有自主權,愿意接哪位客戶就接哪位客戶,平臺公司做的只是為他們提供訂單信息,而這只是一種引導行為,并非起著主導作用。其次,網約車司機的工資并不是和普通勞動關系分發的固定工資且有獎懲,而是根據訂單量來確定,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最后,平臺公司只是提供信息,與司機之間做連接,并不提供租車服務,而且訂單是自己單獨完成的,司機與司機沒有任何合作。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網約車司機定義為自營業者比較合適。
而且在《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這兩個文件中確立了網約車的合法地位,從此以后屬于正常的運營工作。《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中的第十八條規定是“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保證提供服務的駕駛員具有合法從業資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根據工作市場、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從這項規定可以看出平臺公司并沒有與網約車司機簽訂必要的勞動合同,所以平臺公司與網約車司機之間不是勞動關系。
三、網約車司機在集體勞動法中勞動者定位的意義
集體勞動法與個別勞動法對于勞動者是有不同的范疇,集體勞動法的范疇比個別勞動法的范疇較為廣泛,但是對于勞動法的研究來說兩者的比較是無實在意義的。在集體勞動法中勞動者是公務員和具備人事關系的職員,但是這類工作人員完全可以排除勞動法的適用。集體勞動法基于保障勞動力市場的供應者通過自行集結、強化議價的能力,通過法律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和維護團體協商的秩序,并不是直接決定協商的內容和結果,而且它側重的是勞動者通過依托團體力量的自力能力進行補強。
日本的勞動基準法和勞動組合法對勞動者的區別在于是否依靠工資、薪金等其他收入生活,這和集體勞動與個別勞動的區別大致相同。不論是集體勞動法還是個別勞動法,其概念都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否則就是空話。根據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可將網約車司機定位為勞動組合法的勞動者,勞動組合的相應代表可以進行團體商討,這樣不僅能夠防止勞動關系的過度廣泛,還可以幫助團體尋求團結的需求得到滿足。這種融入團體協商的策略機制,會更加顯示出共享經濟模式的特色之處。
結束語:
在這個共享經濟不斷發展的時代,明確網約車的法律定位,不僅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對促進共享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網約車司機是網約車共享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保護網約車司機的合法利益是在共享經濟發展中不可忽略的任務。盡早對網約車司機在集體勞動法的身份定位對經濟發展和司機的利益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參考文獻:
[1]逯慧,陳晉勝. 互聯網約車社會車輛駕駛員的勞動權及其保護[J].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7,(06):67-73.
[2]阮何明. 論網絡預約出租汽車司機的勞動者身份[J]. 法制與社會,2017,(10):293-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