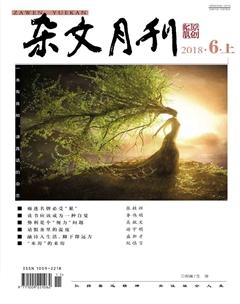我愛生活,并為使其美好而戰斗
哈米
翻譯講究信、達、雅。信達不用說了。雅吶,什么叫雅?作為門外漢的我認為,雅,不僅忠實于原文的內涵,并且優于原文。行家說過,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有優于原文之處。據此觀點,我多年來一直想表達如下的一個意見。這意見并無深奧之處,是很具體單一的。
我是尤利烏斯·伏契克的擁躉者,讀過《絞刑架下的報告》好些不同譯本,有劉遼逸據俄文轉譯的,陳敬容據法文轉譯的,蔣承俊、徐偉珠各自據捷克文直譯的兩個譯本。他們譯筆各有千秋。《報告》中一段最著名的話,劉遼逸是這樣翻譯的:
我愛生活,并且為它而戰斗。我愛你們,人們,我愛你們,當你們也以同樣的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你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我得罪了誰,那么請你原諒吧;我使誰快樂過,那么請你們不要為我而悲哀吧。讓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喚起悲哀......如果眼淚能夠幫助你洗掉心頭的憂愁,那么你們就放聲哭吧。但不要憐憫我,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這段文字極為簡潔,卻堪稱《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核心思想,極具感染力地傳遞出伏契克的人生價值觀和巨大的人格魅力。這是一位英雄對親人、戰友和同志的遺言,但不是那種擲地有聲的豪言壯語,而是極為親切的、既莊嚴又柔情的摯友間促膝談心似的言辭。說的是犧牲與死亡,可傳遞出來的,卻是歡樂和明朗如春日的情愫———這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源自與生俱來的磊落的天性!我不止一次說過,我之所以對其人其作品一見傾心而成為他的擁躉者,并不是由于他所信奉的主義,而是他這種天然自成的、無法效仿的性格魅力。
其實,遠不止是我,許多七零后八零后乃至九零后讀者,他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沒有人向他們宣傳這位捷克英雄了。他們都是在自己的閱讀中發現了這種魅力,被感染了而成為“伏粉”,成為我的同志的。
要說藝術性,這就是《絞刑架下的報告》藝術性(更確切地說是靈性)所產生的效果。不僅僅是上述所引這幾句,整部《報告》都充滿著這種既激越又溫馨的語言。這使得這個作品在所有的監獄文學中獨樹一幟。
上述劉遼逸譯文所以一下子打動了我,除了內涵之外,譯文的美妙是個重要因素。我們都有體會,行文(不管用哪種語言)要有節奏感、音樂性。“我愛生活,并且為它而戰斗”,干凈利落,節節推進,毫無拖沓之感。
可到了陳敬容根據法文轉譯時,這句話譯成了:“我愛生活,為了它的美好,我參加了斗爭。”語氣一下子松弛了,像剎那泄了氣的皮球,沒有了節奏。而且我覺得“斗爭”沒有“戰斗”好。
蔣承俊根據捷克文直接翻譯的也如此,而且重疊了兩個“生活”,更顯拖沓:“我愛生活,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戰斗。”
徐偉珠根據捷克文直譯的也類似而且更加累贅:“我那樣熱愛生活,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戰斗。”
為什么說累贅,因為不僅重疊了“生活”,而且,在“愛”前面加了個“熱”還不夠,再疊上個“那樣”,明顯“蛇足”!
除劉譯外,這種結構類似、卻變動添加字眼的現象,我猜大體是后譯者想區別于前譯者譯法各異的不得已之舉。但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為什么后三位不同于劉譯,在“我愛生活”后面有一句“為了生活的美好”呢?是否原文就是如此?如果是,那么后三位譯法盡管缺乏節奏感,卻是忠實于原作,是準確的。不懂捷克文,只好找來英譯本對照參考,發現后三位與英譯很吻合。但我仍然欣賞劉遼逸的中譯。一位“伏粉”對我說,劉譯只講“我愛生活,并且為它而戰斗”,沒有說到“為了生活的美好”呀。我說“為它而戰斗”,當然指為“美好的生活”,這是不言而喻的,總沒有為了丑惡的生活而戰的吧。
還有,劉譯的最后一句“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同樣節奏明快,而且“悲哀的安琪兒”讀來非常順口,不像其他三位譯成“悲悼天使”或“悲愴的天使”那樣拗口又缺乏詩意。
因此,我每次寫稿引用伏契克這段話,都是選定劉譯的這幾個句子,再根據其他譯者譯的個別字眼綜合調整成最佳組合而用的。后來我又想,沒有譯出原文有的那“為了生活的美好”也不很恰當,能不能譯得更好一些,既有“為了美好的生活”這層意思,又保持緊湊的節奏呢?我想了下,動手把它改“譯”了一下———
我愛生活,并為使其美好而戰斗。我愛你們,人們......
自覺最佳,不知大家認為怎樣。這,算不算就是翻譯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