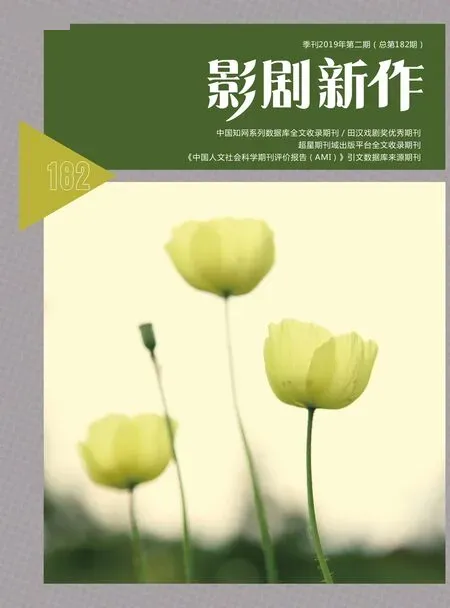微電影劇本禮 物
史 俊
時 間:當代
人 物:李明月 女 35歲 市某區文廣新局副局長 云水村第一書記
張煉章 男 53歲 云水村育種基地董事長
吳山花 女 50歲 云水村村民
趙大爺 男 90歲 云水村村民
王心蘭 女 30歲 云水村村民
萬長春 男 27歲 云水村委會主任 后任黨支部書記
1、云水村村道(日外)
[早晨,初秋的和風吹來,秋意濃濃,楓葉正紅。
[李明月騎著一輛半舊的自行車急切地向鏡頭漸漸駛來,她顯得如此俊秀端莊。
2、云水村塘邊(日外)
[吳山花等人正在洗衣。
[李明月騎車從此路過,下車與大家打招呼。
王心蘭 (邊洗衣)李書記,你回來了。
李明月 是啊,心蘭,我回來了。山花姐,你們吃早飯了嗎?
吳山花 沒有,明月你也沒有吃吧?等下去我家和我一塊吃炒面。
李明月 我吃過了,山花,我趕到村里開個會啦。
吳山花 李書記,鄉親們說組織上要派你去另一個村里扶貧是嗎?
李明月 是啊,山花姐,我真舍不得你們!
3、云水村委會(日內)
[李明月與村“兩委”人員和群眾代表一起開會。
萬長春 同志們,鄉親們,李書記來我們云水村掛點科技扶貧并在我們村兼任第一書記三年了,我們村430戶人家好不容易脫貧了,現在縣委又派她馬上去葉家村扶貧。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李書記講話。
李明月 (動情地噙淚道)同志們,鄉親們,謝謝大家三年以來對我扶貧工作上的支持。日子過得真快啊!記得三年前的今天,我從縣文廣新局來到你們這里扶貧撥窮根,一晃三年就過去了。可以說,這是三年來我在云水村扶貧工作的最后一個會,我明天就要去葉家村了。想想三年來,我們一起依靠科技的力量走上致富之路的日日夜夜,我真是百感交集。我從心里真地舍不得同志們,舍不得鄉親們,舍不得腳下這片金土地。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云水村未來十三五期間新農村科學發展經濟建設規劃……
4、古樟下(夜內)
[明月高懸,傳來野外歡快的蟲鳴鳥叫聲。
[吳山花與張煉章、趙大爺、王心蘭等多個村民正在商議什么。
吳山花 (面對張煉章)我剛得到消息,李書記派去葉家村工作了。李書記多好,真舍不得她走呀。
張煉章 是啊,人家要走,禮輕情意重,按道理我們應該送點禮物聊表心意啊。
吳山花 是啊,我今天請大家來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趙大爺 明月這孩子真是黨教育出來的好主席,可是送什么好呢?記得前年我家養殖的十畝魚苗發了瘟,我們全家急得團團轉,她立馬派來了水產專家為我家魚苗治好了病,還教會了我家科學養魚技術。這年底,我家依靠科技養魚賺了個金滿盆滿。為了回報她,我兒讓我買了兩條中華煙……(趙大爺回憶)
5、(回憶)云水村村委會(夜內)
[李明月正在燈下寫“民情筆記”,這時趙大爺提著兩條中華煙叩門進來。
趙大爺 李書記。
李明月 (扶著老人坐下并為其沏茶)趙爺爺,請坐下。請問你兒子魚的價錢賣得好嗎?
趙大爺 很好很好……
李明月 那您老還有什么事需要我們幫忙?你盡管說。
趙大爺 沒有,是這樣的……明月……(把兩條用檔案袋裝好的煙遞到李明月的面前)這是你老伯的一點心意。
李明月 大爺,這可使不得。我是扶貧工作者,為鄉親們排憂解難是我應盡的義務。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是我高祖父當年在我們這里從事革命工作時常說的道理。何況,兩條中華煙要賣多少斤稻谷才能買到。我曾看見鄉親們在田間拾稻穗,想想看兩條中華煙要撿多少稻穗才夠折這個價呢……
趙大爺 明月,你的高祖父是不是叫李信江?
李明月 是啊,趙大爺,你認識?
趙大爺 認識認識,當年你高祖父隨方志敏來到云水村發動土地革命我還小,你爺爺自帶咸菜薯片來我們這里辦公。我父親病死了還不了債,地主逼我去他家打工抵債,我受盡了欺侮。是你高祖父把我從苦海中救了出來,而他連一餐飯也沒在我家吃過,后來隨方主席北上抗日犧牲…… (說到這時,哽咽道)孩子,你多像你的高祖父,從你的身上我看到了當年的紅軍,看到了我們黨新的希望……
[趙大爺回憶完。
6.古樟下(夜內)
[現實場景:吳山花、張煉章、趙大爺等人仍在商議。
趙大爺 明月這孩子像他高祖父一樣.(轉而又面對張煉章)煉章,你在村里是個帶頭致富的典型,你說說如何表達對李書記的心意?
張煉章 趙大爺,你知道我原來是個窮光蛋,李書記來我們村工作后,跟我結成一比一的幫扶對子。為此,她鼓勵我建起一個蘑菇生產基地,并用自己的工資幫我去信用社抵押貸款。蘑菇獲得豐收后,為了表示謝意,我拿了一個裝有一萬元的紅包找到她……
7. 張煉章育種基地(閃回,夜內)
[張煉章與李明月正在相互交談。李明月朝張煉章承包的田畈上一眼望去,嘉育173、抗旱959、煉章廣銀占等各種新品種長勢喜人。只見這些品種的晚稻穗多粒大、長勢良好,呈現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
李明月 張總,這些年我算了一下,你累計為全縣農業引進各種優質水稻新品種600多個,繁殖與推廣水稻高產良種200多萬斤。特別是近幾年來引種成功推廣的茉莉香占、特秈占13,特秈占25、粵香占、華航一號、溪野占10號等優質新品種,產量達到優質雜交品種的產量,且抗病力強、米質特優,稻谷價比雜交稻谷高10多元/百斤。你培育推廣新品種,每年可為全縣農民兄弟增收400多萬元。
張煉章 李書記,想想當年我還是門外漢,要不是你帶你們科協的技術員一路提供科技育種的新經驗,還每年為我的這個基地舉辦一次現場觀摩會,為農友們挑選稻種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我哪有今天呢?
李明月 張總,看到你們育種基地風生火起我真替你們高興。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停步,不僅自己要富,而且要帶動鄉親們富起來。要走公司+基地+農戶之路,要建起一村一品,讓云水村成為全縣依靠科學育種致富奔小康的樣板村。你說呢,你還有什么事需要我幫忙?
張煉章 (從挎包內取出一個紅包)李書記,這是我基地的一點心意。
李明月 (發現是個紅包,轉而嚴肅地說)張總,你趕緊把這紅包拿走。你小看我了,我是這種人嗎?如果你真心實意地支持我工作,不要害我,趕緊拿回這個紅包……[張煉章回憶完。
8. 古樟下(夜內)
[現實。
張煉章 (面對大家)大家看,我送紅包在李書記那里不也是吃了一鼻子灰。(轉而面對吳山花)山花,你是我們今天群眾議事會的發動者,你說該怎么辦?你送過李書記的禮嗎?
吳山花 送過。當年李書記來我們村,我剛送走了重病多年的丈夫,心里難過又感到寂寞,她就來我家和我同吃同住同勞動,并每次都交伙食費。在我家住了幾天后,她發現我有刺繡的愛好,就發動我和王心蘭等幾個婦女辦起了刺繡廠,為幫助我們從傳統的手工作業中解放過來,提高生產力,還幫我們引進了電腦刺繡機操作管理人員、電腦刺繡花樣設計師來我們廠培訓電腦刺繡生產人員。后來我們資金周轉有困難,李書記又幫我們爭取了一筆扶貧資金……當年刺繡廠辦成功后,我提出給她股份……
9.(吳山花回憶)云水村刺繡廠廠長辦公室(日內)
[待員工們走入車間,吳山花面向李明月。
吳山花 李書記,刺繡廠辦成功了,留守的姐妹不再愁在家無事干了。
李明月 大嬸 ,這是好事。但刺繡廠不能滿足現狀,要做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把我們的刺繡產品打到海內外市場。我今天來和你商量的就是這件事。
吳山花 李書記,我想先和你商量一件事。
李明月 山花,有什么事值得在我面前吞吞吐吐,你倒是說啊。
吳山花 你知道我的刺繡廠是個股份制企業,我想請你入干股。我們10個董事你占十分之一的股,這也是姐妹們的一點心意……
李明月 (轉而嚴肅)山花,別說了,你不是把我當親姐妹一樣看待嗎?親姐妹哪能計較這些?你這是錯看我了。
[回憶完。
10.古樟下(夜內)
吳山花 (面對大家)我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李書記就是這樣的人。
趙大爺 李書記要走,又是去的別的村扶貧,我們總得表示點心意,否則我死了都心不安啊。
張煉章 (望了望吳山花,沉思了會兒)我有個想法……
吳山花 張總,你快說。
張煉章 山花,我想花三四千元錢買個好匾,你們刺繡廠幫我在上面刺上“明月清風 ”四個字送給李書記多好,既表示了我們的心意,李書記也一定樂意接受。
趙大爺 這個辦法好。是啊,這下李書記一定會接受的,不會讓我們再吃一鼻子灰了。
王心蘭 (深情地)要不是李書記牽紅線,我至今還找不到婆家。這繡字的活我來做。
[眾人雀躍。
11. 刺繡廠(日內)
[王心蘭帶頭刺繡,她帶著對李明月的一片用手工深情地繡起了“明月清風”四個字。
12. 云水村村委會(日內)
[吳山花、張煉章、趙大爺、王心蘭等眾鄉親將繡有“明月清風”四個大字的匾額送給李明月。
吳山花 李書記,這塊匾送給你帶回去。這是全村父老鄉親的共同心愿,你總該收下吧。
李明月 (鄭重地接過匾額)謝謝鄉親們。在今后的工作中,“明月清風”,你們送的這塊匾上的字將是我工作和人生的座右銘……
13. 云水村村委會(夜內)
[月牙出現在天穹,泄進窗格。
[待眾鄉親走后,李明月捧著匾額,心潮翻滾。
李明月 (心聲)這是鄉親們的一片心意,我不收又不好,可收了,又能行嗎?這是鄉親們花幾千元買的匾,我不能收,但又該怎么辦呢?有沒有兩全齊美的辦法?
[想了想,恍然大悟。她拿起手機,拍一張匾額的照片。然后打開桌上的電腦,將繡有“明月清風”四個字的匾額編入自己的博客。
[此刻,皓月當空,景色優雅,月色融融,燈光燦燦,令人心曠神怡。李明月在月光燈影下,體態更顯得窈窕婀娜,分外動人。
14. 云水村村委會(日內)
[李明月、萬長春等村“兩委”干部和張煉章、吳山花、趙大爺、王心蘭等眾鄉親都在場。
李明月 (手拿“明月清風”的匾額面對萬長春)長春同志,你是鄉親們通過海選擔任的村主任,又是組織上重用的村支部書記。我今天就要走了,但我還會來你們村的。今天,我送給村兩委的禮物也就是鄉親們送給我的匾額我轉送給大家,我已將這匾額拍進了我的手機,放進了我的博客,記進了我的心坎。讓我們以”明月清風”四個字來共勉,這四個字將永遠激勵我們在各自崗位上,樹立一心為民,服務群眾的宗旨意識,解放思想、不斷創新的改革精神;艱苦奮斗、扎根基層的實干作風;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崇高境界;團結農民、帶領百姓的群眾工作能力;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當一個能帶領群眾致富又純潔的黨的好干部,大家說對不對?
[眾人鼓掌。
萬長春 (鄭重地接過匾額)李書記,您放心,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我是個農村退伍軍人,正如您說的是鄉親們投票讓我當上了村主任,又是您力薦和組織培養讓我成了村支書。我一定會以您為榜樣,牢記眾鄉親的囑托,記住“明月清風 ”四個字,為建設廉政南昌盡我的一份力量和職責。
[倆人緊緊握手。
[接著倆人在眾人的掌聲中一起將繡有“明月清風”的匾額懸掛在墻上。“明月清風”四個字占據了整個銀幕。
[劇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