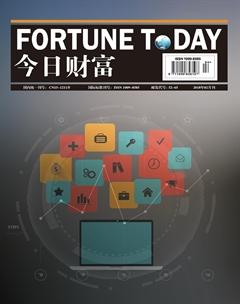地鐵運營服務重要指標的改進
陳善宇
目前各家地鐵在實際統計計算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口徑,實際上造成了統計標準的不統一,從而使各家地鐵指標缺乏對比性。本文著重探討如何將一些重要指標的口徑做到行業統一,以便真實反映各家地鐵的運營水平。
一、現有指標的統計分析
(一)以列車運行圖兌現率為例:在運營時間內列車開出后,在中途站發生故障,需要退出載客服務,如果在中途下線,這該如何統計?據我所知,目前國內同行有兩種方案,一是統計0.5個列次,只要有載客開行一站以上,就統計;二是完全不統計,目前行業這種做法占大多數。但是如果這個列車,是因為車門系統系統故障,需在倒數第二站清客,然后又能空車運行到終點站。這樣一來,光從運行圖上來說,可謂完美,但這樣對乘客服務還是有較大影響;還有就是運行圖也會統計備用空車的,如果某地鐵公司有兩個以上車場出車,某一天安排一個車場多出一列車,另一個車場少出一列車,這樣還需要統計一個抽線,一個加開呢,個人認為若按此實際統計的話意義就不大了。
(二)再說說列車正點率是以列車終點到站時刻和列車運行圖計劃到站時刻相比誤差小于2分鐘的次數。從定義上來講列車中途下線的,沒有到達終點,是不納入統計的。但對乘客而言,的確會晚一個行車間隔才能到達目的地。還有一種情況,列車中途清客后,再運行到終點站退出服務,那么這次列車從指標上來說正點了,運行圖也兌現了,實際上對乘客的影響還是較大的,卻不能在指標里得到很好地體現。
從表面看上述兩個指標看似關系不大,但實際操作時,卻可以進行選擇和規避。比如說,某個列車在中途站晚點了5分鐘,如果我在中途改開車次,是不是就可以算一個加開,一個抽線,這樣運行圖兌現率會下降一點點,但列車正點率變成100%了。還有就是,調度可以采用越站的手段,安排晚點列車越兩三個站,那5分鐘的晚點基本能過來趕過來,這就避免了指標晚點。
二、完善指標
(一)載客列車運行圖兌現率。這主要是從服務、從乘客的角度出發,也方便各家地鐵組織運行服務。比如說某兩家地鐵一天同樣開行1000趟載客列次,但包含空車列次,一家地鐵為1040列,一家地鐵為1080列,某天都抽線10列次,如果按現有運行圖兌現率來說,后者的兌現率必然高于前者。其實對乘客的影響,只有載客列車的車次統計和兌現,才更具有現實意義。這種角度看兩家地鐵公司的當天服務水平是一樣的。而對于那些已發出,但在中途下線的載客列車,建議統一統計為0.5個列次,以便于完整的抽線相區別,畢竟有部分乘客是得到本列次的服務了。
(二)載客列車正點率。現行指標,將空車也納入正點列次,其實意見不大,也不方便調度的調整,實際上,目前大部分地鐵在統計時將空車均會統計為正點,以使指標更好看。其實真正應該關注的是載客列車的影響情況。但現指標列車正點率,必須統計終到的正點率,那如果在某終點站發生電力故障時,因情況需要采用大面積小交路折返時,這時候應該如何計算正點率呢?也最好有個規范,個人認為提前布置為小交路的列車,小交路終到站可以視為終點站來對待,到達小交路終點站的時間不晚點,本列次可視為正點。對于加開載客列車,目前國內同行將加開列次均統計為正點,其實乘客是不知你的列次是圖定還是加開,乘客只對從某站到達某站的時分有一定的熟悉,因而建議可按就是否超過區段正常運行2分鐘來統計正晚點情況。
(三)乘客最大受影響時間。個人認為,這個指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在地鐵運營現實中卻有所忽略。比如說,某次列車在車站停站后,未打開車門,30秒后駛離車站,這種情況下,從運行圖兌現率、列車正點率來看,指標十分完善,而乘客其實會受影響特別大。如果設了這個指標,就可以按乘客需從本站到達下一站,返回坐地鐵再到本站的時間,作為乘客最大受影響的時間。目前,香港地鐵是將這方面納入指標統計中的“最大延誤”。那對于上海等大城市,有時常需要采用越站辦法,在計算方法上可以有所不同,如果司機、車站廣播提前告知,可以安排乘客在前一站下車,那么乘客最大受影響時間就可以計為一個行車間隔。這樣就也可以區分計劃安排和應急突發的影響。
其實地鐵指標的好壞,還與列車運行圖的編制有很大的關系,如果運行圖編制得緊,所用列車數少,折返時間短,可系統對運營調整時間有限,列車的正點率總體而言會有所下降,相反亦然。如何對指標體系進行完善,做到標準統一,需要對指標進行規范詳細的計算說明,最好再以國家標準的形式進行下發,這樣才能確保各家地鐵數據的統一和規范,從而能真正評判國內地鐵的運營服務水平優劣。(作者單位為寧波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