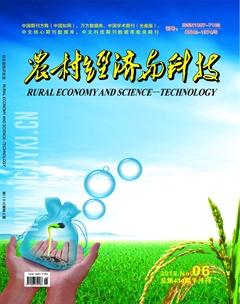旅游社區化與自然文化遺產管理
白露
[摘 要]“旅游社區”的提出已有近30年的時間,但對其本身及相關概念的解釋不清,并存在一定誤讀。誤讀的結果直接影響到自然文化遺產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本文對旅游社區與景區的關系進行了新的闡述,并將旅游社區化理念引入自然文化遺產管理。
[關鍵詞]旅游社區;旅游社區化;旅游社區參與;自然文化遺產管理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旅游社區常被理解為是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較接近、有著共同利益的群體。這一理解強調了旅游社區的區域空間性,即以某一旅游景區為中心,一定的地理距離為半徑來界定。于是也就有學者為理想的旅游社區總結出以下特點:具有一定范圍的社區地域;具有獨特的社區文化;具有優美迷人的社區環境;具有合理高效的社區結構。
而旅游社區最早的提出者Peter·E·Murphy在《旅游:社區方法》中的觀點則是:“旅游社區應該是一種方法或途徑。它從社區的利益出發,由社區控制開發過程,確定發展目標,并由此來追求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之間的平衡。”顯然,Murphy提出旅游社區的初衷并不是一種局限于有形界限之內的區域空間,更接近于一種管理方法。
1 旅游社區與景區的關系
1.1 關系的誤讀
無論是旅游社區的哪種定義,基本都認可了其構成要素包括社區居民、社區環境以及社區文化等。同時,強調不同于一般社區的地方在于,旅游社區往往與旅游景區或旅游目的地有著密切的聯系。也正因此,旅游社區很輕易就被理解為依附于景區的較大空間活動。這一理解顯然把景區或旅游吸引物放在了核心地位,旅游社區則自然而然成為了附屬物。
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旅游社區參與的重要性,但這種重要性的認可往往是從旅游社區作為一種被補償對象的角度出發的。因此,在闡述社區參與的作用時,有學者認為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服務有助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扶貧,可以盡可能減少漏損、最大化旅游收入的乘數效應。可以說這種觀點直接導致了在景區管理的實踐中,地方政府、景區企業以及附近居民自身都將如何從景區開發中獲利作為處理利益關系的根本。
這種對旅游社區與景區關系的誤讀之處有三:
一是誤讀旅游社區的概念。重溫墨菲1985年所說:“旅游業從一產生,就有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能夠將它從純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中脫離出來,從生態環境和當地居民的角度出發,將旅游業考慮為一種社區的活動來進行管理,那么一定能夠獲得更佳的效果,這就是社區方法。”因此,從本質上看,旅游社區的初解應該是一種景區管理的方法,而非區別于景區的區域空間。
二是誤讀旅游社區與景區主附關系。即便承認當下旅游社區的空間群體概念的認知,但將旅游社區作為依附于某一景區的群體也是欠妥的。這種主附關系勢必導致將旅游社區置于次要地位,同時減弱旅游社區在景區管理中的作用。
三是誤讀社區參與的補償機制。積極推進社區參與,對社區居民創造就業,力爭使其從旅游景區的開發中分得一杯羹。這種貌似公平善良的補償機制實質上則是對社區居民權利的剝奪,同時極有可能挑起更大的利益紛爭。
1.2 旅游社區化不等于旅游社區參與
回歸墨菲概念的本源,再次強調旅游社區是一種方法。為了區別當下對旅游社區的普遍理解,本文將體現墨菲初衷的管理方法表述為旅游社區化。目前人們通常把社區參與作為景區管理的一種方法,這就相當于將社區參與與旅游社區化畫了等號,事實上兩者是存在差異的。
1.2.1 旅游社區化應以社區本身為主體,而非景區的附屬物
歸咎于旅游社區理解中刻意強調景區的核心地位以及社區對其的附著性,這使得社區參與的過程往往將以社區居民、社區組織為代表的旅游社區放于次要地位。旅游社區化則應強調景區與社區居民、社區文化以及社區其他資源共同構成旅游社區整體,而非人為割裂對待。
1.2.2 旅游社區化強調社區管理的自主性,而非參與性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常被定義為把社區作為旅游發展的主體進入旅游規劃、旅游開發等涉及旅游發展重大事宜的決策、執行體系中。而在國內景區管理的實踐中,這種“進入”或流于形式,或最多停留于股權制的利益分享。其中更多的則是景區內部分小型服務項目的承擔。
旅游社區化既強調旅游社區包括社區居民與旅游景區等,同時強調其地位的相當,就要求社區管理的高度自主化。這一觀點必然會引起對社區居民自主管理能力的質疑。事實上,旅游社區化的主體不僅包括社區居民、社區組織,還應包括當地政府。正如王瑞紅和陶犁(2004)提出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既指旅游社區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區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方法和手段,也指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旅游發展計劃、項目以及其他各類事物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及其過程,是居民對社區旅游業發展責任的分擔和對社區旅游業發展成果的分享。但按照眾多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以及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真實案例來看,他們所理解的社區參與的主體似乎只包括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政府只是當地旅游發展的一方利益相關者。
1.2.3 旅游社區化突出社區利益所獲,而非利益補償
如果旅游社區居民通過“扮演”景區內的小商小販,或是景區股份公司的股東的所得被認為是景區開發后對其損失的一種補償的話,那就已經假定了社區居民與景區本身的對立。事實上,這一錯誤理解正是源于以上兩點,即旅游社區與景區的割裂以及旅游社區化中社區主體的自主管理程度不高。
既然景區同社區居民一樣同屬于旅游社區,且社區居民或當地政府對景區管理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那社區居民由旅游資源獲得的效益,就不是一種補償,而已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利益獲取。這一點與布蘭登(Brandon)的觀點較為一致,即認為社區參與是使旅游地社區“獲利于”旅游而不是“受利于”旅游。
2 自然文化遺產管理中常見的問題
2.1 遺產開發與保護的矛盾
一方面國內各個地方政府對于世界遺產的申報抱以極大熱情,同時旅游企業也對自然文化遺產的開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另一方面則隨著世界遺產名錄的增加,國內自然文化遺產卻不斷面臨著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惡化的挑戰。2005年《神雕俠侶》劇組被指破壞九寨溝自然景觀。隨后,2006年媒體報道影片《無極》劇組因拍攝過程中對香格里拉生態環境造成破壞被處以9萬元罰款。而張家界也曾因在主要景區內興建大量商業建筑而被聯合國遺產委員會出示紅牌,勒令整改。
這一矛盾產生的原因除了破壞者的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外,更重要的是國內自然文化遺產管理制度中,政府在擔任監督者的同時,也參與了自然文化遺產的旅游經營活動。在多重利益的驅使下,往往出現監管缺失。
2.2 社區參與的無序化表現
社區居民參與國內自然文化遺產旅游的發展也較為普遍。這主要源于遺產旅游開發的客觀需要和遺產管理過程中的利益平衡。前者如武夷山旅游公司在組建時,采取了國家集體農戶合作型組建模式。這基于武夷山周邊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的國情。另一個典型代表是廣東開平碉樓。作為民居建筑的碉樓,其產權屬于具體的華僑家庭,因此,在遺產開發時采用了政府租賃,統一管理的模式。這些由遺產本身產權性質引起的社區參與多少帶有一定的“無奈性”。后者則更多體現在居民因社區資源被出讓后的交換所得,例如景區內服務項目的經營權等。
但這種社區參與的低自主性和被動性,往往導致在遺產管理過程中,不斷產生摩擦。例如,2004年4月1日武夷山景區實施了全封閉的智能化管理方式,對游覽人數、進出車輛等進行合理控制,但實施后受到當地農民、部分車商和旅行社的阻撓,尤其是受到那些在景區擁有農田、菜地農民的抗議,以出入不便為由對景區進行破壞,還與景區員工發生過沖突。至今,封閉式管理不得不暫告一段落。
2.3 遺產價值的人為流失
如《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前言所述,“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越來越受到破壞的威脅,一方面因年久腐變所致,同時變化中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使情況惡化”。
在未能妥善處理旅游業對遺產旅游社區影響的時候——包括與社區居民經濟利益的分配以及社區文化的沖擊,社區居民的離開或社區文化的改變都是遺產價值的人為流失。例如本地居民拆掉老房子,改變風俗習慣,甚至年輕人離開本地出外打工等。
3 旅游社區化在自然文化遺產管理中的實施
針對以上問題,旅游社區化則可以從長遠的角度加以解決。其在自然文化遺產管理中的具體實施包括:
3.1 旅游社區居民最大限度發揮自主管理
雖然旅游社區居民對自然文化遺產的直接管理受到資金和能力的多方面限制,但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這是一條必經之路。因為,旅游社區居民與社區文化、自然文化遺產密切相關,共同構成旅游社區。旅游社區化就是要將其作為共同的主體,進行統一管理。所以,社區居民的自主管理應從經濟鏈條的末端——利益補償,逐步向前端移近,包括對遺產的規劃、管理決策、環境保護等內容。同時,旅游社區的自主管理不單指于社區居民,還可包括非營利性的社區組織。
這種自主管理的價值已得一定的證實。如澳大利亞的卡卡杜國家公園的管理演變之路實際上就是一個逐步確定當地土著人作為管理者的過程。從最初種族歧視和不信任下的完全排除,到土地所有者身份的認可,直至最后國家公園的主要管理者。20世紀90年代初,卡卡杜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由14名委員組成,其中多數委員(10名)是土著居民代表。截至2000年6月30日,包括臨時合同雇員在內的少數民族裔雇員占卡卡杜國家公園所有雇員總人數的32%。
3.2 社區居民通過培訓計劃確保管理者身份
鑒于自然文化遺產管理的專業性,居民作為旅游社區的管理者,同時對自然文化遺產進行管理是一個需要不斷學習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將社區居民的培訓計劃納入遺產的規劃和管理過程。這其中,需要地方政府做好引導工作。同時,社區居民作為管理者,不等同于社區居民必須獨立承擔遺產管理的各項專業工作,如財務、環境保護、資本運營等。專業化的經營工作完全可以通過聘用相關企業委托經營。這一點類似于城市住宅社區中業主成立業主委員會,聘用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進行小區的物業管理。需要強調,這與目前的第三方旅游公司雇用社區居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3.3 第三方僅享有部分經營權限
市場經濟下,除旅游社區居民、地方政府外,其余第三方亦可參與到自然文化遺產的經營活動中來,但應限制在一定的經營權限內。這一方面,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給出了一個可以借鑒的經營機制。
1965年美國國會頒布了《特許經營政策法》(Concessions Policy Act),明晰并規范了國家公園的經營活動,其經營權的界限僅僅限于副業——提供與消耗性地利用與遺產核心資源無關的后勤服務及旅游紀念品,同時經營者的經營規模、經營質量、價格水平等方面必須接受管理者的監管。1998年美國國會根據現實需要,廢除上述法案并通過了《國家公園綜合管理法》(National Park Omnibus Management Act),在公開招標、特許經營費和合同期限等方面做了調整。
3.4 政府明確社區成員身份監督遺產管理
地方政府作為旅游社區的構成主體之一,應始終站在旅游社區的利益角度。同時,市場經濟的環境要求政府應行使好“無形的手”,而不是作為運動員參與到經濟競爭中。因此,目前國內自然文化遺產管理中,政府兼任管理委員會和旅游公司的角色顯然極不適宜。
在自然文化遺產管理的問題上,政府應將管理職能交給以旅游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遺產管理旅游社區化。同時,對其管理進行指導,特別是在前期階段的引導與培訓。另一方面,也需要對參與自然文化遺產經營的第三方進行監管,切實做好遺產的科學開發與保護。
[參考文獻]
[1] 黎潔,趙西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理論的若干經濟學質疑[J].旅游學刊,2001(04).
[2] 唐順鐵.旅游目的地的社區化及社區旅游研究[J].地理研究,1998(06).
[3] 陳秀瓊,黃金火.略論生態旅游開發中的社區參與[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3).
[4] 劉緯華.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若干理論思考[J].旅游學刊,2000(01).
[5] 王瑞紅,陶犁.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形成及內涵[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04(04).
[6] 鄒統釬.遺產旅游管理經典案例[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