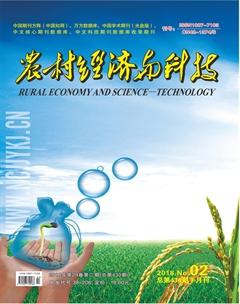山西春節信仰與禁忌民俗調查
岳文凱
[摘 要]以山西傳統農耕村落N村為個案,從民俗志角度對其進行深描,真實記錄春節期間普通農戶的過年信仰習俗,將“送灶”、“接神”、“迎送祖先”以及在此期間的各種言語、行為、本命年、“逢九年”禁忌等文化要素概括出來,展現了山西農村春節民俗信仰、禁忌習俗及其當代變遷。
[關鍵詞]神靈信仰;祖先祭祀;禁忌;變遷
[中圖分類號]K892.1 [文獻標識碼]A
N村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最北端,與忻州市轄區僅相隔兩村,但在語言、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與忻州有著天壤之別,有其獨特的面貌。N村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流傳著許多豐富多彩而又古色古香的傳統民俗文化。
1 春節信仰活動
N村的地方民間信仰駁雜多樣,神靈信仰、祖先崇拜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春節期間當地的主要信仰活動也是圍繞鄉村廟宇與家庭神堂進行。
N村東有“老爺廟”,南有“南神堂”,在村東、西、南、北、中各十字路口分布有八座“五道廟”;在人家院落中都供有天地爺,院門外留有小神龕供門神,門內側有土地爺,馬棚有馬王爺,過去場院有場神爺、家中有財神爺、廚房有灶王爺等。這些神靈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人們在春節期間按照約定俗成的時間在神廟與家中虔誠地供奉祭祀,整個春節成為世俗與神圣交織的有序生活。
當地春節從臘月就開始準備,“臘八”早上吃臘八粥,臘八粥燜熟后,家中長輩會先給家中各個神靈都供奉一小份,之后家庭成員方可分食。
臘月二十三祭灶“送灶王”,一般由家中年長的男性來“送”。入夜,先在灶王神像前上香、點蠟,供奉糖瓜;待香、燭燃盡后,揭下貼在灶臺邊的神像和兩旁的對聯,過去多在“炕火”中點燃,并念叨著“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等話語;現在農村基本都沒有土炕,就將神像放入灶火中燒掉,最后在院中放兩個鞭炮,意為送灶王爺上天。
臘月三十,也是“過年”前最忙的一天。這一天要把院子徹底打掃一遍;掛燈籠,掛柏樹枝、貼春聯,壘旺火,為接神做準備;打掃出一間空房,準備祭祖使用。
1.1 祭祖
當地人將祖先牌位稱之為“樹”,故祭祖又稱“通樹”。在中午之前將院中打掃干凈,選一個僻靜的房間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樹”通常用毛筆在白紙上從左往右依次書寫“五服”內祖先的稱謂及名字,將其供于桌子正中,當地稱其為“親樹”;另一張紙上寫外祖父母及娘舅家去世的先人,此為“戚樹”,置于“親樹”右側。“樹”前擺放香爐,在桌上擺放四碗四碟,當地有“神三鬼四”的說法,在每個小碟旁邊并列放兩柱香,代表祖先所用的筷子,所供奉食物與中午的飯菜無異;中午十二點之前上供完畢、燒香、磕頭、放炮,就意味著將祖先接回家中,當地說法為“通上樹了”,通樹之后一家人才可開飯。自此一日三餐的第一碗飯菜都先要供獻給祖先,上、下午還要為祖先敬茶,一直到正月初二晚上“送樹”之前。
1.2 旺火
當地旺火多為扎成粗捆的谷草,故又稱“年草”。再在周圍壘幾層木材,以延長燃燒時間。谷草外纏繞數圈紅色毛線,谷草內插數枝柏樹枝,意為辟邪,在接神時點燃。
1.3 掛柏樹枝
臘月三十貼春聯時,要在院門和家門正中掛一束用紅色毛線扎好的柏樹枝,與此同時,家中的每一個窗戶無論大小都要插一小枝柏樹,取其“辟邪”之意。
1.4 接神
接神一般在正月初一早上五六點開始,講究的人家會提前請人看接神的“時辰”。接神只能由家中的男人來做,起床凈手后,將各神的供品擺放好:天地爺主要供“豬、羊、雞、兔”等造型的花饃,一說為象征“六畜興旺”,也有人說象征真正的“豬、羊”等祭品;灶王爺處供“棗山”,寓意新的一年米面如山;財神爺處供“錢龍”,寓意財源滾滾。準備妥當,打開家門、院門,從院門口開始接神,先在院門旁的門神邊點燃蠟燭、上三炷香,進入門內接土地爺,同樣點蠟、上香、并敬獻黃表紙,院內接天地爺,屋內接灶王爺和財神爺,儀式都相同。接回諸神之后,點燃院中的旺火,拿出家人的新年衣物在旺火旁烤一下,意為驅邪。與此同時,取幾枝提前準備好的柏樹枝,在將要燃盡的“旺火”上烤熱,家庭成員都取一小枝別在耳后,待日出后方可取下。旺火燃盡,回屋準備早飯;在日出前諸神前香燭均不可熄滅,所以每當香燭將要燃盡時就需要馬上再點燃新的香燭,直到日出為止。
1.5 拜年
初一早上吃罷飯,家中老少男子先去“樹”前磕頭,向祖先拜年,再給家中老人磕頭后,方可外出拜年。初一上午只給同一宗族的“本家”拜年,因為各家都供有“樹”,所以拜年時通常先到供有“樹”的房間磕頭,再在天地爺處給本家長輩磕頭,方可進屋。
1.6 送祖先神
初二天黑后送祖先神,當地稱“送樹”。先將“樹”前的供的飯菜重新加熱,再上香,點蠟,焚燒紙錢、元寶。待香燭燃盡后,將盛有飯菜的四個碗以及香燭紙灰都放入簸箕內,再把寫有祖先稱謂的“樹”放在上面,由家中年長的男性端著簸箕出門“送樹”。走出供祖先的家門后,要將家門上鎖;走出院門后,要在院門口撒灶火灰;之后端著簸箕徑直走到村外無人處,將簸箕中的紙灰、碗中的飯菜等物倒在地上,點燃三炷香,最后點燃“樹”,磕頭后,將簸箕和空碗帶回,回到院中放一個鞭炮,“送樹”才算完成。但簸箕和空碗不能直接拿回屋內,需在院中放一晚上,第二天方可取回。
“送樹”體現了人們對祖先敬畏的心態,關門、灑灶火灰、放鞭炮、空碗不拿回家等行為反映出人們對祖先“靈魂”的畏懼,希望祖先“靈魂”順利離開家中,返回陰宅。
2 春節禁忌
春節期間神靈、祖先全部回到家中,人神共歡,同賀新春。這樣一個特殊的過渡時間和場合,人多口雜,難免會沖撞祖先或神靈,為避免沖撞神靈遭致厄運,當地村民千百年來傳承了種種禁忌,統稱其為“不該”。綜合來看,這些禁忌可分為語言,行為,本命年、逢九年禁忌等三部分。
2.1 語言禁忌
過年時,當地老人常說“說好不說賴”,這些語言上的禁忌一方面體現對祖先、神靈的敬畏,另一方面也體現人們對吉祥如意的追求。與神靈相關的語言禁忌如過年前趕集買神像不能說“買,要說“請”或者“接”;過年給神上香不能說“燒香”,要說“添香”或“加香”,點黃表紙不能說“燒紙”而要說“敬紙”;日常語言更是不能說不吉利的話,饅頭蒸得“虛”要說蒸得“發了”;餃子煮破了要說“煮開了”等等。
2.2 行為禁忌
過年期間對人們的行為有著種種規定。“通樹”后,忌在屋內嬉戲、追逐打鬧;忌家中未出嫁女兒拜祖先,已出嫁的女兒正月初一、初二因為家中“通樹”,更是禁止回娘家,只有等初二晚上“送樹”后,初三才能回娘家拜年,據說是因為要避免讓有著外族身份或將有外族身份的“出嫁”的女兒沖撞了祖先,這可能與某種傳統的防范心理有關。
在除夕夜更是稍不注意便會“犯忌”。除夕夜一過零點,忌掃地洗衣、忌打碎物品、忌把水滴灑于地、忌看病吃藥、忌動針剪刀具、忌開箱柜等;尤其在“接神”之后,禁忌更甚,人們甚至不敢高聲喧嘩;只有等日出之后一部分禁忌才可解除。
此類禁忌既反映了人們在辭舊迎新之際的某些期盼和擔憂,又是人們為保證人神和諧、一年順遂所設置的層層準則。
2.3 本命年、逢九年禁忌
本命年在當地稱“流年”,當地有“流年不順”的說法;“逢九年”即虛歲為“九”的倍數也都不吉利,當地有“九九八十一難”之說。為應對此類特殊的時間節點,在此節點不論男女老幼過年必須穿紅色或黃色的內衣褲,穿紅色襪子,甚至紅色外套;與此同時,更講究的人會佩戴“銅鏡”。“逢九年”禁忌則更為嚴格,“逢九年”之人正月初一忌諱出門拜年,這一年都忌諱參加婚禮、葬禮等活動。
3 春節信仰活動的變遷
3.1 家庭祭祖活動的日漸消失
近年來,村民為圖方便省事,紛紛在過年時直接去祖墳祭拜,如今已很少有村民在家中“通樹”。通過調查可以發現,家中“通樹”仍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通樹將祖先以及逝去的親戚都接回家中,而且需要親自寫“樹”,在每一年的書寫與通樹的過程,都是后輩子孫對家族祖先熟悉的過程,每一年的通樹也在不斷地強化著祖先與家族的聯系;如果舍棄這一傳統而直接去墳地祭拜,這樣的家族氛圍會逐步被淡化,最終后輩的子孫也并不知曉每一座墳丘與自己的血緣聯系。
3.2 春節信仰活動的簡化
村辦小學的取消,使得絕大多數年輕家長選擇帶著孩子去縣城讀書,由此帶來的影響便是村落人口“空心化”。年輕人口的大量外出,使得鄉土傳統、民間信仰的傳承出現斷層,無法順利傳承;年輕人外出受到城市化的沖擊和影響,在孩子放假時回到村內,開學時便匆匆離去,缺少了村內生活的時間,而由于受到外部城市文化的影響,回到村內便覺得與傳統的繁復的鄉土文化、信仰活動格格不入,與鄉土文化產生距離感、陌生感,他們回到村內,更多的是強調快節奏、簡單辦,過完年或孩子開學時便又匆匆離去。所以如今村內過年很少講究“禁忌”,如打掃家不再講究在“送灶”之后;接神也不再為了能多加幾爐香而早起,更有人為了能多睡一會兒,在十二點就接完神回屋睡覺,沒有了給神連續上香的講究。
3.3 春節信仰活動與民眾生活
“過年”是當地最熱鬧、民眾最為期待的節日,它積聚了人們一年的情感與期待,經過充分準備,集中爆發,最終逐漸歸于平淡。當人們約定俗成地以“忙年”、“過年”的形式進入春節獨有的情境之中,諸多年俗在民眾生活中一次次地重復上演,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神、人與祖先溝通交流的神圣時空得以構建,中華民族的神圣意識得以傳遞,神圣傳統得以強化。
這些儀式、信仰傳承的背后,是民眾發自內心的需求:人們通過與神靈、祖先的溝通,祈求一年的風調雨順、人壽年豐;通過崇神敬祖的一系列活動,完成了這一特殊“過渡時間”的狂歡;通過種種禁忌,心靈得到慰藉,情感得到寄托。
由此看來,“過年”這一時期,通過信仰活動與禁忌儀式,使人與神、人與祖先得以溝通交流,日常世俗生活與神圣空間得以同生共存。民眾在此期間,既忙碌又消閑、既謹小慎微又滿懷期待,復雜的情感加上種種神圣的習俗、儀式與禁忌,構成了當地特有的“年味”。
如今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年味”越來越淡,人們普遍感覺“過年”越來越隨便。隨便的背后,是短暫的春節假期使人們少了“忙年”、“過了臘八就是年”的長時間準備,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人們少了“通樹”、“接神”的種種儀式禁忌,神圣與日常失去了明確的劃分,“祭灶”、“接神”、“通樹”等文化元素也不再神秘莫測,“人神同住”的“過渡”時期、“敬畏與狂歡”的復雜心理也歸于平淡。抽離了傳統“過年”中的信仰部分,人們總感覺這并不是“過年”。因此如何傳承傳統春節多樣的信仰習俗與活動,營造出莊重肅穆與歡快熱鬧兼具的新“年味”,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忽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周巍峙.中國節日志·春節(山西卷)[M].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
[2] 蕭放.文化遺產與文化資源——現代語境下的春節習俗意義[J].江西社會科學,2006(02).
[3] 蕭放.春節習俗與歲時通過儀式[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6).
[4] 高丙中.作為一個過渡禮儀的兩個慶典——對元旦與春節關系的表述[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01).
[5] 宣炳善.春節與端午節的節日信仰及其類型[J].文化藝術研究,2009(05).
[6] 張士閃.春節:中華民族神圣傳統的生活敘事[J].河南社會科學,2010(01).
[7] 段友文,王旭.崇神敬祖、節日狂歡與歷史記憶——山西娘子關古村鎮春節民俗調查[J].文化遺產,2012(04).
[8] 李國江.春節與禁忌信仰[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