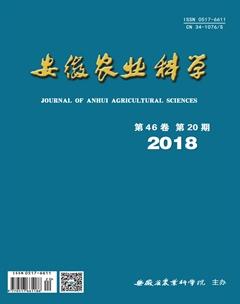征地補償中農民間接損失的量化研究
董子瑄 仝照民 高心雨
摘要 以征地補償中農民間接損失及其量化為研究對象,重新界定征地補償的范圍,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的生態價值及社會保障價值列入到補償范圍內,并運用收益還原法、成果參照法等數學方法測算農民的間接損失,建立間接損失評價體系。以長春市為例,將上述評價體系運用到實踐中,得到長春市各區縣農民間接損失補償的具體數值,分別與其現行征地補償水平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長春市各區縣農民的間接損失補償均高于現行征地補償水平,證明了對農民間接損失進行補償的必要性,并為重建科學、合理、公平、高效的征地補償制度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關鍵詞 征地補償機制;間接損失;量化;失地農民
中圖分類號 S-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8)20-028-03
Abstract Take indirect losses of farmers and its quantitative in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define the scope of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put the land contracting and management rights, land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value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compensation scope, using the method of income reduction and the method of outcome reference measure the indirect losses of farmers, and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ystem. Taking Changchun for example, to apply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practice, get the specific value of indirect loss compensation for farmers in Changchun City, and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compensation level of land expropr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irect loss compensation of farmers in Changchun were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levels, proved the necessity of compensation for farmers indirect losse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asonable, fair and efficient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Key words L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Indirect loss;Quantitative;Landlost farmers
我國現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征地范圍、補償標準、征地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1-4],其中,征地補償范圍問題尤為嚴重。目前國內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征地補償范圍的定性研究上[5-8],而對征地補償范圍內各補償的具體量化卻少有涉及,筆者在重新界定征地補償范圍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
1 間接損失范圍的界定
1.1 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范圍 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征收土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土地補償費是對被征地農民喪失土地使用權的補償;安置補償費是保證農民在喪失土地一段時間內維持現有生活水平的費用;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是對被征土地上的農作物和無法遷移的水利設施、房屋等建筑物等的補償。其中,土地補償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為對失地農民損失的權益性補償,而安置補助費則是對農民的保障性補償。根據上述分析可知,這3項補償費用均為對土地征收的直接損失的補償。
1.2 間接損失范圍的界定
根據“以人為本”的思想,以維護農民權益為根本出發點,綜合考慮農民的生活現狀,筆者認為征地補償范圍應在原有基礎上補充以下3項: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的社會保障價值和土地的生態價值。
1.2.1 土地承包經營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實際上是承包人通過利用土地而長期獲取收益的權利。土地被征收,農民就無法繼續通過土地獲取利益,從而失去其權利,因此政府應對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補償。
1.2.2 土地的社會保障價值。
土地是農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依托。失地后,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方式,又很難迅速找到新的獲取收益的途徑,再加上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在不斷上漲的物價面前,農民的生活難以得到保障。
1.2.3 土地的生態價值。
土地具有產生與維持生物多樣性、調節氣候、凈化環境等多種功能,其生態價值有益于整個社會,農民既是土地生態價值的提供者又是社會的一份子——受益者。失地后,農民失去了享有土地生態價值的權利,因此政府應對其權利進行補償。
2 間接損失量化模型的建立
2.1 土地承包經營權
2.2 土地的社會保障價值
國家對失地農民征地補償的出發點是使其生活水平與征地前相比不降低,則假設將失地農民納入國家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即全國基本統一的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假設農民轉為居民后,其收入不變,則繳納的社會保障費用以當時的收入水平為基數,因此用當時的農民收入水平乘以社會保障繳費費率可以計算出每個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再乘以單位面積土地需要保障的農村人口,得出單位面積土地需要繳納的社會保障費用[9],采取收益還原法計算出土地社會保障價值,如式(3):
2.3 土地的生態價值
對于土地生態價值的量化,結合實際,該研究采用成果參照法。成果參照法是基于特定地區或國家運用各種方法已獲得的實證研究結果,通過適當調整后,轉移到待研究地區,從而得到政策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價值[10]。該研究主要借助謝高地等[11]的研究成果,并結合該研究實際,在其基礎上加以調整,得:
3 補償歸屬的確定
“2.1”“2.2”“2.3”計算的3項土地間接損失并不全部歸失地農民所有。
我國法律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為農民集體組織共同享有,因此失地農民獲得的賠償應該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價值中的一部分。由于國家對農民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沒有明確規定,結合當前實際,該研究采用部分省的規定,即土地補償費在集體組織和承包農戶間按照3∶7的比例分配。
耕地附近一定范圍內的村鎮居民均能受益于農民耕作農用地所產生的生態價值,而農民是農用地生態價值的創造者和保護者,是生態價值補償的主體,耕地被征收后承包農戶失去了生態補償的機會,所以,耕地生態價值應在村鎮居民與承包農戶之間分配。筆者認為在土地的生態價值補償中,歸屬農民的補償因子為該失地農戶人口與該村鎮總人口的比值。
4 征地補償體系的建立
該研究以長春市為例,將上述量化方法運用到實踐中,并與現行征地補償標準進行對比,嘗試將間接損失補償納入現行征地補償中,探索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評價體系。
4.1 數據概覽
該研究采用稻谷、玉米、大豆和花生4種農作物來計算長春市各區縣的農產值。4種農作物產品單價分別為稻谷1 512.3元/t,玉米1 003.3元/t,大豆2 007.4元/t,花生2 761.3元/t。其中,農作物總產量、農作物單價的相關數據來自《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各區縣農村人口,農村戶數,耕地面積的數據來自《長春統計年鑒(2016)》,現行征地補償標準來自各區縣的人民政府文件《關于公布征地補償標準的通知》,具體數據見表1。
4.2 耕地3項權益價值計算
4.2.1 耕地承包經營權價值。單位面積土地的純收益為農作物總產值與土地總播種面積的比值,土地資本化率采用年期存款利率3.6%加風險調整值確定。征地具有強制性,相對風險較小,綜合國內風險調整利率,采用1.0%進行風險調整,則最終土地資本化率r為4.6%。把上述數據代入公式(2)中,計算得到耕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
4.2.2 耕地社會保障價值。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要求城鎮居民按照本人工資收入繳納各種保險,包括醫療保險(個人繳納2%、單位繳納8%)、養老保險(個人繳納8%、單位繳納12%)、失業保險(個人繳納1%、單位繳納2%)、工傷保險(單位繳納1%)、生育保險(單位繳納1%)、住房公積金(個人繳納3.5%、單位繳納3.5%),其中個人繳納總計為工資收入的14.5%,即社會保障費率為14.5%。單位面積土地需要保障的農村人口為農村總人口數與耕地面積的比值。根據《長春統計年鑒》,2015年農民平均年收入為11 749元,把上述數據代入公(3)中,計算得到耕地的社會保障價值。
4.2.3 耕地生態價值。根據謝高地等[12]的研究成果,我國吉林省農田生態系統生物量因子為0.96,7類生態服務價值生物當量因子(不含食物生產和原材料生產2項)的總和為5.81,計算Ea的值,并代入公式(4),計算得到耕地的生態價值。
耕地的3項權益價值見表2。
由表2可知:
(1)長春市各區縣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土地的生態價值起伏趨勢基本一致且波動較大。其中榆樹市的2種權益價值分別為139.85萬和111.39萬元/hm2,相對其他區縣明顯增高,是權益價值最低的市轄區的1.5~2.0倍。榆樹是長春著名的產糧大市,由于其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每年農作物總產值都遠高于其他地區,因此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價值也相應較高。
(2)長春市土地的社會保障價值表現較為平穩,且整體補償水平較低,只有市轄區內超過20萬元/hm2。原因是該研究計算耕地社會保障價值的公式建立在農民的生存發展基礎上,長春市內轄區經濟相對發達,增值空間高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其他區縣,因此呈現由中心向四周遞減的分布規律。
(3)長春市土地權益價值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價值和生態價值為主,兩者占到總價值的 95%,而社會保障價值僅占5%。但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和生態價值補償均不全部歸屬于失地農民,尤其是生態價值補償,由于補償因子系數很小,農民只能獲得其價值中的很小部分。
(4)結合區域要素分析,長春市內經濟發展形勢是以長春市為中心,并向四周遞減。農安、九臺、德惠分別不同程度的與長春市轄區相鄰,而榆樹市并無直接接觸長春市區。基于此,該研究認為在征地補償中,征地損失或與距市轄區距離有關。具體表現為距離市轄區距離越近,耕地所產生的間接價值越低,而更多的表現為直接價值,相反距離市轄區越遠,則會產生更多的間接價值。
4.3 征地補償中農民間接損失的量化 將表2中3項權益價值計算結果代入公式 ,得到長春市各區縣失地農民所得間接補償費,與長春各區縣現行征地補償對比,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長春市各區縣農民的間接損失補償均高于現行平均補償水平,尤其是榆樹市在征地時補償標準較低,且該地區農民間接損失較大,如果不能及時提高標準將引起失地農民的不滿,影響社會安定。在進行征地補償時,耕地3項權益的剝奪使農民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直觀地表明了當前我國普遍使用的“產值倍數法”已經無法給與農民正當合理的征地補償。為了實現社會公平和土地的等價交換,政府應積極將間接損失納入征地補償體系內,希望該研究論證可以為其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5 結語
征地補償是當前征地的核心問題,合理的量化征地補償更是重中之重。該研究從維護農民根本權益出發,在研究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征地補償的范圍,并運用科學合理的方法對失地農民間接損失進行量化。結合長春市實際征地情況,對建立科學合理的征地補償體系進行討論研究,證明了對農民間接損失進行補償的必要性,為重建科學、合理、公平、高效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參考文獻
[1] 李中.我國征地制度:問題、成因及改革路徑[J].理論探索,2013(2):105-108.
[2] 錢中好,牟燕.征地制度、土地財政與中國土地市場化改革[J].農業經濟問題,2015(8):8-12,110.
[3] 張紅,于楠,譚峻.對完善中國現行征地制度的思考[J].中國土地科學,2005,19(1):38-43.
[4] 羅美琴.征地補償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08:2-3.
[5] 申建平.對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范圍的反思[J].比較法研究,2013,27(2):100-109.
[6] 畢建超.國內土地征收補償范圍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J]. 山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6):104-107.
[7] 張紅.我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的問題與對策[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6(14):5-7.
[8] 張麗麗,劉峰.我國土地征收補償范圍與標準之探析——兼談土地行政征收中的權利保障[J].生態經濟,2011(3):117-120,151.
[9] 陳春節,佟仁城.征地補償價格量化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13(1):41-47.
[10] 吳欣欣,陳偉琪.成果參照法在自然生態環境價值評估中的應用現狀及展望[J]. 環境科學與管理,2012,37(11):96-100.
[11] 謝高地,魯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態資產的價值評估[J].自然資源學報,2003,18(2):189-196.
[12] 謝高地,肖玉,甄霖,等.我國糧食生產的生態服務價值研究[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5, 13(3):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