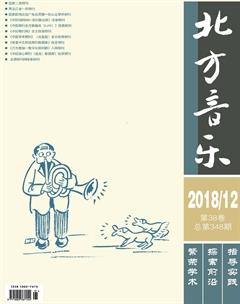《說文解字》音樂文字釋例解讀
李小虎 成海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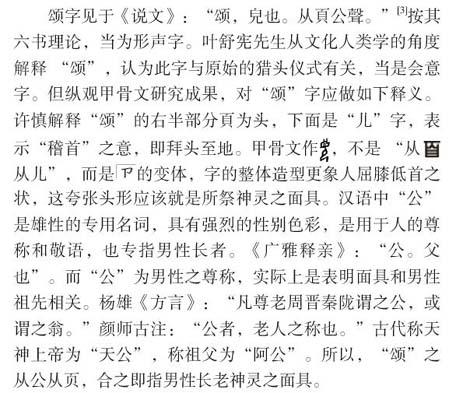
【摘要】《頌》是周王室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是詩、樂、舞三位一體文學樣式的早期文本體現,其詩、樂、舞三位一體的功能體現出先秦時期豐富的禮樂文化。本文從頌的字形字義分析入手,探討頌字以及頌詩后面隱藏的的政治文化功能。
【關鍵詞】《頌》;音樂文字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一、“頌”字形分析
據材料顯示,“頌”字最早見于金文,據容庚先生 《金文編》與徐文鏡編著的《古籀匯編》,其字形大致有頌鼎、史頌匝、蔡疾盤、說文籀文這幾類寫法。[1]古今學者對“頌”字本義的探討,大多是以“誦”“容”二字為主,[2]其他諸說多由此二項派生而來。隨著近現代學者對頌詩研究的不斷發現,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需要對“頌”字再做討論。
(一)頌
頌字見于《說文》:“頌,皃也。從頁公聲。”[3]按其六書理論,當為形聲字。葉舒憲先生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解釋 “頌”,認為此字與原始的獵頭儀式有關,當是會意字。但縱觀甲骨文研究成果,對“頌”字應做如下釋義。許慎解釋“頌”的右半部分頁為頭,下面是“兒”字,表示“稽首”之意,即拜頭至地。甲骨文作,不是 “從從兒”,而是的變體,字的整體造型更象人屈膝低首之狀,這夸張頭形應該就是所祭神靈之面具。漢語中“公”是雄性的專用名詞,具有強烈的性別色彩,是用于人的尊稱和敬語,也專指男性長者。《廣雅釋親》:“公。父也”。而“公”為男性之尊稱,實際上是表明面具和男性祖先相關。楊雄《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顏師古注:“公者,老人之稱也。”古代稱天神上帝為“天公”,稱祖父為“阿公”。所以,“頌”之從公從頁,合之即指男性長老神靈之面具。
由以上分析可知,“頌”字本義其實是一個人在屈膝低頭說話,屈膝低頭表示恭順,進而可知“頌”的本義即為言者恭順謙卑地向對方訴說,儀態是屈膝低首,恭敬虔誠。
(二)頌與誦
字源學將“誦”字分解為左“言”右“甬”。《類篇》:“言,訟也。”本義為訟詞,引申有直言義。“用、甬”音聲相近,“用”字是鐘的象形,“甬”即是鐘。《禮記·月令》:“角斗甬。”鄭玄注:“甬,今斛也。”按其推論,“斛”就是“甬”,其形狀類似于鐘。
鐘常常被古人取用為“大音”之義。《釋名·釋樂》解釋鐘因其中空,音響渾厚,故聲音宏大。《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鐘,音之君也。”因其聲音宏大渾厚,所以排在首位。由此推測,誦的本義應為大聲直言,述說,甚至是言辭鑿鑿之申訴,而并不單指宗教祭祀中與神靈溝通的語言。主持祭祀者的巫史在宗廟祭祀時口誦祝告之辭即為“誦”。如《襄公三十一年》:“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這里的“誦”即為頌揚文王之德。
古代學者鄭玄還對其做了聲訓:“頌,誦也。”如《孟子·萬章下》所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朱熹因其字聲音相近而使用假借并義訓為“頌、誦,通”,強調祝禱者念頌的動作。盡管聲訓、義訓含義不同,但“頌”字的主導意義仍是溝通神靈、彰顯祖先之德行。
(三)頌與容
后世學者對“頌”的注解中還有“容貌”一說同樣值得重視,影響深遠的是清代阮元《釋頌》的“舞容說”,由于缺乏直接的證據而未成定論。清華簡的問世,為阮元的“舞容說”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也使得阮元的“舞容說”成為事實。[4]再回朔先秦有關文獻便可了解“頌”體現為舞容的詩篇文獻多有記載。《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這里明確指出,“舞,動其容也”。又《荀子·樂論》:“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是先王立樂之術也。”這就是先秦時期雅頌之“舞容”,其表演過程體現出禮儀典章制度的赫赫威嚴。
綜上所述,“頌”字當為會意字。“頌”的本義是恭順地與神明溝通,因而必須虔誠恭敬、肅穆莊嚴,祭祀過程的視角是仰視的,不敢怠慢。由此可見,“頌”之基本內涵是下對上的稱頌贊揚。
二、頌的政治文化功能
(一)宗教
頌原是宗廟祭神時所唱的樂歌,內容是歌頌神靈,祈求神靈保佑。《毛詩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后來用文字記錄下來便是“頌”。古代祭祀與戰爭乃頭等大事,祭祀作為一種宗教儀式,其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神靈的庇佑。祭祀詩就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贊頌神靈、祈福避災的詩歌。
《詩經》中的祭祀詩歌大多是用祭祀歌曲來表演的,符合早期音樂歌、樂、舞三位一體綜合表演形式,音樂的場面壯觀、威嚴。所有這些和原始時代的巫祝關系密切。巫祝是溝通上界神靈的使者,地位顯赫職責重大,而能歌善舞就是其部分職能的重要體現。《說文解字》說:“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可見巫舞淵源甚深。所以,在宗教祭祀活動中,歌舞的表現異常的突出。如《商頌·那》:“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上述文獻是祭祀祖先商湯并述其功德的祭祀歌曲,場面是鼓樂齊鳴,氣氛異常的莊嚴。湯王的子孫后代就在聲調和諧莊重肅穆的氛圍之中禱告列祖,以祈求得到先祖護佑。再如《周頌·有瞽》是描寫作樂的篇章,是表現周王祭祀先祖時樂隊齊奏的盛況,鄭箋以“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釋之。《周頌·有瞽》不僅表現了周朝音樂成就的輝煌,而且也顯示了周人“樂由天作”可以溝通人神的宗教觀念。
商周時期,隨著文化意識從“神”向“德”的轉變,宗法祭祀制度成為祭祖的核心。《詩經》中的祭祀詩中就有描寫子孫后裔祭祀祖先的詩篇。如《周頌·維天之命》:“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工,曾孫篤之。”這是以文王曾孫口吻敘寫的祭祀文王的詩歌。前四句是對文王的德行描述,意思是文王之德至高而完美,以至高無上的天命相比,永垂后世。后四句是在描述祭祀者渴望先祖把德行與福祉降臨到自己身上,子孫后代定不忘祖先遺德,誓將其德行發揚光大。
頌詩樂章所表現出的人神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祭祀詩歌都在尋求一種和諧的因素,徐復觀先生說,中國文化“走的是人與自然過分親和的方向”。[5]這種描述人與神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周代禮樂文化興盛所反映的和諧篇章,在頌樂章中也筆墨頗多。這些描寫祭祀的樂歌,其內容大都是祭祀先祖和頌其德行,先王的文德武功,諄諄教誨昭告時王以享后人,“神人以和”的宗教意味不言而喻。
(二)政治
在祭祖的歌頌中也存在著政治目的和功利觀念。祭祀時人們都希望得到神靈的庇佑而生活安康,但統治者是上天神靈的代表,其保留宗教形式的意義自不待言,諸多的祭祀儀式就成為統治者達其目的工具。祭祀詩中很多作品都體現出統治者的政治目的。學者朱狄認為:“古代的祭禮儀式往往具有立法意義,故《說文》:‘儀,度也。所謂度,也就是法度。在祭禮儀式中,無論朗誦、音樂、舞蹈,都具有一種社會強制性。它們的合成結構是一種社會性非常強烈的文化結構。使意義變得更清晰,更容易接受。”[6]這些具體的儀式儀容體現出的就是頌的政治的功能。
商頌中《那》《列祖》詩篇就是通過儀式儀容來達其政治功能即教化目的的樂章。就其祭祀中的歌舞表演來說,則是通過祭祀中像“俯仰屈伸”“容貌得莊”“進退得齊”“行列得正”[4]等這些動作,來表現君臣上下、倫理秩序和神態儀度,使得上下和諧,秩序井然,這些“威儀”之態體現出的就是頌的政治功能。
再如《詩·周頌·執競》:“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威儀反反”就是舞容,再與“鐘鼓喤喤。磬筦將將”相配合,鐘鼓齊鳴,樂聲和諧,主祭者屏神靜氣,祭祀在樂的背景下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進行,盡顯“威儀反反”的儀態,莊重肅穆,其政治目之功效可見一斑。《禮記·樂記》云:“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因此,祭祀活動中虔誠肅穆之心要貫穿祭祀的始終。除此之外,祭祀還對參祭者的容貌儀態、身形步法等都有具體規定,如此一來,禮樂相輔相成,方能體現祭者之義。
由以上分析可知,頌詩中禮樂文化的表現也是比比皆是,從頌詩中可以看出其內在的善與美,可以看出政治與音樂的完美結合,倫理教化之美盡顯禮樂之和,一方面體現出尊卑有序、內外有別的和諧的一面,另一方面還表現了尊祖頌德的美德,即“禮樂相和”方能國泰民安。
參考文獻
[1]段立超.“頌”字本義新考[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6(02).
[2]張啟成.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詩經頌詩新論[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3]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江林昌.由清華簡論“頌”即“容”及其文化學意義[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03).
[5]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自敘[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6]朱狄.信仰時代的文明[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作者簡介:李小虎,甘肅定西人,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音樂史、音樂教育理論等研究;成海霞,甘肅秦安人,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戲劇文學理論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