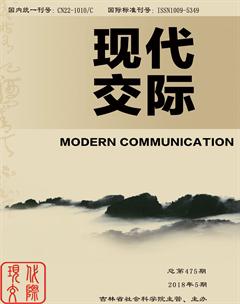論布依族作家羅國凡小說中的婚戀儀式
向紅
摘要:儀式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布依族作家羅國凡的小說再現了本民族獨具特色的婚戀儀式,如體現自由戀愛的“玩表”儀式,代表舊婚俗的“坐家”儀式,張揚民族品性的嫁娶儀式等。作品中布依族儀式的再現不僅弘揚了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推動了文本情節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題的升華。從儀式角度切入研究,拓展了羅國凡小說探討的視角,也有助于揭示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關鍵詞:布依族 羅國凡 說婚戀儀式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05-0102-03
出現于19世紀的“儀式”一詞,起初是人類學中的一個重要術語,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步與各學科發生關聯,其中與文學的關系尤為密切,有學者曾表述“儀式與文學述行密切相關,是文學述行的載體”。[1]P61那么,何謂“儀式”?關于其定義國內外學者表述各異,眾說紛紜。其中,運用較多的是郭于華先生對“儀式”的界定,即“儀式是在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支配下,規定形成具有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套行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情境與場合之下神圣莊嚴的儀典,亦可以是具有功利性質與目的的世俗禮儀與做法。也可將其理解為歸約傳統的、具有約定俗成性質的一整套生存技術,抑或被國家意識形態所采納并運用的一套權利技術。”[2]P1-3本文擬從儀式角度切入研究布依族作家羅國凡的小說,具體探討其作品中婚戀儀式的主要表現形式、文化內涵以及在小說中的意義等。
“儀式是文學與人類學研究的共同鑰匙。”[3]布依族作家羅國凡于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說,以布依族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描繪布依山寨風光、風土人情,表現布依族人們的生存境遇,再現了豐富多彩的民俗儀式。在眾多的儀式中,其作品著墨較多的是布依族的婚戀儀式,如體現自由戀愛的“玩表”儀式,代表落后婚俗的“坐家”儀式以及展現民族品性的嫁娶儀式等。文本中的再現性儀式,不僅推動了小說情節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題的升華,也揭示了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一、“玩表”儀式:體現自由戀愛、塑造人物形象
從儀式的程序性、結構性層面來看,“玩表”是布依族婚戀儀式的開始。“玩表”,“布依語稱之為‘浪哨(yeonosu),漢語稱呼各地不一,謂之‘唱歌‘趕表‘打老表‘鬧門墻‘坐表等。”[4]p4它是布依族青年婚戀社交行為的主要方式,一般多在布依族趕場天或重大節日(六月六、三月三)中進行,布依族適婚青年男女擇寬敞明亮的場壩一隅或山坡一角為場所,以歌為媒,尋覓意中人,以促成婚配。“玩表”儀式展現了布依族青年男女求愛方式富于浪漫色彩,其婚戀狀態為自由戀愛。這種獨具特色的婚戀儀式在布依族作家羅國凡的小說中被大量的重復,幾乎滲透于作者每一篇作品中。如短篇小說《三月三》《崖上花》《“勒友”聲聲》《不生效的結婚證》《月掛竹梢頭》等。在其眾多描寫布依族“玩表”儀式的小說中又以《不生效的結婚證》最具典型性。
在小說《不生效的結婚證》中,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將布依族的“玩表”儀式進行了全景式的直接再現。文本采用回憶的敘事模式表現了布依青年男女“玩表”開始時的互相和歌,接著男孩子們“扯幾篇木葉放在手心打彈聲,表示友好的召喚;姑娘們也用花帕摔著弧形表示歡迎”。[5]p133-134當雙方距離較近時則向意中人拋打“牛肚包”,儀式進一步發展則需雙方派人進行搭橋表明“玩表”對象,“當協議達成后,便一雙雙一對對地四散而去。巖腳下,泉水邊,樹腳下,一切適宜談情說愛的地方,都能聽到愉悅的細語和輕柔的吟唱……”[6]p134作品中“我”和細蕓就是本次“玩表”相識相戀的一對,他們從此開始了趕場天、節慶時赴約,互相對歌盤問,以歌盟誓,交談心聲,憧憬未來。“儀式,自古以來就是溝通人與神、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行為方式,也是人實現思想、情感、信仰和靈魂的一種重要交流媒介。”[7]p29-32在羅國凡的小說中,體現自由戀愛的“玩表”婚戀儀式是布依族青年男女自我與他者、個人與集體的交會,也是個人實現愛情、婚姻的重要途徑。布依族不少青年男女在此儀式中找到了個人的歸宿,并擁有完美的結局如《阿吉的煩惱》中的阿吉與阿葛、《“勒友”聲聲》中的阿冠與阿柳等。但也存在因受布依族戀愛自由、婚姻由父母做主的觀念制約在“玩表”中相戀但“有情人未成眷屬”的青年,如《月掛竹梢頭》中的韋松與竹妹、《崖上花》中的阿倍與阿芹等。
小說中的“玩表”儀式不僅體現了布依族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還在儀式敘事的進程中塑造了一批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因為“儀式是一種敘事,與文本構成相互關系,在敘事過程中它成為展現人物性格或人性的最佳場所”。[8]p33在羅國凡眾多的小說中以《“勒友”聲聲》最富于代表性,小說具體通過“玩表”儀式揭示了三位青年的本性,展現了各自的性格特征。作品中阿柳與阿冠本是于“玩表”中相戀的情侶,但青年阿婁由于在“玩表”中求愛阿柳未遂便心生記恨,將阿柳為了嚇唬流氓情急之下隨口編造的“我會放蠱”之語在左鄰右舍中散播開來,導致阿柳變成人人避之不及的“蠱婆”,阿冠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久久不與阿柳約會,阿婁趁虛而入與陷入絕望的阿柳訂婚。最終,阿婁在阿爹的影響下解除了人們對阿柳的誤會,阿冠也在阿媽的點撥下覺醒,三人間的感情又恢復了常態。文本以“玩表”儀式為線索,展示了三人之間的糾葛,將阿柳的聰慧貌美、善良機智,阿冠的忠厚老實、缺乏主見以及阿婁的富于心計、編造謠言的性格展露無疑。此外,羅國凡的其他小說通過“玩表”儀式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還有《月掛竹梢頭》中品行端正、樂于助人、受制于道德約束的青年教師韋松與美麗勤勞、落落大方的竹妹,《不生效的結婚證》中剛愛敢恨、反抗無力的細蕓,《崖上花》中勤勞無私、一生受制于錯誤政策壓制的阿倍與執著、專一但面對現實又無可奈何的阿芹等。
二、“坐家”儀式:批判舊俗、升華主題
“坐家”儀式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婚戀儀式,又稱“不落夫家”“常住娘家”。此儀式是指在舉行結婚儀式后,新娘不在夫家居住,結婚當日或之后二三日隨送親隊伍一同回娘家或由新郎家派人送回娘家。新婚期間夫婦不允許同房。之后,只有在節慶之日或農忙之時夫家派人去接女方方可回夫家,女方有的當天去當天即回娘家,有的也在夫家小住幾日,此時夫妻可以同房。女方“常住娘家”少則兩三年,多則七八年甚至長達數十年。據了解,“布依族以‘常住娘家為榮,以剛結婚就‘落入夫家為恥,在娘家居住時間越長,女方名節及其家族受到的美譽越多。”[9]p6“常住娘家”以男方派人成功給女方戴假殼儀式[10]p109或女方懷孕而終結,從此女方“落入夫家”開始“坐家”。隨著社會的發展,此種婚戀儀式已經顯示出其不合理性,不能滿足青年男女對婚姻、對家庭的需求、責任與意義,在布依族地區其已經逐步退出歷史的舞臺。
羅國凡的小說對布依族婚戀儀式中落后的“坐家”儀式也有描述。“所有的儀式都是一種語言,因此它傳遞著各種各樣的觀念。”[11]P75相對于先前對再現布依族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玩表”儀式的謳歌、提倡,這里作者對“坐家”儀式傾注更多的是批判、憎恨的情感。像小說《阿吉的煩惱》中,阿吉與母親相依為命,好不容易與阿葛成婚,阿葛又“常住娘家”。阿吉既要照顧年邁體虛、病魔纏身的母親,又要下地干活,還要面臨無錢為母醫病,缺衣少糧,八方催債等困境。家中所有大小事務全由阿吉一人操勞,他急需妻子的幫助,但礙于傳統婚俗的限制他的愿望一時不能達成。阿葛想來協助阿吉但她囿于傳統習俗也是身不由己。此時“坐家”儀式無疑已成為捆綁青年男女組建正常家庭,過幸福生活的枷鎖。另外,作者在小說《不生效的結婚證》中同樣也對以“坐家”儀式為代表的落后婚俗進行了鞭撻。作品中細蕓與“我”本已在“玩表”中盟誓定終身,但父輩們一方以“同姓不開親”為由,一方以胎前婚為理將“我們”間的姻緣拆散,細蕓被迫嫁給了父母胎前就為其選好的小她四歲并也有意中人的丈夫。與前文相反,細蕓的父母擔心其婚姻有變不但不讓她“常住娘家”,反而拿著竹棍趕他去丈夫家“坐家”,細蕓“坐家”后郁郁寡歡,憂郁成疾,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間。細蕓成為舊習俗、舊觀念的犧牲品,同樣因為傳統舊俗也直接葬送了四個布依族青年的幸福。
“文學通過對儀式、風俗、傳統的描寫。呈現出社會和時代的特點,并界定出人物的角色。”[12]p73以上兩部作品中展現的布依族“坐家”儀式,表現了布依族人們生活的社會和時代特征以及儀式對人的命運的影響,令人欣慰的是,通過儀式也界定了女性角色、女性意識意識的復蘇。阿葛在了解到丈夫阿吉面臨的煩惱以及整個事件的原委后,不顧世人的非議,果斷地在剛結婚兩個月之后就獨自一人來到夫家準備“坐家”,她要與丈夫共同面對困境,以解阿吉的燃眉之急。細蕓在與“我”交往受阻后,作為一個女人的她提出了逃婚的念頭,而“我”作為男性卻因沒有膽量面對逃婚帶來的惡果打破了細蕓的計劃,后來她又毫不猶豫地私下里與“我”辦理結婚證。最后她以結束生命來反抗無愛的婚姻,控訴傳統的婚戀習俗。阿葛與細蕓的所作所為均顯示了布依族女性意識的覺醒。
同時,“文學中的儀式書寫其實是作家在利用儀式來操縱人物和情節的發展”[13]p73以及達到升華主題的效果。羅國凡在其小說中通過“坐家”等婚戀儀式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如《阿吉的煩惱》中文本最后借阿葛前去夫家“坐家”之時對其阿媽的勸誡點明了文本的主題:布依族地區結婚時女方向男方收取高昂的禮信錢,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災難性的打擊,影響家庭生活,影響婚姻幸福。同樣,《不生效的結婚證》伴隨著細蕓生命的消逝作者最后憤恨地吶喊:“那些還搞胎前許婚或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的人,不要再給年輕人制造苦惱了吧?!還有那些沒有道理的民族風俗,五百年前訂的寨規也應當結束了!”[14]p149以及文本中作者多次強調的民族地區民族風俗力量大于法律效力等主題思想均是在特定儀式背景中得以升華。
三、嫁娶儀式:再現民俗、張揚品性
“布依族是一個沉湎于儀式中的民族,如所有的儀式都舉行,一年有將近43個儀式。”[15]5p5婚戀儀式作為整個布依族儀式系統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其在布依族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自不待言。“傳統的布依族婚俗規程由‘浪哨(‘玩表)、提親、議親、訂親、結親以及‘不落夫家(‘坐家)6部分組成。”[16]p2-3每一部分婚俗儀式中又包含著眾多程序,對于“玩表”與“坐家”上文已有詳細的論述,對于布依族婚嫁儀式中的其他四項規程,羅國凡在其小說中也有敘寫,再現了布依族多姿多彩的婚俗文化。如小說《月掛柳梢頭》《不生效的結婚證》中對布依族婚俗中青年男女在“玩表”確定戀人關系后,由男方請媒人“提親”等均有或隱或顯的描寫。“提親”“認親”等儀式在小說《阿吉的煩惱》中有不同的表述:即“提茶”“燒香”“拜年”……這些儀式只是各地說法不一,其實質內容卻一致。在小說《女兒嫁到撒貫寨》中作者具體展現了布依族婚禮儀式上的各種習俗,像姑娘出嫁頭一天晚上要“吃姊妹飯”與寨中姐妹告別,男方吹嗩吶迎親以示對女方送親隊伍的尊重和歡迎,新女婿對岳父母鞠躬作揖、男方家內親敬“進門茶”,宴席中擺男女不同桌的“敬老席”等等。可以說,羅國凡通過其小說向讀者展示的是布依族嫁娶儀式大餐,再現了布依族的獨特婚俗文化。
人類學家涂爾干曾說:“儀式是在集合群體中產生的行為方式,它們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17]p134羅國凡通過其小說描寫布依族嫁娶儀式,一方面再現了布依族的婚俗文化,另一方面也通過儀式重塑了布依族人們的心理狀態,張揚了布依族人們的優秀品質。這集中體現在小說《阿吉的煩惱》與《女兒嫁到撒貫寨》中的阿吉母親與韋寡婦身上。阿吉母親身為寡婦,不僅將自家日子過得紅紅火火,而且將兒子的婚事也是準備得妥妥帖帖。如為兒子置辦體面、風光的前去未婚妻家拜年的物品,千方百計湊足女方家長臨娶之前附加的五百元禮信錢,就算東拉西扯也要高高興興地辦成兒子的婚禮等。她自強好勝一切均圍繞不叫人挑寡婦的長短,避免笑話“寡婦辦不成大事”“說寡婦蹩腳,辦事不像樣”。同樣,韋寡婦獨自一人拉扯兩個兒子,受盡欺凌,吃盡苦頭,但她善良本分、倔強堅韌,不僅將兒子養大成人,而且還蓋起了嶄新的三間瓦樓……加之韋寡婦在婚禮上有禮有節的表現,竟使漢族人改變了對布依族的偏見。可見,作者通過儀式將聚焦點集中在兩位寡婦母親的身上,彰顯了布依族真善美的民族品質以及熱情虔誠、自立自強的民族品性。
總而言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儀式是小說的靈魂,它具有特定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羅國凡在其小說中描述布依族獨具特色的婚戀儀式,并不是獵奇布依族民族風俗,它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布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書寫一方面可以傳承即將失傳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還可以思考布依族人民的生存樣態與集體無意識。同時,以儀式為視角切入,既拓展了羅國凡小說研究的空間,更新了研究視角,又有助于揭示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參考文獻:
[1]范捷平.文學儀式和面具的遮蔽功能——兼論異域文學中的“東方形象”[J].德語人文研究,2013(1).
[2]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葉舒憲.文學人類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4]楊昌儒.論布依族“浪哨”文化的演進[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增刊).
[5][6][14]羅國凡.崖上花[A].不生效的結婚證[C].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7]張兵娟.電視媒介事件與儀式傳播[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5).
[8]陳紅.新時期小說中儀式書寫及其意義——以韓少功、莫言為例[D].西南大學,2014.
[9][16]魏承源.黔南布衣族婚俗儀式審美探究[D].四川音樂學院,2017.
[10]陳明媚.論布依族婦女“不落夫家”婚俗的文化內涵[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
[11](美)羅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會人類學[M].吳玫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12][13]馬碩.人類學視野下的小說儀式書寫[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
[15]唐貴嘯.樸素:布依族儀式中的審美意識[D].貴州大學,2008.
[17](法)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吉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8]彭兆榮.文學與儀式:文學與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