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芳華
黃志新 黃瑋 余斌 葉木樓 周成貴 漆蘇敏 周傳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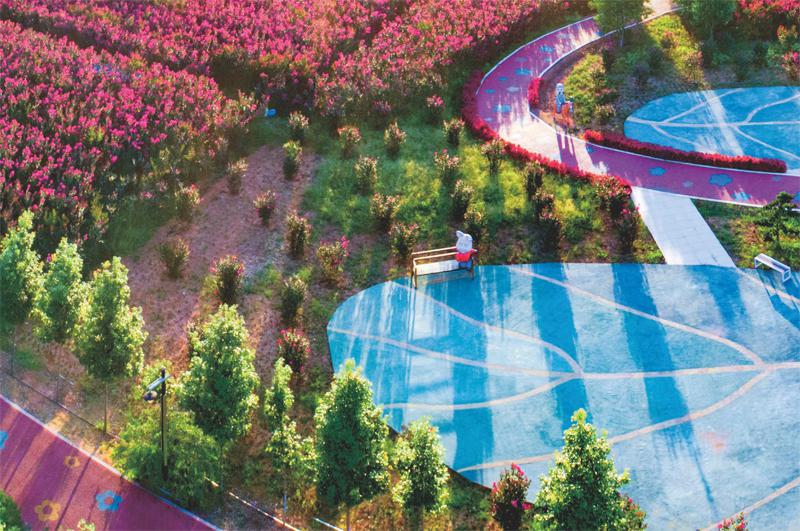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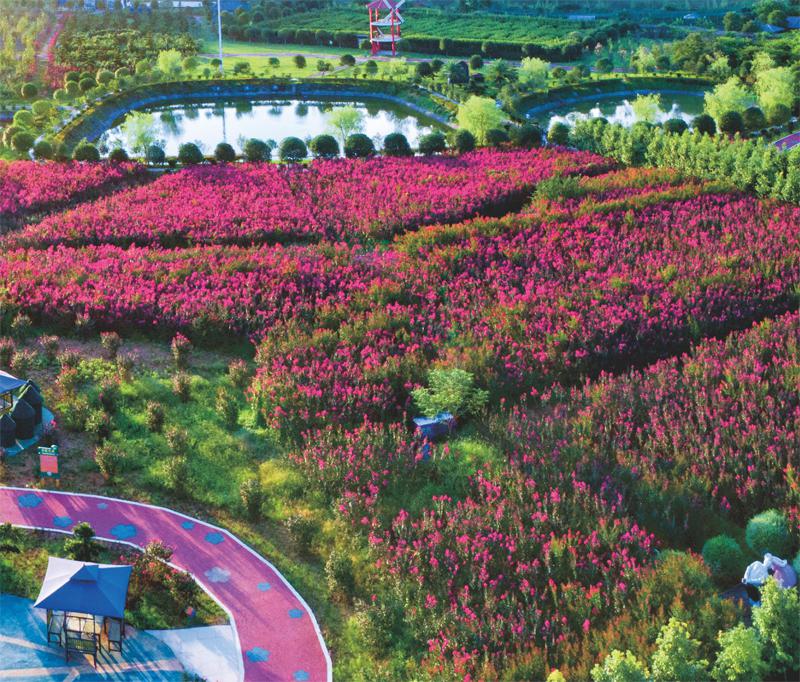

40年彈指一揮間。這期間,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旋律,更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城市地標、高樓大廈、大街小巷不斷舊貌換新顏,各行各業人群的百態眾生相,突發事件、隨手街拍更是考驗攝影人的眼力。
城市化演進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發展無論在發展規模還是在發展水平上都取得了矚目成就,特別是區域中小城市的進步尤為突出。
1978年3月,我國政府明確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基本方針,并于1989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再次重申了“嚴格控制大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方針。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盡管國家在此期間對城市發展方針略有微調,在具體政策表述上有些許變化,但對“控制大城市的發展規模”則是一貫如一的。顯然,該方針對我國后期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工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有效促進了國內中小城市的發展。據統計,1978年~1998年,我國城市數量由193個發展到671個,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鎮卻由2173個發展到18925個,增加了7.71倍,小城鎮的增加幅度遠遠超過了城市增幅。在此階段,我國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是經濟特區的設立使得深圳、汕頭、廈門和珠海4個城市獲得了巨大發展活力;隨后,在1984年,國家又相繼開放了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等14個沿海城市,這些沿海城市的區位優勢和潛能也迅速得到了釋放,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由此,“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大城市群雛形在我國東部和南部地區形成。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我國城市建設和發展也隨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但城市發展的總體格局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
一是受經濟聚合與外擴效應的影響,城市規模增長迅猛,大型城市數量大幅被突破,并出現了大量“特大城市”;二是大型及特大型城市的發展引起了普遍反思和重視。
隨著城市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多,一些大型或特大型城市數量也在自發性增多。然而,部分大城市的良性發展非但沒有出現令人生畏的“城市頑疾”,反而對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輻射帶動作用,并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的新局面。此現象引起了政府及學術界的反思,人們開始改變過去對“發展大城市”一貫否定的看法,肯定了其利好的一面,然而,這并不代表這個時期國家已經放開了對大城市發展的控制。相反,這個階段對大城市的發展要求仍是:一方面,積極控制大城市的市轄區規模,合理規劃和開發新區,發展衛星城來分散大城市的商業與居住功能;另一方面,要求大城市在自身資源優勢基礎上開始向更加集約化、特色化和可持續化的方向發展。基于以上要求,探索城市發展新模式的趨勢由此在國內較為領先的城市中出現。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發生與發展著的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2007年以來,隨著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國家級區域規劃和國家級創新試點城市規劃等政策的密集出臺,我國區域城市群已經借勢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截至2012年底,國內已經基本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遼中南、中原、長江中游、海峽西岸、川渝和關中等十大城市群。諸如南京、寧波和深圳等處在這些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已經紛紛走向新型城市模式的探索之旅,陸續提出了“智慧型城市”“知識型城市”等新的發展目標。可以說,當前,最值得關注和探究的問題是,這些城市在追求“群發展”與“特色發展”的道路上,如何選擇符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發展的關鍵議題之一。
都市出行變遷
改革開放之初,因為經濟實力和技術有限,當時人們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車外,絕大多數都騎自行車或步行。
20世紀80年代初,公交車開始全國普及,在上世紀8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公交車已經成為了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公共交通是城市的窗口和名片,作為市民出行首選的公交車,在最近幾年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十年前,公交車線路短而少、車輛少。如今,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城市從城市規劃、環境保護、節約能源、交通安全等方面出發,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的“公交優先”戰略的不斷實施,公交車的線路和車輛的數量都在不斷地增加,公交車車輛的檔次也在不斷地提升。公交車的作用在日益提升,方便快捷的公交車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橋梁。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摩托車由于它的方便、高效、省力等優點風靡中國。隨著社會的發展,它暴露出的問題也是越來越嚴重,諸如安全性差,尾氣對環境的污染等。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的交通工具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人們出行更快更便捷。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很多人具備了汽車消費的能力,不少市民告別了自行車、電動車、摩托車,將私家車作為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私家車的大量出現,改變的不僅是出行方式和效率,也改變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私家車具有很大的靈活性,私家車主不用風吹日曬去趕公交車,而且不用擔心工作時間的延誤,具有便捷高效的特點。另外,私家車的普及也從側面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
進入21世紀,地鐵成為城市快速軌道交通的先驅,也是現代節能環保的新產品,目前中國只有較大的城市才建有地鐵網絡。地鐵不一定在地下,也可以根據城市的具體條件,運行在地面或高架線路上。地鐵不僅運量大、建設快、安全和準時,還節省能源、不污染環境、節省城市用地。地鐵適用于出行距離較長、客運量需求大的城市中心區域。同時,交通工具在海陸空全面立體覆蓋,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沒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顯現,地球正在逐步地“縮小”。
城市轉型壓力
中國大多數城市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能夠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所釋放出來的政策紅利以及以低要素價格為主要特征的后發優勢。
但是,長期依賴后發優勢的產業升級雖能利用較低廉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借助于對所引技術的模仿性創新來降低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成本和依靠借鑒先發國家經驗大幅度削減制度創新的實驗、風險耗費,但易受先發國家或跨國公司的資本、核心技術、規則、專利等的控制與限制,且可能面臨較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和付出巨大的資源、環境成本,甚至長此以往可能被鎖定于低端技術路徑依賴的貧困陷阱和“引進→模仿→再引進→再模仿”的惡性循環之中,最終產業難以獲得持續升級,甚至出現停滯與倒退。
特別是以佛山、東莞為代表的出口加工業城市,當產業和技術的積累程度日益接近西方國家生產和技術的前沿時,就會引發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的警覺,從而進行技術和價值鏈的封鎖擠壓。
而與此同時,其他“金磚國家”“薄荷四國”和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政策優勢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FDI向其轉移,對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紡織服裝、筆記本電腦及其配套產業等形成了巨大的吸附影響。
過去幾年,諸如佛山、東莞等出口加工業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均出現小幅下降,轉型發展正面臨陣痛期。
就目前而言,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在創業氛圍和創新環境方面仍然面臨很多約束條件。各地通常將精力和優惠政策傾向于大企業集團、知名品牌,而對于草根創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關注不夠。雖然國家在2014年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創業的便利措施,但是創業難、融資難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
在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建設方面,各地主要面臨著高等教育質量不高、區域發展不均衡、專業人才供需失衡、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產業轉化率低、輻射功能相對不足等問題。
由于投入絕對值少、人才匱乏、以前的科技投入欠賬較多等原因,中小城市專利申請和論文發表數量極低,嚴重影響中國知識城市的全面轉型。
而在沿海發達地區,許多城市政府仍希望更強大的產業政策、數量化的轉型指標強力推動轉型,加大投資,保持增長。
從城市群到城市帶
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較具典型的區域城市群,例如,以北京、天津、青島和大連等城市為中心的環渤海灣城市群,以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和寧波等城市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以廣州、深圳、東莞等城市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等。未來,城市群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極有可能是,區域城市群呈現組團式發展,并隨著大城市群之間的互動而鏈接成區域城市帶。現實可以看到,隨著城際交通網絡的便捷化發展和區域內經濟集聚與擴散效應不斷增強,圍繞國家創新試點區的重新布局,新興產業正在各區域內興起并不斷向周邊溢出,區域內城市間產業分工與協作正在加深,經濟上更為密切的“紐帶”正在將不同城市整合成一個彼此協作但各具特色的城市帶系統。
我們以長江中游區域為例,目前,在此區域,已經基本形成了以武漢為核心的“武漢城市群”、以長沙為核心的“長株潭城市群”、以南昌為核心的“環鄱陽湖城市群”和以合肥為核心的“皖江城市群”。未來可能的演化趨勢是:首先各城市群內部進行優勢資源整合與調配,局部區域先形成內部組團,例如皖江城市群以合肥市為核心,巢湖、馬鞍山和蕪湖等市為骨干的組團城市群將會因集聚而形成。此后,新一輪的互動將在這四大組團城市群間展開,以長江中下游交通走廊為主軸,向東南分別呼應“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形成我國中下游地區重要的城市帶。這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征。
這種“群帶式發展”將會對單個城市產生何種影響呢?從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經驗來看,它將會極大增強群內城市的互通關聯度,這種互通關聯度不僅意味著城際間擁有高效便捷的信息交通網絡,更在于擁有創造共同福祉與城市治理的機會空間。換言之,城市群或城市帶的發展并不意味著不同城市在空間上的無縫連接,而是指城市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分工協作已經密不可分,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群帶式發展將會為新興經濟的核心發展要素——人才提供更多的流動性選擇。
尋回城市精神
西方著名學者斯賓格勒說:“將一個城市和一座鄉村區別開來的不是它的范圍和尺度,而是它與生俱來的城市精神。”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看來,我們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種崇高感和超越感,提煉形成主題詞的形式,讓口號體現出強大的感召力。
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的內在氣質和根本價值的追求,是內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學法則。城市精神需要通過有代表性的符號解讀出來,而城市口號最具代表性。比如,“動感香港”這個口號很成功,因為它體現了香港工業、經濟和文化的動態與香港人的活力。
要詮釋城市精神,首先需要對城市進行明確定位,否則會事倍功半。如廣州的城市口號“一日讀懂兩千年”,既想照顧到該城市多元的歷史,又想打造現代主題文化,由于定位不明,不知取舍,容易不知所云。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彥平舉例道,往往一個城市有很好的文化資源,偏偏定位偏差,如大同,云岡石窟聞名中外,卻把自己叫做“煤炭之都”;甌越古地、南戲故里的溫州,以“中國鞋都”自得;還有古都南京,自稱“博愛之都”,反遭網民揶揄。
城市口號應該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僅包含歷史文化基礎,還必須有群眾基礎。劉彥平對在城市口號的塑造中民間參與嚴重不足表示擔憂。他認為,城市品牌的實質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對城市歷史的自豪感、對城市發展前景信心的綜合表達。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從設計、管理到增值,都應有市民的參與。
民間參與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浙江寧波曾舉行了口號海選,最后選定的一句“書藏古今,港通天下”就是出自一對來自湖南長沙的游客夫妻之手。
對大城市來說,依托雄厚的財力和發達的傳媒廣告業,宣傳、營銷自己的口號并不難。然而營銷只是推廣、輔助手段,不能解決城市精神重塑的大問題。如何利用歷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長動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還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包亞明說。
中國城市新版圖
1999年以來,中國開始對區域發展戰略進行調整,逐步形成了由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和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戰略構成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并由此形成支撐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的四大戰略區域。
然而,隨著長江中游城市群和長江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特別是以高鐵為代表的快速交通網絡在中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全面覆蓋,交通網絡化不僅縮短了東、中區域之間的時間距離,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提升了城市之間的可達性和便利程度。
網絡化的交通體系讓東部發達省(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廣州等區域中心城市經濟外溢的輻射效應得到有效發揮,中部地區以其天然的區位優勢成為東部地區經濟腹地的條件。
從時間距離收縮地圖來看,無論以上海還是北京為中心,以城市為載體的中國經濟空間格局的變化趨勢均顯示出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空間緊密壓縮,尤其是以上海為中心東中15個省(市)空間距離發生明顯收縮。
而時間距離地圖反映出東北、西北、西南目前仍然是群帶狀的城市體系或點線狀的城市體系,城市沿一條主線展開,能夠連接的城市節點比較少,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區域合作范圍均受限。
綜合來看,快速綜合交通體系的建設,加快了東、中合為一體的腳步,共同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區的趨勢逐步增強,而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在高鐵時代將面臨邊緣化的壓力,成為未來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重點。
未來中國城市空間體系將逐步呈現從東中部中心地區到東北和西部外圍地區的“一團五線”發展格局:東中部是中心區域,北至京呼線、東南臨海、西抵東經110°山區綿延帶的群網狀城市體系聚合成“一團”,形成“巨掌”,縱橫交錯的交通網絡匯聚于全國性中心城市,猶如經脈交匯于掌心;東北和西部是外圍區域,群帶狀城市體系延伸出“五線”,京哈線、隴海—蘭新線、長江下游延伸線、滬昆線和南海沿線形成五根“手指”;京廣線作為縱貫南北的大動脈,構成手掌和手指之間的關節線,向東對接東中部的網絡體系,向西發散出西部的群帶體系,使指掌間收放自如、行動統一;包昆線作為外圍的南北大通道,實現西部群帶體系的互聯互通,構成手指中部的關節線,使指間行動彼此兼顧,縱橫聯動。
同時,知識型發展將成為一種重要的城市發展模式。知識型發展是以“基于知識的發展”為理念,以數字技術促進城市智慧化發展,以知識創新促進城市知識產業集群化發展,以知識網絡促進城市空間結構虛擬化發展,以知識管理促進城市善治的一種城市綜合發展模式。當前,城市形態和布局不均衡、資源與環境約束等諸多困境正在激發相關部門對未來發展模式的積極思考。可以預見的是,為了適應國內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需要,各區域城市群中的骨干城市(以大中型城市為主)將成為城市轉型發展的先驅。尤其在知識經濟、智慧發展和低碳生活的多重背景之下,知識型發展模式將是一個備受推崇的選擇。
事實上,以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合肥為代表的國內城市在創新型國家建設和自主創新戰略的號召下,已經積極提出了構建創新型城市的戰略發展思路,并從整體上實施了城市創新運動。從這些城市的轉型實踐上不難看出,它們的行動正是在知識型發展模式上進行的有益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