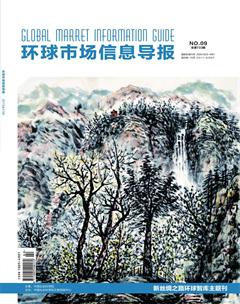網絡虛擬財產的定性分析與現實法律思考
衷妍

網絡虛擬財產是一種新型財產,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逐漸出現了交融的領域,也隨之引發了一系列有關虛擬財產的矛盾問題。學界對于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問題一直爭論不休,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出臺,首次對虛擬財產作出了規定,但這一規定較為模糊,對其法律屬性界定采折中觀點。本文通過對虛擬財產的外延和權利屬性問題進行比對分析的方式,進而提出法律思考,望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隨著網絡化浪潮的到來, “互聯網+”產業的興起,越來越多的法律糾紛開始涉及到網絡數據或者可以說是虛擬化的“財產”方面,虛擬財產能得法律上正名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2017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的正式出臺, “虛擬財產”被劃入民事權利客體體系中,該法在第一百二十七條明確規定, “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然而,在“虛擬財產”被作為一種法律概念廣泛運用之時,我們對于虛擬財產的外延界定,性質界定都沒有達成明晰的一致見解,這就使得關于“虛擬財產”的其他法條編纂陷入了一定的僵局。因此,對于當前虛擬財產兩個核心問題:虛擬財產的外延界定和虛擬財產的權利屬性界定的解決就至關重要。
一、虛擬財產的外延界定
目前,法律上對于網絡虛擬財產概念還未做出明確的界定,學者也持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虛擬財產是網絡游戲軟件中的軟件模塊運行時顯示在電腦屏幕上的影像,它不是勞動創造的,沒有價值,不屬于財產。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首先,筆者認為虛擬財產不限于網絡游戲及其附屬物,而是包括網絡環境下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對獨立又具獨占性的所有信息資源。其次,虛擬財產是一種財產,財產客體具有價值性,即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馬克思曾經指出: “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價值。”顯示在電腦屏幕上的影像出現并存在的意義正是其價值的體現,因此不能說虛擬財產沒有價值。
還有學者認為,虛擬財產更加強調其“虛擬”性,只要是數字化的,非物化的財產形式,一切存在于網絡虛擬空間內的、由持有人隨時調用的專屬性數據資料都被納入網絡虛擬財產的范圍,而不管其是否具有交易價值。在此筆者認為,網絡虛擬財產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現下各種游戲裝備,賬號及其積分等級的線上線下交易都成為了一種常態,以現在的網絡游戲裝備交易為例,淘寶上搜索某游戲的頂尖裝備其交易價格可以達到數萬元。并且,越來越多的網絡用戶通過注冊、購買等方式在網絡空間交流,娛樂,學習,實現其自身在網絡空間內的需求,虛擬財產的可使用性也在此體現。因此,虛擬財產作為一種財產而言,具備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當前虛擬財產已涉及各個領域,出現各種形式,并且隨著網絡的進一步發展還會繼續增加,單純用列舉的方法來歸納虛擬財產的種類是不符合實際和立法的長遠性考慮的,在此筆者贊同用“虛擬入口”和“虛擬資產”兩個“中層概念”來把握虛擬財產的邊界。
作為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連接, “虛擬入口”即用戶接入網絡空間的關卡,其通過創制一個新的節點和一條可交換路徑使得用戶在虛擬世界里被發現,被承認,進而成為適格的信息資源提供者和搜索者。這就是我們通俗意義上的“注冊”產生賬號或者編碼索引的網頁地址的過程,而此種注冊所產生的“身份識別憑證”,根據服務內容的不同可以進一步分為電子郵件賬戶、社交通訊賬戶、社交媒體賬戶、網絡游戲賬戶、文件存儲和分享賬戶、商業賬戶、網上商城賬戶以及軟件許可證等等; “網頁地址”則指用戶通過注冊、購買、租賃或授權等方式取得的,用以向他人提供和接受信息的網絡資源名稱標識。
根據“通道—內容”的區分原則,我們可以把“虛擬資產”視為“虛擬入口”背后存儲在網絡服務器上的種種消息實體。例如:游戲賬號與賬號內包含的積分、裝備,網盤賬號與網盤內存儲的照片、音樂、視頻,比特幣賬號與用戶挖曠,交易所得的比特幣等都構成虛擬入口與虛擬資產的對應關系。筆者認為, “虛擬入口”的意義即在于為用戶獲取和獨占“虛擬資產”提供一個以賬戶或網頁鏈接為載體的資格。此外,雖然“虛擬財產首先耍滿足虛擬的特陛,這就意味著虛擬財產對網絡游戲虛擬環境的依賴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不能脫離網絡游戲而存在”,然而只存在于網絡等虛擬世界的物品也不能稱為法律意義上的虛擬財產,必須與現實社會產生了一定的關聯。因為如果物品完全脫離于現實世界而存在進而成為完全意義上的虛擬,其固然仍具有其使用價值能給用戶帶來愉快的心理,滿足用戶的心理需求,但是其交易價值也隨著物品與現實世界的脫節而失去。如大富翁游戲中的鈔票,地產就不屬于虛擬財產法律意義上的考量范疇。此外,在判斷這種關聯達到伺種程度才能稱其具有現賣^生這一問題時,一個可行的衡量標準就是這種所謂的虛擬財產能在現實中找到相應的對價,而且能實現在虛擬世界和現實社會間的自由轉換。
二、虛擬財產的權利屬性界定
當前學界占主流的觀點即“物權說”和“債權說”,應當說,兩派別學者均完成了對自身觀點的完整論證,但由于兩種學說都存在自身“命門”,難免遭受到對方的攻擊,以致難以達成完全其識。
“物權說”認為網絡虛擬財產具有特定性和獨立性,應當被界定為物,主張將虛擬財產界定為所有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立新認為,網絡虛擬財產在界定其為物時,最大的障礙就是其沒有形,因為大陸法系的民法認為物必有形,說一個東西沒有形的時候,很難認定它是物。但是這個觀點其實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就解決過了,以電為例,以前我們沒有電以前,認定物必有形,沒有任何疑問,但是一旦發明了電,如何界定其性質?在民法上認定爭論了很多年,說物必有形,電無形但是它有價值。最后德國得出一個結論說,它是一種特殊的物,這種特殊的物就叫自然力。由此可見,虛擬財產作為一種無形但有價值的物,可以將其劃入物權的范疇。但實際上,我國目前對網絡虛擬財產的界定尚未能明確類型化標準,因此所謂虛擬財產具有物權的特定性和獨立性也就無從考量。此外,將虛擬財產的無體性特征與物權法所規定的物權的標的為有體物不符,但若此時徹底改變物權法的有體物基礎,擴大物的范圍,使得虛擬財產在物權法中占據一席之地,在目前我國物權法體系剛剛建立,對有體物的物權研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將會徹底摧毀物權法體系。
“債權說”通過用戶與運營商之間存在的合同債權來理解虛擬財產權,將虛擬物的取得、轉讓、滅失等視為一種債的關系。的確,該說不存在用戶與運營商之間的權利界定難題,但該說受制于債權的相對性,在解釋用戶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救濟時面臨困難。此時“債權說”的解決方案,只得是借助“第三人侵害債權”這一相對模糊的侵權法機制。因此“債權說”雖能夠自圓其說,但在解釋論上也未免給人“拖泥帶水”之感;其次,《民法總則》118條第2款明確規定,債權的客體是民事主體的“行為”,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客觀存在。而網絡虛擬財產是獨立于人主觀之外的客觀存在,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不是民事主體的行為,因而不能成為債權的客體。
三、虛擬財產納入當前法律的思考
201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是我國民法基本法第一次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概念作出規定。從表面意義上來看,《民法總則》只是明確了網絡虛擬財產受保護,但對其受何種保護、如何保護并沒有加以界定,而當前學界對于虛擬財產的權利屬性認定也陷入了困局,但可以通過比對四次《民法總則(草案)》關于虛擬財產條文的內容分析立法機關的趨向,即一審稿認為應當將其劃入物權范疇;二審稿刪去此條款;三、四審稿又對其進行了折中界定。綜合來看,立法機關趨于將網絡虛擬財產歸屬于物的法律范疇中。
筆者認為,雖然《民法總則》將網絡虛擬財產納入了“民事權利”一章的民事權利客體的保護范疇,但其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仍沒有作出明確界定,這就存在兩大問題:其一,網絡虛擬財產未明確納入公民的私有財產范圍。根據現有的法條規定,立法者并沒有明確網絡虛擬財產可以享有同現實物質世界中公民的私有財產的同等保護。其二,網絡虛擬財產尚未納入民法上的物的范疇。我國采取物權法定的立法模式,所以應該在一定的時間范疇內將民法意義上的物的范圍進行延伸,在不損害公民合法權益的同時將網絡虛擬財產納入物的范同。值得注意的是,這在立法技術上將是一次巨大的挑戰,如若過于草率必然會造成整個法律體系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