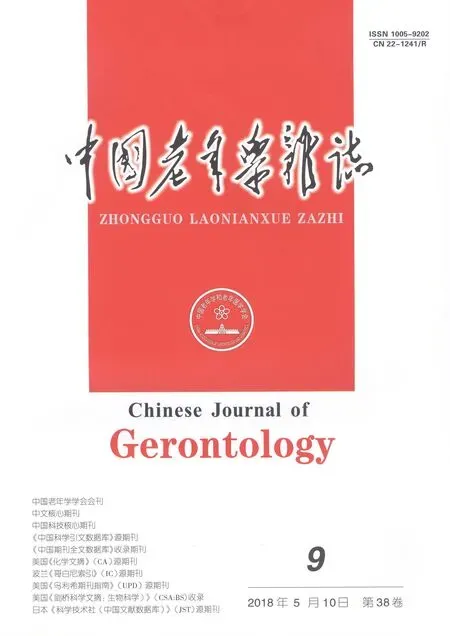針藥結合治療失眠的臨床療效
蘇 敏
(中山市國丹中醫院,廣東 中山 528400)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中山市國丹中醫院針灸科門診就診失眠患者60例,按照患者就診的先后順序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30例。治療組男14例,女16例,年齡20~75〔平均(56.63±7.78)〕歲,病程35~365〔平均(65.29±6.83)〕d;對照組男15例,女15例,年齡18~75〔平均(56.25±7.53)〕歲,病程31~365〔平均(64.85±6.61)〕d。兩組一般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診斷標準:中醫診斷依據1993年國家衛生部《中藥新藥治療失眠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標準。西醫診斷依據精神與行為障礙國際分類(ICD)-10及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納入標準:①符合失眠的中西醫診斷標準;②意識清楚,能清晰對答,無嚴重心、肺、腎、肝等疾病,無精神疾病,無藥物依賴史;③妊娠、哺乳期患者;④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①不符合納入標準者;②不能按照研究方案進行治療觀察者;③疼痛、酗酒或精神藥物濫用和依賴所致失眠者;④由于身體或其他原因不能參與本研究者。
1.2治療方法
1.2.1治療組 采用針刺療法結合耳穴貼壓聯合阿普唑侖片口服治療。(1)針刺療法取穴:四神針(前頂、后頂、絡卻)、腦三針(腦戶、腦空)、手智針(內關、神門、勞宮)和眠三針(內關、神門、三陰交)。配穴:心脾兩虛證加脾俞、心俞;心腎不交證加心俞、腎俞;心膽氣虛證加心俞、膽俞;肝火擾心證加太沖、行間;痰熱擾心證加足三里、豐隆。取穴、針刺方法均參照全國中醫藥行業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經絡腧穴學》。進針得氣后,連接G6805-A型電針儀,采用連續密波,強度以病人能耐受為度,配合TDP照射,每次30 min,1次/d,每周日休息。(2)耳穴貼壓:取穴:神門、皮質下、交感、心、肝、脾、腎、膽。方法:將耳廓常規消毒,用醫用膠布貼將王不留行籽貼壓在穴位的敏感點上。囑患者睡前自行按壓5 min,以自感耳廓充血、發熱、發脹為度。每次貼1只耳廓,兩耳交替貼壓,每2 d交換一次。(3)藥物治療:口服阿普唑侖片,0.4 mg/次,睡前服用。
1.2.2對照組 只給予口服阿普唑侖片,0.4 mg/次,睡前服用。兩組均治療4 w后評估療效。
1.3療效評價
1.3.1一般療效評定 根據《精神疾病治療效果標準修正草案》中失眠的療效標準。治愈:睡眠時間恢復正常或每晚睡眠時間大于6 h,白天疲乏感消失。顯效:睡眠時間較前增加2 h,白天疲乏感消失。有效:睡眠時間較前增加1 h,白天疲乏感減輕或存在。無效:治療前后睡眠無改善或加重。
1.3.2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評估患者主觀癥狀的變化 主要用于受試者睡眠困難的自評。0~3分為無睡眠障礙,4~5分可能有睡眠障礙,6分及以上存在失眠。患者得分越高,睡眠質量越差。
1.3.3匹茨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評估睡眠質量的變化 該表由19個自評和5個他評條目組成,其中18個條目組成7個因子,每個因子按0~3分等級計分,累積各因子成分得分為PSQI的總分,總分范圍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質量越差。PSQI≤7分為睡眠質量正常,PSQI>7分為低睡眠質量。
1.3.4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評定量表簡表(WHO-QOL-BREF)評定治療前后患者生活質量改善情況 包括生理、心理、社會、環境等4 個領域 26 個項目,分值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好。量表采用問卷形式,在專業人員的統一指導下自行答卷。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軟件。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 果
2.1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治愈9例,顯效15例,有效3例,無效3例;對照組治愈3例,顯效9例,有效13例,無效5例。治療組總有效率(90.0%)優于對照組(83.3%,P<0.05)。
2.2兩組治療前后AIS、PSQI評分比較 見表1。

表1 兩組治療前后AIS、PSQI評分比較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1)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2)P<0.05;下表同
2.3兩組治療前后WHO-QOL-BREF評分比較 見表2。
2.4不良反應 治療期間兩組均未出現不良反應。

表2 兩組治療前后WHO-QOL-BREF評分比較
3 討 論
失眠屬于中醫學“不寐”、“不得臥”、“不得眠”等范疇。失眠的病因病機多種多樣,中醫學認為睡眠和醒覺是由神的活動來主宰,主要病位在心腦與臟腑,主要病機是心神被擾,腦神失養,神不守舍〔3~7〕。《素問·靈蘭秘典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六節臟象論》:“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素問·宣明五氣篇》:“心藏神”。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腦為元神之府。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卷一·論治總則》 “頭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三因方》:“頭者,百神所聚”。張景岳《景岳全書卷十八·不寐》:“蓋寐本乎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楊上善著《黃帝內經太素》:“頭是心神所居”。《顱鹵經》:“元神在頭,曰泥丸,總眾神也”。清代王清任提出腦與精神活動關系密切,“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王宏翰在《醫學原始》中明確提出了記憶、知覺和睡眠皆由腦所主,是中醫學較早期的腦主知覺和睡眠的理論。近代張錫純提出“心腦共主神明”的認識,將元神與識神、腦與心在功能結構上緊密結合。
本次研究主要使用廣州中醫藥大學靳瑞教授所創的“靳三針”療法,主要穴位均位于頭部。根據《素問·脈要精微論》:“諸陽之神氣皆上會于頭,諸髓之精氣皆上聚于腦,頭為精明之府”。管子曰“腎生腦”(《管子·水池》),《素問·經脈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素問·五臟生成篇》說:“諸髓者,皆屬于腦”。針刺上述穴位,可以直接刺激腦部,能使患者神氣散者聚,失者復,亢者平,抑者揚〔8〕,達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共奏安神調腦、促進睡眠的作用。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心開竅于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腎在竅為耳”,《靈樞·脈度》:“腎氣通于耳”,因此可見,心腎皆開竅于耳。耳穴貼壓療法有可留置的特性,能對耳穴產生持續的刺激效應。耳的神經分布豐富,具有“人體穴位的全息縮影”之稱,通過對耳穴及其所屬神經進行規律的刺激,可以調節大腦神經系統的興奮與抑制狀態,使其達到平衡,從而治療失眠〔9,10〕。
本研究結果表明,靳三針療法結合耳穴貼壓聯合藥物治療失眠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
4 參考文獻
1吳 江,賈建平.神經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6:484-5.
2楊寶峰.神經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117-9.
3劉雅楠,林成蔭,吳煥淦,等.從脾胃論治針刺治療失眠癥臨床觀察〔J〕.中國針灸,2015;35(8):768-72.
4杜津莉,樊煒駿,杜洪娟.靳三針結合加味烏梅丸治療圍絕經期失眠的臨床觀察〔J〕.中國藥房,2017;28(8):1104-7.
5劉 義,馮 慧,劉文娟,等.針刺對原發性失眠癥患者覺醒狀態調節作用及其相關神經電生理學效應研究〔J〕.中國針灸,2017;37(1):19-23.
6崔 揚,王偉志.針灸治療失眠的研究現狀〔J〕.黑龍江中醫藥,2012;41(4):59-60.
7中國中醫科學院失眠癥中醫臨床實踐指南課題組.失眠癥中醫臨床實踐指南〔J〕.世界睡眠醫學雜志,2016;3(1):11.
8袁 青,劉龍琳,沈秀進,等.論“靳三針”學術內涵〔J〕.中國針灸,2014;34(7):701-4.
9徐 征,朱麗群.耳穴埋豆治療慢性肝炎伴失眠癥患者的效果〔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4;34(9):2880-2.
10羅 曼,屈簫簫,李少源,等.耳穴迷走神經刺激治療原發性失眠癥及其情感障礙35例:病例系列研究〔J〕.中國針灸,2017;37(3):2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