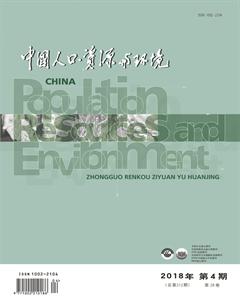貿(mào)易開放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影響
齊紹洲 徐佳
摘要 綠色“一帶一路”建設(shè)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貿(mào)易開放則是促進(jìn)“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技術(shù)進(jìn)步的重要渠道。本文用SBM模型測算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用以衡量沿線國家的綠色技術(shù)進(jìn)步,并基于面板門檻模型從進(jìn)口貿(mào)易和出口貿(mào)易兩個角度考察了沿線國家貿(mào)易開放基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基礎(chǔ)設(shè)施、金融發(fā)展和制度質(zhì)量4個因素的綠色技術(shù)溢出門檻效應(yīng)。研究發(fā)現(xiàn):①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基礎(chǔ)設(shè)施、金融發(fā)展和制度質(zhì)量四個變量對“一帶一路”沿線31個國家貿(mào)易開放的綠色技術(shù)溢出都存在顯著門檻效應(yīng)。進(jìn)口貿(mào)易的綠色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隨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兩個門檻的跨越而由負(fù)轉(zhuǎn)正并逐步增強(qiáng);在跨越基礎(chǔ)設(shè)施、金融發(fā)展和制度質(zhì)量門檻前后,進(jìn)口貿(mào)易的綠色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都為正,但在跨越門檻之后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出口貿(mào)易在樣本期內(nè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呈負(fù)向影響,但影響程度隨四個變量門檻的跨越而逐漸降低,顯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②沿線國家基于四個門檻變量的通過情況有所不同。跨越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門檻和金融發(fā)展水平門檻的樣本國家較多,跨越制度質(zhì)量水平門檻的國家次之,跨越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門檻的樣本國家還較少。③貿(mào)易開放整體有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相比出口貿(mào)易,進(jìn)口貿(mào)易更有助于促進(jìn)“一帶一路”國家綠色技術(shù)進(jìn)步。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逐步提升沿線國家在此四方面的發(fā)展水平將有利于綠色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的充分顯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