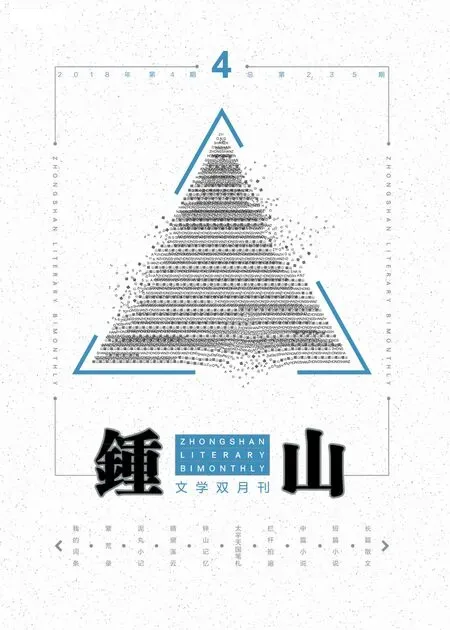陳寅恪對中醫(yī)的看法
王彬彬
WANGBINBIN
一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清末的變法維新運(yùn)動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在《鐘山》2018年第2期發(fā)表的 《陳寶箴的喉骨》一文,對此有所評介。但陳寶箴還是一個具有專業(yè)水準(zhǔn)的中醫(yī),能夠為人處方看病。陳寶箴的父親陳偉琳(字琢如)是鄉(xiāng)間名醫(yī),陳寶箴繼承了父親在醫(yī)學(xué)方面的志趣。而陳寶箴對中醫(yī)的興趣也為兒子陳三立所承襲。陳三立同樣具有為人看病開藥的本領(lǐng)。所以,義寧陳氏,其實是中醫(yī)世家。陳三立之子陳寅恪,從小耳濡目染,對中醫(yī)也了解甚深。對中醫(yī),陳寅恪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在清末政壇有轟轟烈烈的表現(xiàn),也與其時政壇上清濁兩類人物都多有瓜葛。陳寅恪晚年,曾撰《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記述和評說清末政壇狀況及祖父和父親在清末政壇的所作所為。據(jù)陳寅恪門人蔣天樞說,此稿作于1965年夏至1966年春,是陳寅恪最后之作。這個《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目錄如下:
弁言
(一)吾家先世中醫(yī)之學(xué)
(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
(三)孝欽后最惡清流(佚)
(四)吾家與豐潤之關(guān)系(佚)
(五)自光緒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間清室中央政治之腐敗(佚)
(六)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guān)系
(七)關(guān)于寅恪之婚姻(佚)
正文原有七個部分,三、四、五、七四個部分都在混亂中散失了。現(xiàn)存者是經(jīng)蔣天樞整理的殘稿。在《弁言》中,陳寅恪說:“今既屆暮年,若不于此時成之,則恐無及。因就咸同光宣以來之朝局,與寒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guān)者,證諸史料,參以平生耳目見聞,以闡明之。并附載文藝瑣事,以供談助,庶幾不賢者識小之義。既不誣前人,亦免誤來者。知我罪我,任之則已。 ”又說:“清代季年,士大夫?qū)嵱星辶鳚崃髦帧R”救嘶蛞允澜恢x,或以姻婭之親,于此清濁兩黨,皆有關(guān)聯(lián),故能通知兩黨之情狀并其所以分合錯綜之原委。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毀譽(yù)務(wù)求一持平之論斷。他日讀者倘能詳考而審察之,當(dāng)信鄙言之非謬也。”陳寅恪要以乃祖乃父的事跡為中心,對晚清政壇清濁兩黨做一評說,并且自信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立論,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
然而,這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卻首先說的是自家的“家學(xué)”:“中醫(yī)之學(xué)”。曾祖、祖父、父親三代俱習(xí)中醫(yī),俱能處方治病,實在與清末政治沒有什么關(guān)系。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中醫(yī)知識,與他們的政治作為、與清季政壇之清濁,也實在看不出有何牽扯。陳寅恪首先述說“吾家先世中醫(yī)之學(xué)”,豈非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但陳寅恪何許人,豈會犯博士買驢的錯誤?此中或有深意存焉。此一層,最后再說。
第一部分“吾家先世中醫(yī)之學(xué)”,一開頭寫道:
吾家素寒賤,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虛所謂讀書種子者。先曾祖以醫(yī)術(shù)知名于鄉(xiāng)村間,先祖先君遂亦通醫(yī)學(xué),為人療病。寅恪少時亦嘗瀏覽吾國醫(yī)學(xué)古籍,知中醫(yī)之理論方藥,頗有由外域傳入者。然不信中醫(yī),以為中醫(y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若格于時代及地區(qū),不得已而用之,則可。若矜夸以為國粹,駕于外國醫(yī)學(xué)之上,則昧于吾國醫(yī)學(xué)之歷史,殆可謂數(shù)典忘祖歟?曾撰三國志中印度故事、崔浩與寇謙之及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法曲篇等文,略申鄙見,茲不贅論。小戴記曲禮曰:“醫(y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曾祖至先君,實為三世。然則寅恪不敢以中醫(yī)治人病,豈不異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長女流求,雖業(yè)醫(yī),但所學(xué)者為西醫(yī)。是孟子之言信矣。
又說:
中醫(yī)之學(xué)乃吾家學(xué),今轉(zhuǎn)不信之,世所稱不肖之子孫,豈寅恪之謂耶?
這里主要表達(dá)了三種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自家雖然自曾祖至父親,三代俱通中醫(yī),自己也讀過不少中醫(yī)古籍,然而,自己卻并不相信中醫(yī)。中醫(yī)固然有見效之藥,但卻無法用科學(xué)理論進(jìn)行解釋。在特定的時代和地區(qū),不得已而用中醫(yī),自然是可以的,但如果把中醫(yī)矜夸為“國粹”,讓中醫(yī)凌駕于西醫(yī)之上,那就是十分荒謬的。第二層意思是,自己雖然讀過不少中醫(yī)古籍,但卻不敢像曾祖、祖父和父親那樣為人看病開藥。雖然是中醫(yī)世家,但自己的長女流求卻學(xué)的是西醫(yī),所以,自己是家學(xué)的背叛者,是不肖子孫。第三層意思尤為重要,那就是所謂中醫(yī),也并非完全是中土的產(chǎn)物,在理論和方藥兩方面,都頗有域外傳入者。換句話說,所謂中醫(yī),也并非純粹是中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
二郭嵩燾是陳寶箴摯友。當(dāng)陳寶箴在湖南巡撫任上銳意革新時,郭嵩燾多有贊助。郭嵩燾曾為陳寶箴父親陳偉琳撰墓碑銘,其中寫道:
江以西有隱君子,曰陳琢如。先生諱偉琳,系出江州,世所稱義門陳氏者也。先世有仕閩者,遂為閩人。祖鯤池,由閩遷江西之義寧州,再傳而生先生。考克繩,以孝義,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始六七歲,授章句,已能通曉圣賢大旨。端重簡默,有成人之風(fēng)。及長,得陽明王氏書讀之,開發(fā)警敏,窮探默證,有如夙契,曰:“為學(xué)當(dāng)如是矣!奔馳夫富貴,泛濫夫詞章,今人之學(xué)者,皆賊其心者也。惟陽明氏有發(fā)聾振瞆之功。”于是刮去一切功名利達(dá)之見,抗心古賢者,追而躡之。久之,充然有以自得于心。一試有司,不應(yīng)選,決然舍去,務(wù)以德化其鄉(xiāng)人,尤相獎以孝友。其事父母, 力壹心,承順顏色,不言而曲盡其意。母謝太淑人病亟,夜馳二十里,禱于神。比反,太淑人寐方覺,言神餌我以藥,疾以霍然。先生以太淑人體羸多病,究心醫(yī)家言,窮極《靈樞》、《素問》之精蘊(yùn),遂以能醫(yī)名。病者踵門求治,望色切脈,施診無倦。自言:“無功德于鄉(xiāng)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盡也。”
這讓我們明白,陳家先前便是江西江州人,后來因為有人在福建做官,一度徙家福建。到了陳偉琳的祖父一代,又從福建遷回江西。陳偉琳的父親名克繩,生子四人,偉琳是最小的兒子。偉琳之所以研習(xí)起醫(yī)學(xué),是因為母親體羸多病。為治母病而學(xué)醫(yī),卒成地方名醫(yī),以至于“病者踵門求治”。
偉琳的中醫(yī)之學(xué),傳給了兒子寶箴。陳寅恪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記述了幾件祖父在中醫(yī)上的表現(xiàn)。翁同騄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十日”條云:
晚訪陳右銘,未見。燈后右銘來辭行,長談。為余診云,肝旺而虛,命腎皆不足,牛精汁白術(shù)皆補(bǔ)脾要藥,可常服。(自注:脈以表上十五杪得十九至,為平。余脈十八至,故知是虛。)寶箴字右銘。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這一年,是寶箴春風(fēng)得意的一年。1893年,寶箴被任命為直隸布政使,并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詢。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寶箴被任命為東征湘軍的糧臺,駐守天津。此時,寶箴已準(zhǔn)“專折奏事”。1895年秋天,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達(dá)到政治生涯的頂峰。為翁同騄把脈療疾時,應(yīng)該尚在糧臺任上。正月二十這天,太陽落山時分,翁同騄拜訪陳寶箴,未遇。掌燈后,寶箴回訪兼辭行,二人長談。長談中,寶箴大概看出翁同騄氣色不佳,于是主動提出為其把脈。翁同 曾任帝師,此時是軍機(jī)大臣。陳寶箴敢于為其把脈開藥,可見他對自己的醫(yī)學(xué)是很自信的。
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又說:
猶憶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先祖擢任直隸布政使,先君侍先祖母留寓武昌,……一日忽見傭工攜魚翅一?,酒一甕并紙一封,啟先祖母曰,此禮物皆譚撫臺所贈者。紙封內(nèi)有銀票伍百兩,請查收。先祖母曰,銀票萬不敢收,魚翅與酒可以敬領(lǐng)也。傭工從命而去。譚撫臺者,譚復(fù)生嗣同丈之父繼洵,時任湖北巡撫。曾患疾甚劇,服用先祖所處方藥,病遂痊愈。譚公夙知吾家境不豐,先祖又遠(yuǎn)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饋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側(cè),時方五六歲,頗訝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報。在童稚心中,固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
這說的是陳寶箴為時任湖北巡撫的譚繼洵 (譚嗣同之父)治病之事。陳寶箴任直隸布政使,在光緒十九年,陳寅恪記憶略有誤。北上任職前,陳寶箴是湖北布政使,居家武昌。北上時,家眷未隨行,仍留居武昌。陳寶箴治好了譚繼洵的重病,于是譚繼洵差人送上魚翅、美酒和重金。陳寅恪時方五六歲,頗驚異于為人治病竟獲如此厚報。
陳寅恪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還說了這樣一件事:
又光緒二十五年先祖寓南昌,一日諸孫侍側(cè),閑話舊事,略言昔年自京師返義寧鄉(xiāng)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適門外有以人參求售者,購服之即痊。先祖詫曰,吾家素貧,人參價貴,售者肯以賤價出賣,此必非真人參,乃薺絇也。蓋薺絇似人參,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載甚明(見本草綱目壹貳“薺絇”條)。特世人未注意及之耳。寅恪自是始知有本草之書,時先母多臥疾,案頭常置本草綱目節(jié)本一部,取便翻閱。寅恪即檢薺絇一藥,果與先祖之言符應(yīng)。是后見有舊刻醫(yī)藥諸書,皆略加批閱,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書中所言為人處方治病,唯藉作考證古史之資料,如論胡臭與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戊戌政變后,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被朝廷革職。1898年11月,陳寶箴攜眷定居于南昌。這里說的,便是陳寶箴閑居南昌時對諸孫回憶舊事。薺絇似人參而能治咳嗽之病,是《本草綱目》上寫明了的,但“世人未注意及之”。而寶箴一聽母親以賤價購得人參并且果然治愈咳嗽之癥,便知此必非真人參而實為薺絇,可見其中醫(yī)素養(yǎng)超乎流俗。陳寅恪生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此時年方九歲,但已知有《本草綱目》一書。九歲的寅恪,聽了祖父對于薺絇的介紹后,居然想到查閱《本草綱目》以驗證祖父之言,宜乎日后成為學(xué)術(shù)大家。而且,從此以后,見到舊刻醫(yī)學(xué)書籍,都要看一看。雖然寅恪自謙曰一知半解,但以他的資質(zhì),讀了許多中醫(yī)古籍,對中醫(yī)的知解決非很粗淺。
《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沒有提及父親陳三立為外人處方治病事,但說到了他常給兒子看病開藥:
寅恪少時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處方藥。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寧,始得延西醫(yī)治病。自后吾家漸不用中醫(yī)。蓋時勢使然也。
寅恪兒時生病,都由祖父和父親以中醫(yī)診治。可見父親三立也是能開藥方的。1900年,陳三立攜眷移居南京。自此家中有人生病,便請西醫(yī)治療。1900年便能放棄中醫(yī)而信任西醫(yī),是不容易的,而作為中醫(yī)世家,能斷然舍中醫(yī)而就西醫(yī),就更是難能可貴了。陳三立在父親主導(dǎo)的湖南新政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實非偶然。
三陳寅恪雖然自幼便讀中醫(yī)古籍,讀了許多,具備豐富的中醫(yī)知識,但卻并不以此為人療疾,只是把中醫(yī)知識用于歷史研究。應(yīng)該說,中醫(yī)方面的學(xué)養(yǎng),幫助陳寅恪弄明白了歷史上的一些問題;而政治史、經(jīng)濟(jì)史、文化史方面的廣博知識,又讓陳寅恪對中醫(yī)發(fā)展史有獨特而深刻的見解。下面,對陳寅恪涉及中醫(yī)的幾篇文章略作介紹。
(一)《狐臭與胡臭》
此文頗短小,才一千多字,原刊1937年6月出版的 《語言與文學(xué)》,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
《狐臭與胡臭》一開始寫道:“中古華夏民族曾雜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統(tǒng),近世學(xué)人考證之者,頗亦翔實矣。寅恪則疑吾國中古醫(yī)書中有所謂腋氣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與此端有關(guān)。”陳寅恪在中古醫(yī)書中發(fā)現(xiàn)“腋氣”病名,又稱“狐臭”。他想到中古時期華夏民族曾與“西胡”混血,便疑“狐臭”之病,源自“西胡”,而本來稱“胡臭”,后來才衍變成“狐臭”。
陳寅恪首先糾正了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和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中關(guān)于“狐臭”(“胡臭”)敘說的錯誤。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狐臭”條云:“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易著于人。小兒多是乳養(yǎng)之人先有此病,染著小兒。”這種關(guān)于“狐臭”的描述,基本是胡說了。陳寅恪指出,巢元方認(rèn)為患腋氣者“腋下有如野狐之氣”,所以又稱“狐臭”,這在字面上雖然說得通,但其實是在望文生義。歐美之人,當(dāng)盛年時,大抵有腋氣,與血氣不和也沒有關(guān)系。至于說“狐臭”具有傳染性,也是謬誤。孫思邈《千金要方》論“胡臭”:“有天生胡臭者,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胡臭”都是天生,沒有后天染上者。孫思邈所說也頗謬。
陳寅恪指出,南宋楊士瀛所撰《仁齋直指》中有“腋下胡氣”條目,并為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沿用。 “胡臭”之“胡”,自然是“胡人”之“胡”。古代“胡”“狐”二字雖可通用,但在《千金要方》《仁齋直指》《本草綱目》編撰之時,卻不可認(rèn)為“胡”乃“狐”之同音假借;諸書都寫作“胡”而不寫作“狐”,也不可認(rèn)為是音近而訛寫。實際上,在古代,所謂腋氣一病,尚有“胡臭”與“狐臭”兩種稱謂并行。
陳寅恪又舉了兩個古籍所載身有“胡臭”而有“胡人”血統(tǒng)者的例子。當(dāng)然,即便如此,也不能斷定有“胡臭”者就必定有“胡人”血統(tǒng)。陳寅恪說:
……證據(jù)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結(jié)論,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國中古舊籍,明載某人體有腋氣,而其先世男女又可考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二人而論,則不得謂腋氣與西胡無關(guān)。疑此腋氣本由西胡種人得名,迨西胡人種與華夏民族血統(tǒng)混淆既久之后,即在華人之中亦間有此臭者,倘仍以胡為名,自宜有人疑為不合。因其復(fù)似野狐之氣,遂改“胡”為“狐”矣。若所推測者不謬,則“胡臭”一名較之“狐臭”,實為原始,而且正確歟?
借助中醫(yī)舊籍中關(guān)于腋氣的介紹,陳寅恪指出腋氣本來是“西胡”人種獨有,所以,有“胡臭”之名行世。后來,當(dāng)華人與“西胡”混血之后,后代便也有人體有腋氣,再稱之為“胡臭”便不合適了,又因為腋氣之癥頗似野狐之騷,便改“胡臭”為“狐臭”了。
(二)《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
此文原刊《清華學(xué)報》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
這篇文章,指出《三國志》中作為真實事跡介紹的曹沖和華佗的故事,有的其實是來自于佛教讀物,是把佛教讀物中的神話故事,嫁接到曹沖、華佗身上而已。文章一開始說:
陳承祚著三國志,下筆謹(jǐn)嚴(yán)。裴世期為之注,頗采小說故事以補(bǔ)之,轉(zhuǎn)失原書去取之意,后人多議之者。實則三國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于其間,特跡象隱晦,不易發(fā)覺其為外國輸入者耳。陳壽(承祚)著《三國志》,以態(tài)度謹(jǐn)嚴(yán)為人稱道。裴松之(世期)注《三國志》,常常援引小說故事來補(bǔ)充本文敘述,也因此時常遭到后人的譏嘲。因為小說故事往往出自想象虛構(gòu),不能視作歷史事實。然而,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三國志》本文中敘述的故事,有些也正是來自于佛教的神話傳說。
《三國志·魏志》說曹操之子曹沖從小便異常聰慧,有成人之智。有一次,孫權(quán)送來一頭大象,曹操想知道其重量,遍詢諸人,無人能想出稱量的辦法。曹沖說,置大象于大船之上,在吃水線上刻下印痕,然后稱物入船,便能得知大象的重量了。曹操大喜,即依法而行。這就是著名的曹沖稱象的故事。后人往往信以為真。陳寅恪指出,這故事其實出自北魏時期譯出的《雜寶藏經(jīng)》。《雜寶藏經(jīng)》云:
天神又問,此大白象有幾斤?而群臣共議,無能知者。亦募國內(nèi),復(fù)不能知。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陳寅恪指出,《雜寶藏經(jīng)》雖然到北魏時期才譯出,但此書原本雜采諸經(jīng)而成,其中所載故事,別見于中國先后譯出之佛典中。所以以船稱象的故事,完全可能先于《雜寶藏經(jīng)》而傳入中國。如果找不到先于《雜寶藏經(jīng)》傳入中國而載有此故事之佛典,那也不能證明此故事絕對沒有先期傳入,因為載有此故事之書完全可能已經(jīng)亡逸而無可查考。并且:“或雖未譯出,而此故事僅憑口述,亦得輾轉(zhuǎn)流傳至于中土,遂附會為倉舒(引按曹沖字倉舒)之事,以見其智。但象為南方之獸,非曹氏境內(nèi)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與孫權(quán)貢獻(xiàn)混成一談,以文飾之,此比較民俗文學(xué)之通例也。”
那時的人們?yōu)榱丝滹棽軟_之智,遂把佛經(jīng)中的故事粘貼到曹沖身上。又因為曹操統(tǒng)治的地域,不可能有大象,便拉扯上南方的孫權(quán),說大象是孫權(quán)贈送。《三國志》有“華佗傳”,其中關(guān)于華佗行狀的敘述,很多也來自佛教典籍,并“華佗”這個名稱,也源自天竺語(梵文)。《三國志·華佗傳》中說,華佗字元化,深諧“養(yǎng)性之術(shù)”,時人以為其年已過百,但仍是壯年之態(tài)。華佗精通醫(yī)術(shù),為人治病,往往藥到病除。華佗還擅長“外科手術(shù)”。如果病“結(jié)積在內(nèi)”,針灸、服藥俱無用,必須“刳割”(開刀),便先讓病人服下“麻沸散”(麻醉藥),病人立即便如醉死一般,失去知覺。于是華佗便“破取”,也就是切開身體。如果是腸子有病,便把有病的那段剪下來“湔洗”,然后再縫上去。病人不醒不痛,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一個月后傷口便恢復(fù)如初。一次,華佗在路上遇見一人患咽喉堵塞病,食物不得下咽。家人用車子載著欲往就醫(yī)。華佗聽見呻吟聲,停車往視,對那人說:“剛才路過的地方,有一賣餅家有蒜泥姜汁大醋調(diào)和的佐料,你去弄得三升飲下,病便好了。”那人依言而行,“立吐蛇一枚”。他把蛇掛在車邊。華佗尚未走遠(yuǎn)。此人趕上華佗,卻見華佗車內(nèi)掛著此種蛇十多條。又有一個士大夫身體不適,華佗說:“你的病已經(jīng)很嚴(yán)重,必須破腹除病。但你的壽命也只剩十年。此病不足以讓你喪命,你忍病十載,也就免得受破腹之苦。”此人痛癢難耐,必欲除之,華佗于是為其破腹治病。病雖然立即好了,但此人也在十年后死了。廣陵太守患病,胸中煩悶,面色赤紅、食欲減退。華佗診脈后說:“你胃中有蟲數(shù)升,快要形成內(nèi)疽,是吃多了腥物的原因。”于是煎了二升湯藥,先讓病人服一升,過一會兒把剩下的服完。不一會,吐出蟲兒三升左右。蟲兒皆赤頭,身子蠕動,半身是生魚絲。病也立即好了。曹操聽說了華佗的神技,便把他召到身邊。曹操患有頭風(fēng)病,深以為苦。每次發(fā)病,心亂目眩。華佗針扎曹操胸膈,病痛立愈。華佗離家日久,十分想家,便說收到家信,要請假回家一趟。回家后又一再以妻子生病為由續(xù)假。曹操多次寫信催促華佗回來,又命地方官趕緊把華佗送回。但華佗自恃身懷絕技,不愿在曹操身邊受驅(qū)使,遲遲不上道。曹操大怒,派人到華佗家查看。如果其妻果然患病,便賞賜小豆四十斛,延長其假期,但限定回來的日子。如果華佗是說謊,便將其捕押到許昌。華佗被押解到許昌,經(jīng)審訊拷問,如實供述了自己的行為。曹操便把華佗殺了。華佗死了,而曹操頭風(fēng)病仍在。曹操說:“華佗能治愈此病。但這個小人故意不治愈,想以此自重。我就是不殺他,他也不會為我斷此病根。”后來,曹操愛子曹沖病重,曹操哀嘆說:“我后悔殺了華佗,讓這個兒子活活死掉。 ”
陳寅恪指出,華佗為歷史上真實人物,這沒有疑義。但《三國志》中敘述的那些神技,卻讓人無法相信。斷腸破腹、數(shù)日即愈,在當(dāng)時決無可能,只能是一種神話。梵文中“藥”,發(fā)音為“阿伽佗”,后來省去“阿”,猶如“阿羅漢”只剩“羅漢”。元化固然本姓華,但本名卻并非“佗”。“當(dāng)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為‘華佗’,實以‘藥神’目之。”

……總而言之,三國志曹沖華佗二傳,皆有佛教故事,輾轉(zhuǎn)因襲雜糅附會于其間,然巨象非中原當(dāng)日之獸,華佗為五天外國之音,其變遷之跡象猶未盡亡,故得以推尋史料之源本。夫三國志之成書,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時,猶不甚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若是之廣,社會所受之影響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誠,猶不能別擇其偽,而并筆之于書。則又治史者所當(dāng)注意之事,固不獨與此二傳有關(guān)而已。
陳壽撰《三國志》時,佛教傳入中國尚不久,而其神話故事卻已傳播如此之廣,在民間社會之影響已經(jīng)如此之深,以至于以陳壽的嚴(yán)謹(jǐn)、精誠,都不能識別其為來自印度的神話,難怪陳寅恪要大發(fā)感慨了。
(三)《崔浩與寇謙之》
本文原刊《嶺南學(xué)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之陳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館叢稿初編》。
文章首先強(qiáng)調(diào)崔浩與寇謙之之關(guān)系,是北朝史中一大公案。寇謙之是著名的道教人物。道教雖然一開始是中國本土產(chǎn)物,但后來漸漸接受模仿外來之學(xué)術(shù)和技藝,變易演進(jìn),便成為一龐大復(fù)雜之混合體。綜觀二千年來道教的發(fā)展變化,每一次變革,必與一種外來學(xué)說的影響有關(guān),而影響道教最深最巨者,當(dāng)推佛教。佛教影響道教的方式,是醫(yī)藥和天算。借助醫(yī)藥和天算,佛教從精神上征服道教人士,讓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佛教的學(xué)說、思想。陳寅恪進(jìn)而說:
……自來宗教之傳播,多假醫(yī)藥天算之學(xué)以為工具,與明末至近世西洋之傳教師所為者,正復(fù)相類,可為明證。吾國舊時醫(yī)學(xué),所受佛教之影響極深……
以醫(yī)藥與天算為傳播手段,是宗教傳播的通例。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亦復(fù)如此。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大大借助了醫(yī)藥。佛教的醫(yī)學(xué)理論和技術(shù)手段,進(jìn)入中醫(yī)系統(tǒng),深刻地影響了中醫(yī)的理念與方法。所以,從佛教傳入之日起,中醫(yī)便不能認(rèn)作純是中國本土產(chǎn)物。

耆域者,天竺人也。晉惠之末,至于洛陽,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因取凈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shù)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此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咒,如咒永文法,樹尋荑發(fā),扶疏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yīng)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數(shù)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yīng)器中有若淤泥者數(shù)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耆域不但能治人之病,還能令死了多年的樹起死回生。《高僧傳》本是為佛教高僧來游中國者立傳,傳主當(dāng)是真實人物。而耆域原本是印度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卻與真實人物同列僧傳。陳寅恪指出:“事雖可笑,其實此正可暗示六朝佛教徒輸入天竺之醫(yī)方明之一段因緣也。”又說:“至道教徒之采用外國輸入之技術(shù)及學(xué)說,當(dāng)不自六朝始,觀吾國舊時醫(yī)學(xué)之基本經(jīng)典,如內(nèi)經(jīng)者,即托之于黃帝與天師問對之言可知。 ”
四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中,論白居易《法曲》時,指出白居易等人認(rèn)為是“華聲”的音樂,其實不過是先前輸入之“胡樂”。例如“霓裳羽衣曲”,“實原本胡樂,又何華聲之可言?”進(jìn)而指出:
夫琵琶之為胡樂而非華聲,不待辯證。而法曲有其器,則法曲之與胡聲有關(guān)可知也。然則元白諸公之所謂華夷之分,實不過今古之別,但認(rèn)輸入較早之舶來品,或以外國材料之改裝品,為真正之國產(chǎn)土貨耳。今世侈談國醫(yī)者,其無文化學(xué)術(shù)史之常識,適與相類,可慨也。20)陳寅恪認(rèn)為,元白諸人在音樂上強(qiáng)行進(jìn)行“華夷之分”,是十分可笑的。他們所謂的“華聲”,不過是較早輸入中國之“夷音”。陳寅恪又把話題轉(zhuǎn)到醫(yī)學(xué)上。今天那些侈談“國醫(yī)”、認(rèn)定所謂“中醫(yī)”是“國粹”者,其可笑正與元白相同。今天人們熟知、信奉的種種中醫(yī)理念、方法,或許正是先前輸入的外國貨。
現(xiàn)在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陳寅恪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意在揭示祖父和父親與清末政壇的關(guān)系,尤其是要說明祖父和父親在戊戌變法中所起的作用。但一開始卻寫的是自家先前三代與中醫(yī)的因緣,并且發(fā)表了一通對中醫(yī)的看法。這看似偏離主旨,其實恐怕意在借中醫(yī)演變,表達(dá)對清末思想界中西之爭的看法。中醫(yī)的許多理論方法被視作“國學(xué)”“國粹”,但其實不過是較早輸入之外來東西。同樣,在許多方面,清末守舊者認(rèn)作是“傳統(tǒng)”“國粹”的東西,也不過是早些時候從外國輸入的洋貨,而被守舊者視作是洪水猛獸、與傳統(tǒng)觀念冰炭難容的思想,只因是新近輸入,便有如此遭遇。
陳寅恪讓我們知道,至遲從元稹、白居易的時候開始,所謂中西之爭、華夷之別,實不過是古今之爭、早遲之別而已。
2018年4月30日
注釋:
(1)(2)(3)(4)(5)(7)(9)(10)(11)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163頁,第165—166頁,第167頁,第168頁,第169頁,第169頁,第169頁,第169—170頁,第169頁。
(6)郭嵩燾:《陳府君墓碑銘》,見《郭嵩燾全集》第十五,岳麓書社2012年12月版,第574頁。
(8)劉夢溪:《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故宮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1—22頁。
(12)陳寅恪:《狐臭與胡臭》,見《寒柳堂集》第140—142頁。
(13)(14)(15)(16)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見《寒柳堂集》第157頁,第157—158頁,第158—159頁,第160—161頁。
(17)(18)(19) 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見《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13頁,第114頁,第114頁。
(20)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144頁。